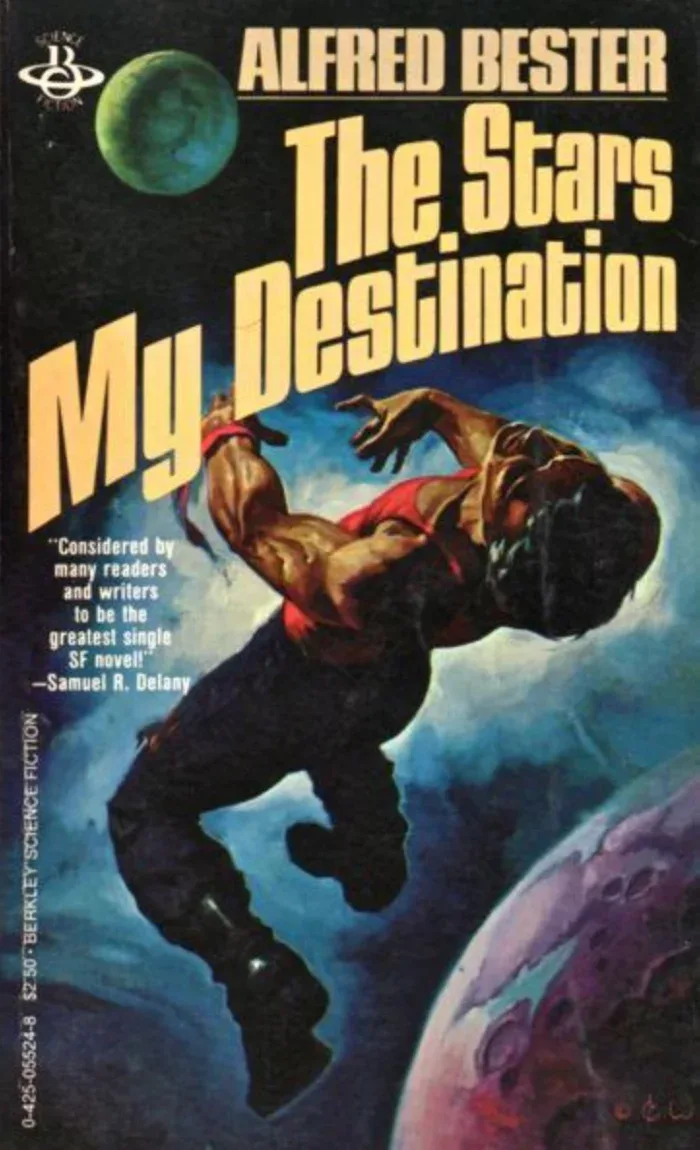第五章
在圣吉龙以南,靠近西班牙-法国边境的地方,坐落着法国最深的深渊——古夫尔·马特尔。它的洞穴在比利牛斯山脉下蜿蜒数英里。它是地球上最令人生畏的洞穴医院。从未有病人成功地从它那漆黑的黑暗中琼特出去。从未有病人成功地确定自己的方位并得知那黑色医院深处的琼特坐标。
除了前额叶切除术,只有三种方法能阻止一个人琼特:头部受到打击导致脑震荡、使用镇静剂阻止集中精神,以及隐藏琼特坐标。在这三种方法中,琼特时代认为隐藏坐标最为实用。
排列在古夫尔·马特尔蜿蜒通道两侧的牢房是从活生生的岩石中开凿出来的。它们从未被照亮。通道也从未被照亮。红外线灯照射着黑暗。这是一种只有佩戴着经过特殊处理镜片的窥视镜的守卫和看护人员才能看到的黑光。对病人来说,只有古夫尔·马特尔的黑色寂静,被远处地下水流的奔腾声打破。
对福伊尔来说,只有寂静、奔流声和医院的例行公事。八点钟(或者可能是这个永恒深渊中的任何时刻),他被铃声唤醒。他起身,收到他的早餐,通过气动管道送入牢房。必须立刻吃掉,因为杯盘的陶瓷代用品设定在十五分钟内溶解。八点半,牢门打开,福伊尔和其他数百人盲目地在蜿蜒的走廊里拖着脚步走向卫生区。
在这里,仍然在黑暗中,他们像屠宰场里的牛肉一样被处理;清洗、剃须、照射、消毒、给药和接种。他们的纸质制服被脱下烧毁。发放新的制服。然后他们拖着脚步回到自己的牢房,牢房在他们去卫生区时已被自动擦洗干净。在他的牢房里,福伊尔听着没完没了的治疗谈话、讲座、道德和伦理指导,度过整个上午。然后又是寂静,除了远处水流的奔腾声和走廊里戴着护目镜的守卫悄无声息的脚步声。
下午是职业疗法。每个牢房里的电视屏幕亮起,病人将手伸入屏幕的阴影框中。他能看到三维图像,感觉到广播传送来的物体和工具。他裁剪医院制服,缝制它们,制造厨房用具和准备食物。尽管实际上他什么也没碰到,他的动作却通过遥控传输到工场,在那里完成工作。在这短暂的一小时放松之后,又是黑暗和寂静。
但每隔一段时间……一周一两次(或许一年一两次),会传来远处沉闷的爆炸声。这些震动足以让福伊尔从他一直在寂静中煽动的复仇熔炉中分心。他向卫生间里那些看不见的人影低声询问。
“那些爆炸声是什么?”
“爆炸声?”
“爆炸声。听起来很远,我。”
“那是‘蓝色琼特’。”
“什么?”
“蓝色琼特。总有那么些时候,有人受够了杰弗里。再也受不了了,他。就向着茫茫的蓝色虚空琼特。”
“耶稣。”
“是的。他们不知道自己在哪儿。不知道要去哪儿。向着黑暗进行蓝色琼特……我们会在山里听到他们的声音。砰!蓝色琼特。”
他感到震惊,但他能理解。黑暗、寂静、单调摧毁了理智,带来了绝望。孤独难以忍受。被埋葬在古夫尔·马特尔监狱医院的病人们急切地盼望着早晨的卫生时段,希望能低声说句话,听到一句话。但这些碎片是不够的,绝望随之而来。然后就会有另一次遥远的爆炸。
有时,受苦的人们会互相攻击,然后在卫生间爆发野蛮的斗殴。这些斗殴会立即被戴着护目镜的守卫制止,早上的讲座就会切换到宣扬耐心美德的“道德纤维”录音带。
福伊尔把录音带背得滚瓜烂熟;每一个词,磁带上的每一次咔哒声和裂纹声。他学会了厌恶讲师的声音;那理解人的男中音,那欢快的男高音,那推心置腹的男低音。他学会了对治疗性的单调充耳不闻,机械地进行他的职业治疗,但他无力抵抗无尽的独处时光。狂怒是不够的。
他记不清日子,记不清饭餐,记不清布道。他不再在卫生间低语。他的心智开始飘忽,他开始漫游。他想象自己回到了“诺玛德”号上,重温着他为生存而战的经历。然后,他连这微弱的幻觉也抓不住了,开始越来越深地沉入紧张性精神症的深渊;沉入子宫般的寂静、子宫般的黑暗和子宫般的睡眠。
有过短暂的梦境。一次,一位天使对他哼唱。另一次,她轻声歌唱。他三次听到她说话;“哦,上帝……”和“该死的!”还有“哦……”带着令人心碎的降调。
他沉入他的深渊,听着她的话。
“有一条出路,”他的天使在他耳边低语,甜美而令人安慰。她的声音柔和而温暖,却燃烧着愤怒。那是一位愤怒天使的声音。
“有一条出路。”它从虚无中在他耳边低语,突然间,带着绝望的逻辑,他意识到有一条逃离古夫尔·马特尔的路。他以前没看到真是个傻瓜。
“是的,”他嘶哑地说。“有条出路。”
传来一声轻柔的喘息,接着是一个轻柔的问题:“谁在那儿?”
“是我,就我,”福伊尔说。“你认识我。”
“你在哪里?”
“这儿。我一直在这儿,我。”
“但这里没有人。我一个人。”
“得谢谢你帮我。”
“听到声音是坏事,”愤怒的天使低语道。“走向深渊的第一步。我得停下来。”
“你给我指了条出路。蓝色琼特。”
“蓝色琼特!我的天,这一定是真的。你说的是贫民窟的行话。你一定是真的。你是谁?”
“格利弗·福伊尔。”
“但你不在我的牢房。你甚至不在附近。男人在古夫尔·马特尔的北区。女人在南区。我在南900。你在哪里?”
“北-111。”
“你离我四分之一英里远。我们怎么能——我的天!当然!是‘低语线’。我一直以为那是个传说,但它是真的。它现在起作用了。”
“我这就走,我,”福伊尔低语道。“蓝色琼特。”
“福伊尔,听我说。忘了蓝色琼特。别扔掉这个机会。这是个奇迹。”
“什么奇迹?”
“古夫尔·马特尔有个声学怪现象……地下洞穴里常有……回声、通道和回音廊的怪现象。老前辈们称之为‘低语线’。我从不相信他们。没人相信过,但这是真的。我们正通过低语线互相交谈。除了我们,没人能听到我们。我们可以说话,福伊尔。我们可以计划。也许我们可以逃脱。”
她的名字叫吉斯贝拉·麦昆。她性情火爆,独立自主,聪明伶俐,因盗窃罪在古夫尔·马特尔服刑五年。吉斯贝拉兴致勃勃、怒气冲冲地向福伊尔讲述了她反抗社会的经历。
“你不知道琼特对女人做了什么,格利。它把我们锁起来了;把我们送回了后宫。”
“什么是后宫,姑娘?”
“一个闺房。一个把女人冷藏起来的地方。经过一千年的文明(书上这么说),我们仍然是财产。琼特对我们的贞洁、我们的价值、我们的完好状态是如此大的威胁,以至于我们像保险箱里的金盘子一样被锁起来。我们无事可做……没有任何体面的事。没有工作。没有事业。没有出路,格利,除非你冲出去,打破所有规则。”
“你非得这样吗,吉兹?”
“我必须独立,格利。我必须过自己的生活,而那是社会允许我的唯一方式。所以我离家出走,变成了骗子。”吉兹接着描述了她反抗的骇人细节:“脾气敲诈”、“白内障敲诈”、“蜜月和讣告抢劫”、“獾式琼特”和“闪光扒窃”。
福伊尔告诉了她关于诺玛德号和汤加岛的事;他的仇恨和他的计划。他没有告诉吉斯贝拉他的脸或者小行星带里那两千万白金条的事。
“诺玛德号怎么了?”吉斯贝拉问道。“是像那个叫达格纳姆的人说的那样吗?被外空袭击者炸毁了?”
“我不知道,我。记不清了,姑娘。”
“爆炸可能抹去了你的记忆。休克。而且被困六个月也没什么帮助。你注意到诺玛德号上有什么值得打捞的东西吗?”
“没有。”
“达格纳姆提到过什么吗?”
“没有,”福伊尔撒谎道。
“那么他一定有别的理由把你逼进古夫尔·马特尔。他肯定还想从诺玛德号上得到别的东西。”
“是的,吉兹。”
“但你那样试图炸毁沃加真是个傻瓜。你就像一头野兽试图惩罚伤害它的陷阱。钢铁没有生命。它不会思考。你无法惩罚沃加。”
“不懂你的意思,姑娘。沃加从我身边过去了。”
“你要惩罚的是大脑,格利。设下陷阱的大脑。找出沃加号上的人。找出下令从你身边经过的人。惩罚他。”
“是的。怎么做?”
“学会思考,格利。那个能想出如何让诺玛德号启动、如何组装炸弹的头脑,应该也能想出办法。但不要再用炸弹了;用脑子。找到沃加号船员中的一员。他会告诉你船上有谁。追踪他们。找出下令的人。然后惩罚他。但这需要时间,格利……时间和金钱;比你拥有的更多。”
“我有一辈子的时间,我。”
他们隔着“低语线”低语了好几个小时,声音虽小却近在耳边。每个牢房只有一个特定的点能听到对方的声音,这就是为什么他们花了这么长时间才发现这个奇迹。但现在他们弥补了失去的时间。吉斯贝拉开始教育福伊尔。
“如果我们能逃出古夫尔·马特尔,格利,那必须一起行动,而我不会把自己的命运交给一个文盲伙伴。”
“谁是文盲?”
“你就是,”吉斯贝拉坚定地回答。“我有一半时间得跟你说黑话,我。”
“我能读会写。”
“也就仅此而已……这意味着除了蛮力,你将毫无用处。”
“说正经的,你,”他生气地说。
“我说的就是正经的,我。如果世界上最强的凿子没有刃,那又有什么用?我们得磨砺你的智慧,格利。得教育你,伙计,就是这样。”
他顺从了。他意识到她是对的。他不仅需要为越狱做准备,也需要为寻找沃加号进行训练。吉斯贝拉是一位建筑师的女儿,受过一流的教育。她把这些知识,掺杂着五年黑社会生涯的愤世嫉俗的经验,灌输给福伊尔。偶尔他会反抗艰苦的学习,然后就会有低声的争吵,但最终他会道歉并再次屈服。有时吉斯贝拉会厌倦教书,然后他们就会漫无目的地闲聊,在黑暗中分享梦想。
“我想我们坠入爱河了,格利。”
“我也这么想,吉兹。”
“我是个老巫婆,格利。一百零五岁了。你长什么样?”
“很可怕。”
“多可怕?”
“我的脸。”
“你说得自己很浪漫。是那种让男人更有魅力的激动人心的伤疤吗?”
“不是。我们见面时你会看到的,我们。那不对,是吧,吉兹?就是简单的:‘我们见面时。’句号。”
“好孩子。”
“我们总有一天会见面的,对吧,吉兹?”
“希望很快,格利。”吉斯贝拉遥远的声音变得干脆利落。“但我们必须停止空想,开始工作。我们必须计划和准备。”
吉斯贝拉从黑社会继承了大量关于古夫尔·马特尔的信息。从未有人成功地从洞穴医院中琼特出去,但几十年来,黑社会一直在收集和整理关于它们的信息。正是从这些数据中,吉斯贝拉迅速识别出了连接他们的“低语线”。也正是基于这些信息,她开始讨论逃跑。
“我们能成功,格利。一分钟也别怀疑。他们的安全系统肯定有几十个漏洞。”
“以前没人找到过。”
“以前没人有过搭档。我们会共享信息,我们会成功的。”
他不再拖着脚步往返于卫生间。他触摸着走廊的墙壁,留意着门,注意它们的质地,计数,倾听,推断并汇报。他记下了卫生间里的每一个步骤,并向吉兹汇报。他在淋浴间和鼻烟室里向周围的人低声提出的问题都带有目的性。福伊尔和吉斯贝拉一起,构建了古夫尔·马特尔的日常运作及其安全系统的图景。
一天早上,从卫生间回来时,他正要踏回自己的牢房,却被拦住了。
“排好队,福伊尔。”
“这里是北-111。我现在知道该在哪儿下车了。”
“继续走。”
“但是——”他吓坏了;“你们要换我的牢房?”
“有访客要见你。”
他被押送到北走廊的尽头,那里与构成医院巨大十字架的其他三条主走廊交汇。十字架的中心是行政办公室、维修车间、诊所和工厂。福伊尔被推进一个和他牢房一样黑暗的房间。门在他身后关上了。他意识到黑暗中有一个微弱的闪烁轮廓。那不过是一个模糊身体和骷髅头的幽灵影像。骷髅脸上两个黑色的圆盘要么是眼窝,要么是红外护目镜。
“早上好,”达格纳姆说。
“你?”福伊尔惊呼道。
“我。我有五分钟时间。坐下。椅子在你后面。”
福伊尔摸索着找到椅子,慢慢坐下。
“玩得开心吗?”达格纳姆问道。
“你想要什么,达格纳姆?”
“情况变了,”达格纳姆干巴巴地说。“上次我们谈话时,你的台词全是‘滚蛋’。”
“滚蛋,达格纳姆,如果这能让你好受点的话。”
“你的应对能力提高了;你的谈吐也一样。你变了,”达格纳姆说。“变得太厉害了,也太快了。我不喜欢。你发生了什么事?”
“我一直在上夜校。”
“你在这所夜校待了十个月了。”
“十个月!”福伊尔惊讶地重复道。“那么久?”
“十个月没有光明,没有声音。十个月的单独监禁。你应该垮了。”
“哦,我确实垮了。”
“你应该在抱怨。我说得对。你非同寻常。照这个速度下去太久了。我们等不及了。我想提出一个新的提议。”
“诺玛德号金条的百分之十。两百万。”
“两百万!”福伊尔惊呼道。“你为什么一开始不提这个?”
“因为我不知道你的能耐。成交吗?”
“差不多。还没。”
“还有什么?”
“我离开古夫尔·马特尔。”
“当然。”
“还有其他人。”
“可以安排。”达格纳姆的声音变得尖锐。“还有别的吗?”
“我要求查阅普雷斯蒂安的档案。”
“不可能。你疯了吗?讲点道理。”
“他的航运档案。”
“干什么用?”
“查他一艘船上的人员名单。”
“哦。”达格纳姆的热情又回来了。“这个我可以安排。还有别的吗?”
“没有了。”
“那就成交。”达格纳姆很高兴。那模糊的光影从椅子上站了起来。“我们六小时内让你出来。我们会立刻开始为你朋友安排。可惜我们浪费了这段时间,但没人能搞懂你,福伊尔。”
“你为什么不派个心灵感应者来审问我?”
“心灵感应者?讲点道理,福伊尔。整个内行星加起来都不到十个完全的心灵感应者。他们的时间都排到未来十年了。无论花多少钱,我们都说服不了一个来打断他的日程安排。”
“我道歉,达格纳姆。我以为你不懂行。”
“你差点伤了我的感情。”
“现在我知道你只是在撒谎。”
“你在恭维我。”
“你可以雇一个心灵感应者。为了两千万的分成,你肯定能轻易雇到一个。”
“政府绝不会——”
“他们并非都为政府工作。不。你肯定有什么太烫手的东西,不能让心灵感应者靠近。”
光芒的模糊身影猛地扑过房间,抓住了福伊尔。
“你知道多少,福伊尔?你在掩盖什么?你在为谁工作?”达格纳姆的手颤抖着。“天哪!我真是个傻瓜。当然你不寻常。你不是普通的太空人。我问你;你在为谁工作?”
福伊尔挣开达格纳姆的手。“没人,”他说。“没人,除了我自己。”
“没人,嗯?包括你在古夫尔·马特尔那个你急于营救的朋友?天哪,你差点骗了我,福伊尔。告诉杨-尤维尔上尉我祝贺他。他的手下比我想象的要好。”
“我从未听说过任何杨-尤维尔。”
“你和你的同伴将在这里腐烂。交易取消。你会在这里溃烂。我会把你转移到医院最差的牢房。我会把你沉到古夫尔·马特尔的最底层。我会……警卫,这里!警——”
福伊尔抓住达格纳姆的喉咙,把他拖倒在地,用他的头撞击石板地。达格纳姆扭动了一下,然后就不动了。福伊尔扯下他脸上的护目镜戴上。视力在柔和的红色和玫瑰色的光影中恢复了。
他身处一个小接待室,里面有一张桌子和两把椅子。福伊尔脱下达格纳姆的夹克穿上,两下快速的猛拉撕裂了肩膀。达格纳姆那顶歪戴的强盗帽放在桌子上。福伊尔把它扣在头上,拉下帽檐遮住脸。
对面的墙上有两扇门。福伊尔打开一扇门一条缝。它通向北走廊。他关上门,跳过房间,试了另一扇门。它通向一个防琼特的迷宫。福伊尔溜过门,进入迷宫。没有向导带领他穿过迷宫,他立刻迷路了。他开始在曲折的通道里奔跑,发现自己又回到了接待室。达格纳姆正挣扎着跪起来。
福伊尔再次转回迷宫。他跑着。他来到一扇关着的门前,猛地推开。门后是一个用正常光线照明的大型车间。两个在机床旁工作的技术员惊讶地抬起头。
福伊尔抓起一把大锤,像个穴居人一样扑向他们,将他们击倒。身后传来达格纳姆在远处的喊叫声。他疯狂地环顾四周,害怕发现自己被困在死胡同里。车间呈L形。福伊尔绕过拐角,冲破另一个防琼特迷宫的入口,再次迷路。古夫尔·马特尔的警报开始响起。福伊尔用大锤猛击迷宫的墙壁,打碎了薄薄的塑料遮蔽物,发现自己身处女性区南走廊的红外线照明下。
两个女警卫沿着走廊跑过来,跑得很快。福伊尔挥动大锤,放倒了她们。他靠近走廊的尽头。面前是一长排牢房门,每扇门上都标着一个发光的红色数字。头顶上,走廊由发光的红色球体照明。福伊尔踮起脚尖,用锤子击打头顶上方的球体。他敲穿了灯座,砸断了电缆。整个走廊一片漆黑……即使戴着护目镜也看不见。
“扯平了;现在都在黑暗里了,”福伊尔喘着气说,沿着走廊飞奔,一边摸着墙壁一边数着牢房门。吉斯贝拉已经准确地向他描述了南区的景象。他正数着路走向南900。他撞上一个人影,是另一个警卫。福伊尔用大锤砍了她一下。福伊尔数乱了,继续跑,停了下来。
“吉兹!”他吼道。
他听到了她的声音。他遇到另一个警卫,解决了她,继续跑,找到了吉斯贝拉的牢房。
“格利,看在上帝的份上……”她的声音很低沉。
“退后,姑娘。退后。”他用大锤对着门猛击三下,门向内爆开。他踉跄着走进去,撞上一个人影。
“吉兹?”他喘着气说。“不好意思……路过。想着顺便拜访一下。”
“格利,以——的名义!”
“是的。真是糟糕的见面方式,嗯?来吧。出去,姑娘。出去!”
他把她拖出牢房。“我们不能试图冲过办公室。他们不喜欢我回去那里。你的卫生间往哪边走?”
“格利,你疯了。”
“整个区都黑了。我砸断了电缆。我们还有一半机会。走,姑娘。走。”
他用力推了她一下,她领着他沿着通道走向女子卫生间的自动隔间。当机械手脱掉他们的制服,给他们涂上肥皂、喷洒和消毒时,福伊尔摸索着找到医疗观察窗的玻璃窗格。他找到了它,挥动大锤砸碎了它。
“进去,吉兹。”他把她扔进窗户,自己也跟了进去。他们俩都赤身裸体,浑身油腻的肥皂,伤痕累累,流着血。福伊尔滑倒了,在黑暗中摸索着寻找医务人员进入的门,撞得粉碎。
“找不到门,吉兹。从诊所过来的门。我——”
“嘘!”
“但是——”
“安静,格利。”一只沾满肥皂的手找到了他的嘴,捂住了它。她紧紧抓住他的肩膀,指甲刺破了他的皮肤。洞穴里的喧嚣声中,传来近在咫尺的脚步声。警卫们正盲目地穿过卫生隔间。红外线灯还没修好。
“他们可能没注意到窗户,”吉斯贝拉嘶嘶地说。“安静。”
他们蹲在地板上。脚步声杂乱地穿过围栏。然后他们走了。
“现在安全了,”吉斯贝拉低语道。“但他们很快就会有探照灯。来吧,格利。出去。”
“但是通往诊所的门,吉兹。我以为——”
“没有门。他们用螺旋楼梯,而且会把楼梯拉上去。他们也想到了这种逃跑方式。我们得试试洗衣升降机。天知道那有什么用。哦,格利,你这个傻瓜!你这个十足的傻瓜!”
他们爬过观察窗回到围栏里。他们在黑暗中寻找运送脏制服和发放新制服的升降机。而在黑暗中,自动机械手再次给他们涂上肥皂、喷洒和消毒。他们什么也找不到。
一阵警报器的尖锐哭嚎声突然在洞穴中回荡,压倒了所有其他声音。随之而来的是一片令人窒息的寂静,如同黑暗本身。
“他们在用测震仪追踪我们,格利。”
“什么?”
“测震仪。它能追踪穿过半英里坚硬岩石的低语。这就是他们拉响警报要求安静的原因。”
“洗衣升降机?”
“找不到。”
“那就来吧。”
“去哪儿?”
“我们跑。”
“去哪儿?”
“我不知道,但我不会束手就擒。来吧。运动对你有好处。”
他又一次把吉斯贝拉推到前面,他们奔跑着,喘息着,踉跄着,穿过黑暗,向下进入南区最深的区域。吉斯贝拉摔倒了两次,撞在通道的转弯处。福伊尔带头跑,手里握着二十磅重的大锤,锤柄像天线一样伸在前面。然后他们撞到一堵空白的墙壁,意识到已经到了走廊的尽头。他们被困住了,无路可逃。
“现在怎么办?”
“不知道。看来我的主意也到头了。我们肯定回不去了。我在办公室里揍了达格纳姆。讨厌的家伙。看起来像毒药瓶上的标签。你有什么主意吗,姑娘?”
“哦,格利……格利……”吉斯贝拉抽泣起来。
“我指望着你的主意呢。‘不要再用炸弹了,’你说。真希望我现在有一个。可以——等等。”他摸了摸他们倚靠着的湿漉漉的墙壁。他感觉到砂浆缝隙的棋盘格凹痕。
“G·福伊尔快报。这不是天然洞壁。是人造的。砖石结构。摸摸看。”
吉斯贝拉摸了摸墙。“那又怎样?”
“意思是这条通道不止于此。它继续延伸。他们把它堵住了。让开。”
他把吉斯贝拉推到通道上方,用手在地上蹭了蹭,给沾满肥皂的手掌增加摩擦力,然后开始用大锤猛击墙壁。他以稳定的节奏挥舞着,哼哧哼哧地喘着气。钢制大锤击打墙壁,发出如同水下撞击石头般的沉闷声响。
“他们来了,”吉兹说。“我听见了。”
沉闷的打击声开始带有碎裂、碾压的杂音。传来一阵低语声,接着是松散砂浆持续不断的细碎掉落声。福伊尔加倍努力。突然,传来一声巨响,一股冰冷的空气冲到他们脸上。
“通了,”福伊伊尔咕哝道。
他猛烈地攻击墙上破洞的边缘。砖块、石头和旧砂浆四处飞溅。福伊尔停下来,叫了吉斯贝拉。
“试试。”他扔掉大锤,抓住她,把她举到齐胸高的开口处。当她试图扭动身体穿过锋利的边缘时,疼得叫喊起来。福伊尔毫不留情地推着她,直到她的肩膀和臀部都过去了。他松开她的腿,听到她掉到另一边的声音。
福伊尔把自己拉上去,撕扯着身体穿过墙上锯齿状的缺口。他感觉到吉斯贝拉的手试图在他摔落在一堆松散砖块和砂浆中时缓冲一下。他们俩都穿过去了,进入了古夫尔·马特尔未被占据的洞穴的冰冷黑暗中……数英里未经探索的石窟和洞穴。
“天哪,我们还能成功,”福伊尔咕哝道。
“我不知道是否有出路,格利,”吉斯贝拉冷得发抖。“也许这里全是死胡同,与医院隔绝了。”
“一定有出路。”
“我不知道我们能否找到。”
“我们必须找到。走吧,姑娘。”
他们在黑暗中跌跌撞撞地前进。福伊尔扯掉眼睛上那副没用的护目镜。他们撞上岩架、角落、低矮的天花板;他们从斜坡和陡峭的台阶上摔下来。他们爬过一道刀刃般的山脊,来到一片平坦的地面,脚下一滑。两人都重重地摔在一片光滑的地板上。福伊尔摸了摸,用舌头舔了一下。
“冰,”他咕哝道。“好兆头。我们在一个冰洞里,吉兹。地下冰川。”
他们摇摇晃晃地站起来,叉开双腿,小心翼翼地穿过这在古夫尔·马特尔深渊中形成了数千年的冰层。他们爬进一片由石笋和钟乳石组成的石林,石笋从锯齿状的地面向上生长,钟乳石从洞顶向下垂落。每一步的震动都使巨大的钟乳石松动,每一刻都有一根沉重而尖锐的石矛从头顶轰然落下。在石林的边缘,福伊尔停下来,伸手拽了一下。传来清脆的金属声。他拉起吉斯贝拉的手,把一根细长的锥形石笋放在她手里。
“手杖,”他咕哝道。“像盲人一样用它。”他折断另一根,然后他们敲打着、摸索着、踉跄着穿过黑暗。除了恐慌的奔跑声——他们喘息的呼吸和狂跳的心脏,石杖的敲击声,无数水滴声,以及古夫尔·马特尔下方地下河遥远的奔流声——再无其他声音。
“不是那边,姑娘,”福伊尔碰了碰她的肩膀。“再往左一点。”
“你到底知不知道我们在往哪里走,格利?”
“向下,吉兹。跟着任何向下的斜坡走。”
“你有什么主意?”
“是的。惊喜,惊喜!用脑子代替炸弹。”
“用脑子代替——”吉斯贝拉歇斯底里地大笑起来。“你用大锤冲进南区,这就是你所谓的用脑子代替炸——炸——炸——”她像驴一样嘶叫着,像猫头鹰一样嚎叫着,完全失控,直到福伊尔抓住她摇晃起来。
“闭嘴,吉兹。如果他们用测震仪追踪我们,他们从火星都能听到你。”
“对——对不起,格利。对不起……”她吸了口气。“为什么向下?”
“那条河;我们一直听到的那条。它一定就在附近。很可能是从后面的冰川融化下来的。”
“那条河?”
“唯一确定的出路。它一定在山里的某个地方冲出来。我们游泳过去。”
“格利,你疯了!”
“怎么了,你?你不会游泳?”
“我会游泳,但是——”
“那我们就得试试。走吧,吉兹。来吧。”
随着他们的体力开始衰竭,河水的奔流声越来越响。吉斯贝拉终于停了下来,喘着粗气。
“格利,我得休息一下。”
“太冷了。继续走。”
“我走不动了。”
“继续走。”他摸索着去抓她的胳膊。
“把你的手拿开,”她愤怒地喊道。瞬间,她变得像只发怒的小猫。他惊讶地松开了她。
“你怎么了?冷静点,吉兹。我指望着你呢。”
“指望什么?我告诉过你我们必须计划……制定一个逃跑方案……现在你却把我们困在这里了。”
“我自己也被困住了。达格纳姆要换我的牢房。我们没法再用低语线了。我不得不这样做,吉兹……而且我们出来了,不是吗?”
“出来到哪里?迷失在古夫尔·马特尔。寻找一条该死的河淹死自己。你是个傻瓜,格利,而我也是个白痴,让你把我困在这里。该死的!该死的!你把一切都拉低到你那低能的水平,你也把我拉下来了。跑。打。揍。这就是你所知道的一切。打。砸。炸。毁——格利!”
吉斯贝拉尖叫起来。黑暗中传来一阵碎石的咔嗒声,她的尖叫声逐渐减弱,消失在一声沉重的落水声中。福伊尔听到她在水中挣扎的声音。他向前一跃,喊道:“吉兹!”然后踉跄着跌下悬崖边缘。
他摔了下去,平拍在水面上,冲击力令人眩晕。冰冷的河水包围了他,他分不清哪里是水面。他挣扎着,窒息着,感觉到湍急的水流将他冲撞在冰冷滑腻的岩石上,然后像气泡一样被冲到水面。他咳嗽着,喊叫着。他听到吉斯贝拉的回应,她的声音微弱而模糊,被咆哮的激流声淹没。他顺着水流游泳,试图追上她。
他喊叫着,听到她越来越微弱的回应声。咆哮声越来越响,突然间,他被冲下一道嘶嘶作响的瀑布水帘。他沉入一个深潭底部,再次挣扎着浮出水面。旋转的水流将他缠绕在一个冰冷的身体上,那身体正紧贴着光滑的岩壁支撑着。
“吉兹!”
“格利!谢天谢地!”他们紧紧抱在一起片刻,任由河水撕扯着他们。
“格利……”吉斯贝拉咳嗽着。“它从这里流过。”
“那条河?”
“是的。”他扭动身体经过她,靠着墙壁支撑自己,感觉到一个水下隧道的入口。水流正把他们吸进去。
“抓紧,”福伊尔喘着气说。他向左右探索。水潭的墙壁光滑,没有抓手。
“我们爬不出去。得从这儿过去。”
“没有空气,格利。没有水面。”
“不可能永远没有。我们屏住呼吸。”
“可能比我们能屏住呼吸的时间还长。”
“只能赌一把了。”
“我做不到。”
“你必须做。没有别的办法了。深呼吸。抓住我。”
他们在水中互相支撑着,大口喘气,充满肺部。
福伊尔把吉斯贝拉推向水下隧道。“你先走。我紧跟在你后面……如果你遇到麻烦,我会帮你。”
“麻烦!”吉斯贝拉声音颤抖地喊道。她潜入水中,任由水流将她吸入隧道口。福伊尔紧随其后。汹涌的水流将他们向下、向下、向下拖拽,在一个磨得像玻璃一样光滑的隧道两侧来回撞击。福伊尔紧跟在吉斯贝拉后面游着,感觉到她扑腾的双腿敲打着他的头和肩膀。
他们穿过隧道,直到肺部炸裂,盲目的眼睛凸出。然后又传来咆哮声和水面,他们可以呼吸了。光滑如玻璃的隧道壁变成了锯齿状的岩石。福伊尔抓住吉斯贝拉的腿,抓住河边一块突出的石头。
“得从这里爬出去,”他喊道。
“得爬出去。你听到前面那咆哮声了吗?瀑布。急流。会被撕成碎片。出来,吉兹。”
她太虚弱了,爬不出水面。他把她的身体推上岩石,自己也跟了上去。他们躺在湿漉漉的石头上,累得说不出话来。最后,福伊尔疲惫地站了起来。
“必须继续,”他说。“沿着河走。准备好了吗?”
她无法回答;她无法抗议。他把她拉起来,他们踉跄着穿过黑暗,试图沿着激流的岸边走。他们穿过的巨石巨大无比,像支石墓一样矗立着,堆积、混乱、散落成一个迷宫。他们摇摇晃晃地扭曲着穿过它们,迷失了河流的方向。他们无处可去。
“迷路了……”福伊尔厌恶地咕哝道。“我们又迷路了。这次真的迷路了。我们该怎么办?”
吉斯贝拉开始哭泣。她发出无助而又愤怒的声音。
福伊尔踉跄着停下来坐下,把她也拉了下来。
“也许你说得对,姑娘,”他疲惫地说。“也许我真是个该死的傻瓜。我把我们困在这个无法琼特的困境里,我们输了。”
她没有回答。
“脑力活就到此为止了。你给我的教育真是糟糕透顶。”他犹豫了一下。“你觉得我们该不该试着原路返回医院?”
“我们永远也回不去了。”
“我想也是。只是在练习我的脑子。我们该不该弄出点动静?制造点噪音好让他们用测震仪追踪我们?”
“他们永远也听不到……永远也找不到我们。”
“我们可以制造足够的噪音。你可以稍微打我几下。对我们俩来说都是一种乐趣。”
“闭嘴。”
“谋杀!真是一团糟!”他向后瘫倒,头枕在一丛柔软的草上。
“至少我在诺玛德号上还有机会。有食物,我能看到我想去的地方。我能——”他停了下来,猛地坐直。“吉兹!”
“别说那么多话。”
他摸了摸身下的地面,抓起一把泥土和几簇草。他把它们塞到她脸上。
“闻闻这个,”他笑着说。“尝尝。是草。吉兹。泥土和草。我们逃出古夫尔·马特尔了。”
“什么?”
“外面是黑夜。漆黑一片。阴天。我们从洞穴里出来却不知道。我们出来了,吉兹!我们成功了!”
他们跳起来,仔细看着、听着、嗅着。夜色难以穿透,但他们听到了夜风轻柔的叹息,闻到了绿色植物生长的甜香。远处传来狗叫声。
“我的天,格利,”吉斯贝拉难以置信地低语道。“你说得对。我们逃出古夫尔·马特尔了。我们只需要等到天亮。”她笑了起来。她张开双臂拥抱他,吻了他,他也回以拥抱。他们兴奋地喋喋不休。他们再次瘫倒在柔软的草地上,疲惫不堪,却无法休息,渴望着,不耐烦着,眼前是全部的人生。
“你好,格利,亲爱的格利。你好,格利,过了这么久。”
“你好,吉兹。”
“我告诉过你我们总有一天会见面的……很快就会。我告诉过你,亲爱的。今天就是那一天。”
“是夜晚。”
“是夜晚,确实如此。但不再有沿着低语线的夜间低语。我们的夜晚结束了,格利亲爱的。”
突然,他们意识到自己赤身裸体,紧紧相拥,不再分离。吉斯贝拉沉默了,但没有动。他几乎是愤怒地抱紧她,用一种不亚于她的欲望将她吞没。
黎明到来时,他看到她很美;修长苗条,有着烟红色的头发和丰满的嘴唇。
但黎明到来时,她看到了他的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