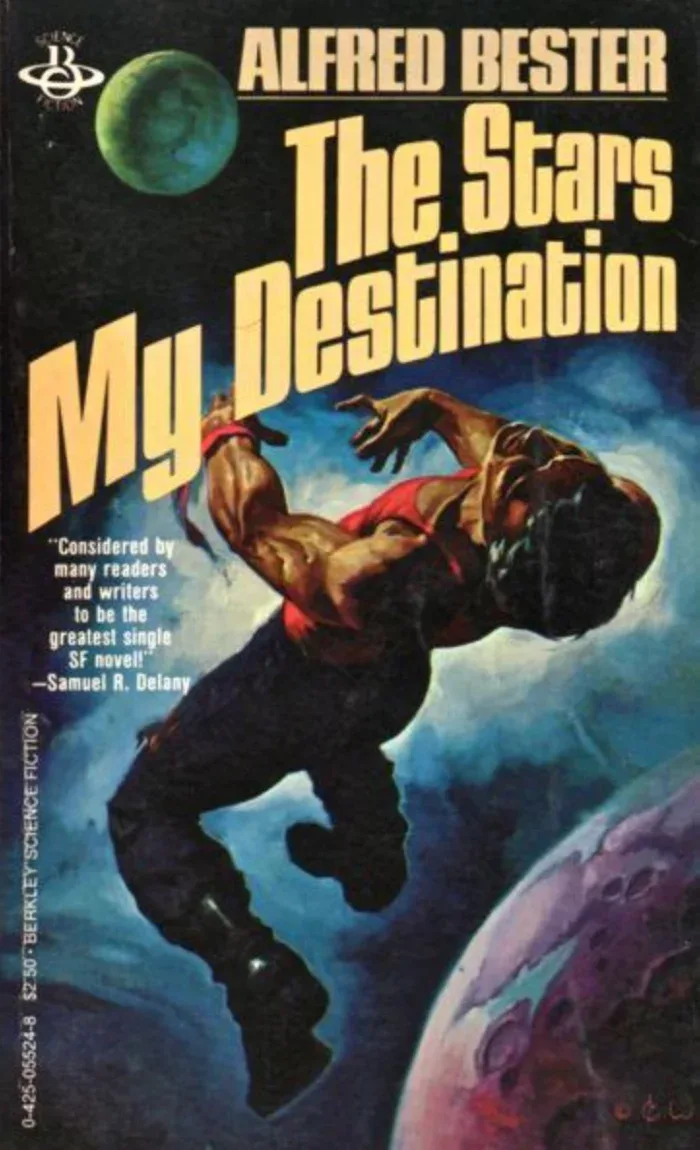他瞬移辛辛那提-新奥尔良-蒙特雷到墨西哥城,出现在庞大的联合地球大学医院的精神病科。科这个名字几乎不足以形容这个区域,它占据了医院这座大都市中的一整个城区。达格纳姆瞬移到治疗部第43层,看向那个隔离的水缸,福伊尔正漂浮在里面,不省人事。他瞥了一眼在场的、留着络腮胡的杰出绅士。
“你好,弗里茨。”
“你好,索尔。”
“真是的,精神病科主任亲自照看我的病人。”
“我想我们欠你人情,索尔。”
“你还在为蒂科沙滩的事耿耿于怀吗,弗里茨?我没有。我的辐射污染了你的病区吗?”
“我已经把所有东西都屏蔽了。”
“准备好干脏活了吗?”
“我真希望知道你到底想干什么。”
“信息。”
“而你必须把我的治疗部门变成一个审讯室来获取它?”
“就是这个主意。”
“为什么不用普通的药物?”
“已经试过了。没用。他不是普通人。”
“你知道这是非法的。”
“我知道。改变主意了?想退出?我可以花二十五万复制你的设备。”
“不,索尔。我们永远欠你人情。”
“那就开始吧。先来‘噩梦剧场’。”
他们推着水缸沿着走廊进入一个一百英尺见方的软垫房间。这是治疗部门一个被废弃的实验项目。噩梦剧场曾是早期试图通过将精神分裂症患者退缩的幻想世界变得无法居住,从而将他们震回客观世界的尝试。但这种对患者情感的粉碎和撕裂被证明是一种过于残酷且效果可疑的治疗方法。
为了达格纳姆,精神病科主任掸去了3D视觉投影仪上的灰尘,并重新连接了所有感官投影仪。他们将福伊尔从他的水缸中倒出,给他注射了一针苏醒剂,并将他留在地板中央。他们移走了水缸,关掉灯,进入了隐藏的控制室。在那里,他们打开了投影仪。
世上每个孩子都以为自己的幻想世界独一无二。精神病学知道,个人幻想中的欢乐与恐惧是全人类共有的遗产。我们的恐惧、罪疚、恐怖和羞耻可以从一个人身上交换到另一个人身上,而无人会注意到其中的区别。联合医院的治疗部门记录了数千份情感磁带,并将它们浓缩成噩梦剧场中一场包罗万象、恐怖至极的表演。
福伊尔醒了过来,气喘吁吁,汗流浃背,却从未意识到自己已经醒来。他被长着蛇发、血眼的复仇女神厄里倪厄斯抓住。他被追逐、诱捕、从高处抛下、焚烧、剥皮、弓弦勒死、被寄生虫覆盖、被吞噬。他尖叫着。他奔跑着。剧场里的雷达“蹒跚场”阻碍了他的脚步,将它们变成了梦中奔跑时那种可怕的慢动作。而在磨砺声、尖叫声、呻吟声、追逐声组成的刺耳杂音中,一个持续不断的声音的细线低语着,袭击着他的耳朵。
“诺玛德在哪里诺玛德在哪里诺玛德在哪里诺玛德在哪里诺玛德在哪里?”
“沃加,”福伊尔嘶哑地说。“沃加。”他被自己的执念所感染。他自己的噩梦使他对这一切免疫了。
“诺玛德在哪里?你把诺玛德留在哪里了?诺玛德发生了什么?诺玛德在哪里?”
“沃加,”福伊尔喊道。“沃加。沃加。沃加。”
在控制室里,达格纳姆咒骂着。精神病科主任监视着投影仪,瞥了一眼时钟。
“一分四十五秒,索尔。他撑不了多久了。”
“他必须崩溃。给他最后的特效。”
他们将福伊尔活埋了,缓慢地、无情地、可怕地。他被带入黑暗的深渊,被包裹在恶臭的粘液中,隔绝了光线和空气。他慢慢窒息,同时一个遥远的声音轰鸣着:“诺玛德在哪里?你把诺玛德留在哪里了?如果你找到诺玛德就能逃脱。诺玛德在哪里?”
但福伊尔回到了“诺玛德”号上他那无光、无气的棺材里,舒适地漂浮在甲板和顶棚之间。他蜷缩成一个紧密的胎儿姿势,准备入睡。他心满意足。他会逃脱的。他会找到沃加。
“刀枪不入的混蛋!”达格纳姆咒骂道。“以前有人抵抗过噩梦剧场吗,弗里茨?”
“从未。你说得对。那是个不寻常的人,索尔。”
“必须把他撕开。好吧,别再搞这些了。我们接下来试试‘夸大狂’模式。演员们准备好了吗?”
“都准备好了。”
“那就开始吧。”
妄想症有六种可能的发展方向。“夸大狂”(Megalomania的缩写)模式是治疗部门用于确定和描绘特定夸大狂病程的戏剧化诊断技术。
福伊尔在一张豪华的四柱大床上醒来。他身处一间豪华的卧室,挂着锦缎,墙纸是天鹅绒。他好奇地环顾四周。柔和的阳光透过格子窗滤入。房间对面,一个贴身男仆正悄悄地摆放衣服。
“嘿……”福伊尔咕哝道。
男仆转过身。“早上好,福尔迈尔先生,”他低声说道。
“什么?”
“早上好,先生。我已经准备好了棕色斜纹布衣服和科尔多瓦皮鞋,先生。”
“怎么了,你?”
“我——”男仆好奇地看着福伊尔。“有什么不对劲吗,福尔迈尔先生?”
“你叫我什么,伙计?”
“用您的名字,先生。”
“我的名字是……福尔迈尔?”福伊尔挣扎着在床上坐起来。“不,不是。是福伊尔。格利弗·福伊尔,那是我的名字,我。”
男仆咬了咬嘴唇。
“请稍等,先生……”他走出去喊了一声。然后他低声说了几句。一个穿着白色衣服的可爱女孩跑进卧室,坐在床边。她握住福伊尔的手,凝视着他的眼睛。她脸上带着忧虑。
“亲爱的,亲爱的,亲爱的,”她低语道。“你不会又要开始那一套了吧,是吗?医生发誓你已经好了。”
“又开始什么?”
“就是那些关于你是普通水手的格利弗·福伊尔的胡话,还有——”
“我就是格利弗·福伊尔。那是我的名字,格利弗·福伊尔。”
“亲爱的,你不是。那只是你几周来的幻觉。你工作过度,喝太多酒了。”
“我一辈子都是格利弗·福伊尔,我。”
“是的,我知道,亲爱的。在你看来是这样。但你不是。你是杰弗里·福尔迈尔。那个杰弗里·福尔迈尔。你是——哦,告诉你有什么用呢?穿好衣服,我的爱人。你得下楼。你办公室的人都急疯了。”
福伊尔任由男仆给他穿衣,茫然地下了楼。那个显然爱慕他的漂亮女孩领着他穿过一个巨大的画室,里面堆满了画桌、画架和半成品画布。她带他进入一个巨大的大厅,里面摆满了办公桌、文件柜、股票行情自动收录器,还有职员、秘书和办公室人员。他们进入一个高大的实验室,里面堆满了玻璃和铬合金器皿。燃烧器闪烁嘶嘶作响;鲜艳的液体冒泡翻滚;空气中弥漫着有趣的化学品和奇特实验的宜人气味。
“这都是什么?”福伊尔问道。
女孩让福伊尔坐在一张豪华的扶手椅上,旁边是一张巨大的办公桌,桌上堆满了有趣的纸张,上面潦草地写着迷人的符号。在一些纸上,福伊尔看到了“杰弗里·福尔迈尔”这个名字,用一种威严而权威的签名潦草地写着。
“这儿有点疯狂的误会,就是这样,”福伊尔开始说。
女孩让他安静下来。“里根医生来了。他会解释的。”
一位令人印象深刻的绅士,举止干练而令人安心,走到福伊尔面前,摸了摸他的脉搏,检查了他的眼睛,满意地点点头。
“好,”他说。“非常好。你快要完全康复了,福尔迈尔先生。现在请你听我说一会儿,好吗?”
福伊尔点点头。
“你对过去一无所知。你只有一个虚假的记忆。你过度劳累了。你是个重要人物,对你的要求太多了。一个月前你开始酗酒——不,不,否认是没用的。你喝酒了。你迷失了自我。”
“我——”
“你开始相信自己不是著名的杰夫·福尔迈尔。一种幼稚的逃避责任的尝试。你想象自己是一个叫福伊尔的普通太空人。格利弗·福伊尔,是吗?还有一个奇怪的编号……”
“格利弗·福伊尔。AS:I27/I27:006。但那是我。那是——”
“那不是你。这才是你。”里根医生挥手指向他们能透过透明玻璃墙看到的有趣的办公室。
“只有当我们帮助你抛弃那个太空人的梦境时,你才能找回真实的记忆。”里根医生向前倾身,他擦得锃亮的眼镜闪烁着催眠般的光芒。“详细地重建你那虚假的记忆,我会将其摧毁。你想象中你把‘诺玛德’号飞船留在哪里了?你是如何逃脱的?你想象中‘诺玛德’号现在在哪里?”
福伊尔在这浪漫迷人的景象前动摇了,这景象似乎触手可及。
“在我看来,我把诺玛德号留在了——”他突然停了下来。
一张魔鬼般的脸从里根医生眼镜反射的高光中凝视着他……一张可怕的老虎面具,扭曲的额头上刻着“诺玛德”。福伊尔站了起来。
“骗子!”他低吼道。“这是真的,我。这儿才是假的。发生在我身上的事是真的。我是真的,我。”
索尔·达格纳姆走进实验室。“好了,”他喊道。“收工。失败了。”实验室、办公室和画室里熙熙攘攘的场景结束了。演员们悄悄地消失了,没有再看福伊尔一眼。
达格纳姆向福伊尔露出致命的微笑。“很顽强,是吧?你真是独一无二。我叫索尔·达格纳姆。我们有五分钟谈谈。到花园里来。”
治疗大楼顶部的镇静花园是治疗规划的一大胜利。每一个视角、每一种色彩、每一条轮廓都被设计用来平息敌意、舒缓抵抗、融化愤怒、驱散歇斯底里、支撑忧郁和沮丧。
“坐下,”达格纳姆说着,指着一个水池边的长凳,水池里清澈的水叮咚作响。“我得四处走走。不能离你太近。我‘发热’了。你知道那是什么意思吗?”
福伊尔愠怒地摇了摇头。
达格纳姆双手捧住一朵兰花火焰般的花朵,在那里停了一会儿。“看着那朵花,”他说。“你会看到的。”他沿着小路走上去,突然转过身。“当然,你说得对。发生在你身上的一切都是真的……只是到底发生了什么?”
“滚蛋,”福伊尔低吼道。
“你知道吗,福伊尔,我挺佩服你的。”
“滚蛋。”
“以你自己原始的方式,你既有独创性又有胆量。你是克罗马农人,福伊尔。我一直在调查你。你在普雷斯蒂安船坞扔的那颗炸弹很漂亮,而且你为了凑钱和材料差点毁了综合医院。”达格纳姆屈指数着。“你洗劫了储物柜,偷了盲人病房的东西,从药房偷了药品,从实验室备品室偷了仪器。”
“滚蛋,你。”
“但是你对普雷斯蒂安有什么不满?你为什么要炸毁他的船坞?他们告诉我你闯了进去,像个科曼奇印第安人一样在船坞里横冲直撞。你到底想干什么,福伊尔?”
“滚蛋。”
达格纳姆笑了。“如果我们要聊天,”他说,“你得把你的话说完。你的对话变得单调了。诺玛德号怎么了?”
“我不知道诺玛德号,什么都不知道。”
“那艘船最后一次报告是在七个多月前。然后……无影无踪。你是唯一的幸存者吗?这段时间你都在干什么?装饰你的脸吗?”
“我不知道诺玛德号,什么都不知道。”
“不,不,福伊尔,那不行。你脸上纹着‘诺玛德’。新纹的。情报部门核查发现你起航时就在‘诺玛德’号上。福伊尔,格利弗:AS:128/127:006,三级机械师助手。好像这一切还不足以让情报部门抓狂,你还乘坐一艘失踪了五十年的私人发射艇回来。伙计,你正在反应堆里被烤着呢。情报部门想要所有这些问题的答案。你应该知道中央情报局是如何从人们身上榨取答案的。”
福伊尔吃了一惊。达格纳姆点点头,看到他的观点深入人心。“所以我认为你会听从理智。我们需要信息,福伊尔。我试图骗取它;承认。我失败了,因为你太顽强了;承认。现在我提供一个公平的交易。如果你合作,我们会保护你。如果你不合作,你将在情报实验室里度过五年,信息会被一点点地从你身上割下来。”
并非屠宰的前景吓坏了福伊尔,而是失去自由的想法。一个人必须自由才能筹集资金,再次找到沃加;才能撕裂、扯碎、掏空沃加。
“什么样的交易?”他问道。
“告诉我们诺玛德号发生了什么,以及你把它留在哪里了。”
“为什么,伙计?”
“为什么?因为打捞物,伙计。”
“没什么可打捞的。她就是个残骸,仅此而已。”
“即使是残骸也有打捞价值。”
“你的意思是你愿意喷射一百万英里去捡碎片?别开玩笑了,伙计。”
“好吧,”达格纳姆恼怒地说。“还有货物。”
“她被劈开了。没剩下货物。”
“那是你不知道的货物,”达格纳姆秘密地说。“‘诺玛德’号正在向火星银行运送白金条。银行每隔一段时间就必须调整账户。通常情况下,行星间的贸易足以在纸面上平衡账户。战争打乱了正常贸易,火星银行发现普雷斯蒂安欠他们两千多万信用点,除了实际交付外没有办法拿到钱。普雷斯蒂安正用‘诺玛德’号上的白金条交付这笔钱。它锁在事务长的保险箱里。”
“两千万,”福伊尔低语道。
“上下差个几千。船投了保,但这只意味着承保人博内斯和尤伊格公司拥有打捞权,他们比普雷斯蒂安更难对付。不过,你会得到一笔奖励。比如说……两万信用点。”
“两千万,”福伊尔又低语道。
“我们假设一艘外围卫星袭击舰在航线上某处追上了‘诺玛德’号并攻击了她。他们不可能登船抢劫,否则你不会被留下活口。这意味着事务长的保险箱仍然——你在听吗,福伊尔?”
但福伊尔没有在听。他看到的是两千万……不是两万……两千万白金条,那是通往沃加的宽阔大道。不再需要从储物柜和实验室里小偷小摸;两千万唾手可得,然后摧毁沃加。
“福伊尔!”
福伊尔醒了过来。他看着达格纳姆。“我不知道诺玛德号,什么都不知道,”他说。
“你现在又怎么了?为什么又装傻了?”
“我不知道诺玛德号,什么都不知道。”
“我提供的是公平的报酬。一个太空人用两万信用点可以疯狂挥霍一阵子……一年的挥霍。你还想要什么?”
“我不知道诺玛德号,什么都不知道。”
“要么是我们,要么是情报局,福伊尔。”
“你也不那么急着让他们抓到我,否则你就不会费这么多周折了。但反正也没用。我不知道诺玛德号,什么都不知道。”
“你这个混——”达格纳姆试图压抑怒火。他向这个狡猾的原始生物透露得稍微多了点。“你说得对,”他说。“我们不急着让情报局抓到你。但我们已经做好了自己的准备。”他的声音变硬了。“你以为你能装傻,对抗我们。你以为你能让我们对诺玛德号束手无策。你甚至想着你能抢在我们前面去打捞。”
“不,”福伊尔说。
“现在听好了。我们在纽约有个律师等着。他准备对你提起刑事诉讼,罪名是海盗行为;太空海盗、谋杀和抢劫。我们要把所有罪名都安在你头上。普雷斯蒂安会在二十四小时内让你定罪。如果你有任何犯罪记录,那就意味着脑叶切除术。他们会打开你的颅骨,烧掉你一半的大脑,阻止你再次琼特。”达格纳姆停下来,严厉地看着福伊尔。当福伊尔摇头时,达格纳姆继续说道。——“如果你没有记录,他们会判你十年所谓的医疗。在我们这个开明的时代,我们不惩罚罪犯,我们治愈他们;而治愈比惩罚更糟。他们会把你藏在某个洞穴医院的黑洞里。你会被永久关在黑暗和单独监禁中,这样你就无法琼特出去。他们会装模作样地给你打针和治疗,但你会在黑暗中腐烂。你会待在那里腐烂,直到你决定开口。我们会让你永远待在那里。所以下定决心吧。”
“沃加,我要让你死得惨烈。”
“我什么都不知道,关于诺玛德号。什么都不知道!”福伊伊尔说。
“好吧,”达格纳姆啐道。突然,他指向他曾用手捂住的那朵兰花。它已经枯萎腐烂。“这就是将要发生在你身上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