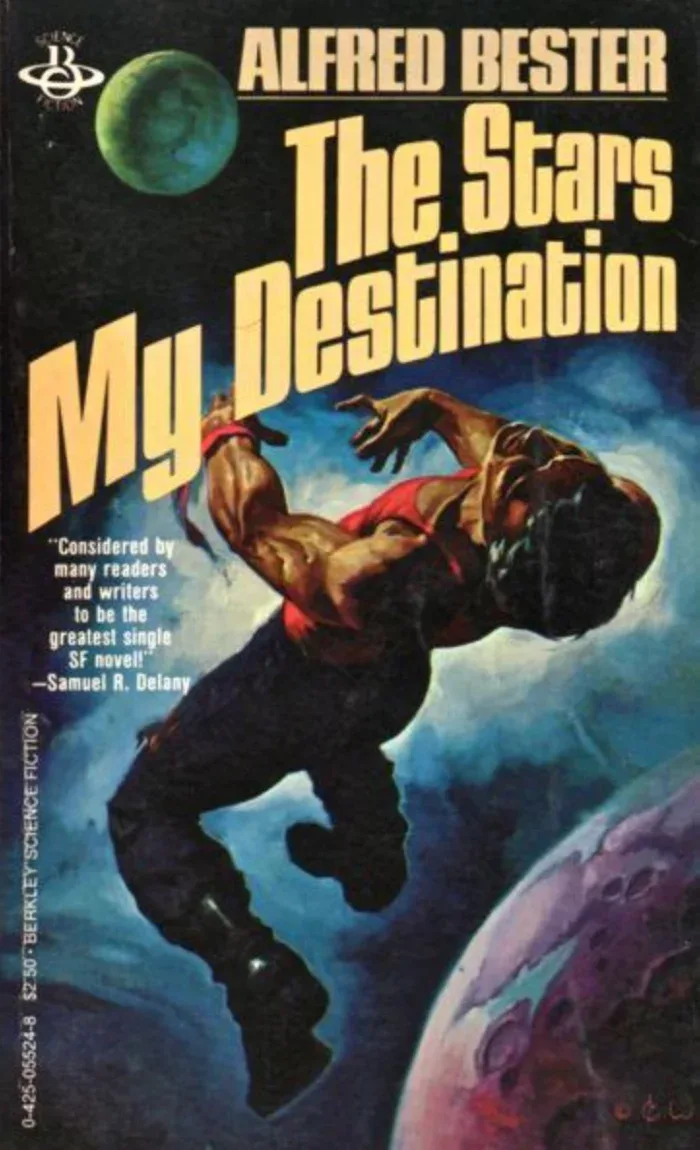第十六章
他的感官在普雷斯蒂安城堡象牙与黄金的星室中恢复了正常。视觉成为视觉,他看到了高大的镜子和彩色玻璃窗;金边图书馆里,人造人图书管理员站在梯子上。声音成为声音,他听到人造人秘书在路易十五式书桌旁敲打着手动记忆珠记录器。味觉成为味觉,他啜饮着机器人调酒师递给他的干邑白兰地。
他知道自己已是困兽犹斗,面临着人生的抉择。他无视敌人,审视着机器人调酒师脸上那永恒的光束,那经典的爱尔兰式笑容。
“谢谢,”福伊尔说。
“我的荣幸,先生,”机器人回答道,等待着下一个提示。
“天气不错,”福伊尔说道。
“总有某个地方天气晴朗,先生,”机器人光彩照人。
“糟糕的一天,”福伊尔说。
“总有某个地方天气晴朗,先生,”机器人回应道。
“天,”福伊尔说。
“总有某个地方天气晴朗,先生,”机器人说。
福伊尔转向其他人。“那就是我,”他说,指着机器人。“那就是我们所有人。我们空谈自由意志,但我们不过是反应……在规定轨道上的机械反应。所以……我在这里,我在这里,等待着反应。按下按钮,我就会跳起来。”
他模仿着机器人罐装的声音。“很乐意为您效劳,先生。”
突然,他的语气鞭笞着他们。“你们想要什么?”
他们不安地骚动起来,带着目的。福伊尔被烧伤,被打倒,被惩戒……然而他却正在掌控他们所有人。
“我们规定一下威胁,”福伊尔说。“如果我不……我将被绞死、车裂、分尸,在地狱受尽折磨……什么?你们想要什么?”
“我要我的财产,”普雷斯蒂安说着,冷冷地笑了笑。
“十八磅多一点的PyrE。是的。你出什么价?”
“我不出价,先生,我要求属于我的东西。”
杨-尤维尔和达格纳姆开始说话。福伊尔让他们安静下来。“一次按一个按钮,先生们。普雷斯蒂安现在正试图让我跳起来。”
他转向普雷斯蒂安。“再用力点,血和金钱,或者换个按钮。此刻你有什么资格提要求?”
普雷斯蒂安抿紧嘴唇。“法律……”他开始说。
“什么?威胁?”福伊尔笑了。“难道我会因为任何事而被吓倒吗?别傻了。用你除夕夜的方式跟我说话,普雷斯蒂安……毫无怜悯,毫无宽恕,毫无虚伪。”
普雷斯蒂安鞠躬,吸了口气,收起了笑容。“我给你权力,”他说。“收养你做我的继承人,成为普雷斯蒂安企业的合伙人,氏族和分支的首领。我们可以一起拥有世界。”
“用PyrE?”
“是的。”
“你的提议已知悉并拒绝。你愿意献出你的女儿吗?”
“奥利维亚?”
普雷斯蒂安呛住了,握紧了拳头。
“是的,奥利维亚。她在哪儿?”
“你这个败类!”普雷斯蒂安喊道。“肮脏……普通小偷……你竟敢……”
“你愿意用你的女儿换PyrE吗?”
“是的,”普雷斯蒂安回答道,声音几乎听不见。
福伊尔转向达格纳姆。“按下你的按钮,死神头颅,”他说。“如果讨论要在这个层面上进行……”
达格纳姆厉声说道:“正是如此。毫无怜悯,毫无宽恕,毫无虚伪。你出什么价?”
“荣耀。”
“啊?”
“我们不能提供金钱或权力。我们可以提供荣誉。格利弗·福伊尔,拯救内行星免于毁灭的人。我们可以提供安全。我们会抹去你的犯罪记录,给你一个光荣的名字,保证你在名人堂占有一席之地。”
“不,”吉斯贝拉·麦昆厉声打断道。“别接受。如果你想成为救世主,就毁掉这个秘密。不要把PyrE交给任何人。”
“PyrE是什么?”
“安静!”
达格纳姆厉声说道。
“这是一种仅凭思想就能引爆的热核炸药……通过意念致动,”吉斯贝拉说。
“什么思想?”
“任何想要引爆它的人的意愿,直接指向它。如果它没有被惰性铅同位素绝缘,这就会使它达到临界质量。”
“我叫你安静,”达格纳姆低吼道。
“如果大家都有机会争取他,我也想要我的机会。”
“这比理想主义更重要。”
“没有什么比理想主义更重要。”
“福伊尔的秘密是,”杨-尤维尔低声说道。“我知道PyrE现在相对来说是多么不重要。”
他对着福伊尔笑了笑。“谢菲尔德的法律助手无意中听到了你们在老圣帕特里克教堂那次小讨论的一部分。我们知道空间琼特的事。”
突然一片寂静。
“空间琼特,”达格纳姆惊呼道。“不可能。你不是认真的吧。”
“我是认真的。福伊尔证明了空间琼特并非不可能。他从一艘外围卫星袭击舰瞬移了六十万英里到诺玛德号的残骸。正如我所说,这远比PyrE重要得多。我想先讨论那件事。”
“每个人都在说他们想要什么,”罗宾·韦恩斯伯里慢慢地说。“你想要什么,格利弗·福伊尔?”
“谢谢,”福伊尔回答道。“我想受到惩罚。”
“什么?”
“我想被净化,”他用窒息的声音说道。烙印开始出现在他缠着绷带的脸上。“我想为我所做的一切付出代价,了结这笔账。我想摆脱我背负的这个该死的十字架……这个快要压断我脊椎的痛苦。我想回到古夫尔·马特尔。如果我罪有应得,我想要脑叶切除术……我知道我罪有应得。我想要——”
“你想要逃避,”达格纳姆打断道。“没有逃避。”
“我想要解脱!”
“不可能,”杨-尤维尔说。“你脑袋里锁着太多有价值的东西,不能因为脑叶切除术而丢失。”
“我们已经超越了像犯罪和惩罚这样简单幼稚的事情,”达格纳姆补充道。
“不,”罗宾反对道。“必须永远有罪恶和宽恕。我们永远无法超越那个。”
“利润与损失,罪恶与宽恕,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福伊尔笑了笑。
“你们都那么肯定,那么简单,那么一心一意。只有我一个人在怀疑。让我们看看你们到底有多肯定。你会放弃奥利维亚·普雷斯蒂安?给我,是的?你会把她交给法律吗?她是个杀人犯。”
普雷斯蒂安试图站起来,然后跌回椅子里。
“必须有宽恕,罗宾?你会宽恕奥利维亚·普雷斯蒂安吗?她谋杀了你的母亲和妹妹们。”
罗宾脸色苍白。杨-尤维尔试图抗议。
“外围卫星没有PyrE,尤维尔。谢菲尔德透露了这一点。你无论如何都会对他们使用它吗?你会让我的名字变成普遍的诅咒……像林奇和博伊科特一样吗?”
福伊尔转向吉斯贝拉。“你的理想主义会带你回古夫尔·马特尔服完你的刑期吗?还有你,达格纳姆,你会放弃她吗?让她走吗?”
他听着呐喊声,看着混乱的场面片刻,苦涩而克制。
“生活如此简单,”他说。“这个决定如此简单,不是吗?我该尊重普雷斯蒂安的财产权吗?行星的福祉?吉斯贝拉的理想?达格纳姆的现实主义?罗宾的良心?按下按钮,看着机器人跳起来。但我不是机器人,我是宇宙的一个怪胎……一个会思考的动物……我正试图看清穿过这片泥沼的道路。我该把PyrE交给世界,让它自我毁灭吗?我该教世界如何进行空间琼特,让我们把我们的怪胎秀从一个星系传播到另一个星系,遍及整个宇宙吗?答案是什么?”
调酒师机器人将调酒杯猛地摔过房间,发出一声响亮的碰撞声。在随之而来的惊讶寂静中,达格纳姆咕哝道:“该死!我的辐射又打扰了你的玩偶,普雷斯蒂安。”
“答案是肯定的,”机器人相当清晰地说。
“什么?”福伊尔吃惊地问道。
“你问题的答案是肯定的。”
“谢谢,”福伊尔说。
“我的荣幸,先生,”机器人回应道。“人首先是社会的一员,其次才是个人。你必须与社会同行,无论它选择毁灭与否。”
“完全失控了,”达格纳姆不耐烦地说。“关掉它,普雷斯蒂安。”
“等等,”福伊尔命令道。他看着刻在钢铁机器人脸上那光彩照人的笑容。“但社会可能如此愚蠢。如此混乱。你目睹了这次会议。”
“是的,先生,但您必须教导,而非命令。您必须教导社会。”
“进行空间琼特?为什么?为什么要伸向星星和星系?为了什么?”
“因为你还活着,先生。你还不如问:生命为何存在?不要问它。去活它。”
“完全疯了,”达格纳姆咕哝道。
“但很有趣,”杨-尤维尔低声说道。
“生命肯定不止于活着,”福伊尔对机器人说。
“那么请您自己去寻找吧,先生。不要因为您有疑虑就要求世界停止运转。”
“为什么我们不能一起前进?”
“因为你们都不同。你们不是旅鼠。总得有人带头,并希望其他人会跟随。”
“谁带头?”
“那些必须这样做的人……被驱使的人,被迫的人。”
“怪人。”
“你们都是怪胎,先生。但你们一直都是怪胎。生命本身就是个怪胎。那是它的希望和荣耀。”
“非常感谢。”
“我的荣幸,先生。”
“你挽救了局面。”
“总有某个地方天气晴朗,先生,”机器人光彩照人。然后它发出嘶嘶声,叮当作响,然后崩溃了。
福伊尔转向其他人。“那东西说得对,”他说,“而你们错了。我们是谁,我们中的任何一个,能为世界做决定?让世界自己做决定吧。我们是谁,能对世界保守秘密?让世界知道并自己决定吧。到老圣帕特里克教堂来。”
他瞬移了;他们跟着。方形街区仍然被封锁着,到这时已经聚集了庞大的人群。许多鲁莽和好奇的人正瞬移进冒烟的废墟,以至于警察设立了一个保护性感应场来阻止他们。即便如此,顽童、猎奇者和不负责任的人仍然试图瞬移进废墟,结果被感应场烧伤,尖叫着离开。
杨-尤维尔发出信号,力场关闭了:福伊尔穿过滚烫的瓦砾,来到大教堂东墙,墙体还剩下十五英尺高。他摸索着冒烟的石头,按压并撬动。传来一阵研磨的隆隆声,一块三乘五英尺的部分震开了,然后卡住了。福伊尔抓住它,用力拉。那部分颤抖着;然后烤焦的铰链坍塌了,石板坍塌。
两个世纪前,当有组织的宗教被废除,各种信仰的正统信徒被迫转入地下时,一些虔诚的灵魂在老圣帕特里克教堂建造了这个秘密壁龛,并将其变成了祭坛。十字架的金色仍然闪耀着永恒信仰的光辉。在十字架脚下放着一个惰性铅同位素制成的小黑盒子。
“这是预兆吗?”福伊尔喘着气说。“这是我想要的答案吗?”
在任何人能抓住它之前,他抢走了那个沉重的保险箱:他瞬移了一百码,来到面向第五大道的大教堂台阶残骸处。在那里,他在众目睽睽之下打开了保险箱。知道其内容物真相的情报人员发出一片惊愕的喊叫声。
“福伊尔!”达格纳姆喊道。
“看在上帝的份上,福伊尔!”杨-尤维尔喊道。
福伊尔取出一块PyrE块,颜色像碘晶体,大小像香烟……一磅超钚同位素的固溶体。
“PyrE!”他对着人群咆哮道。“拿着!留着!这是你们的未来。PyrE!”
他把那块东西扔进人群,对着身后咆哮道:“旧金山。俄罗斯山平台。”
他瞬移圣路易斯-丹佛到旧金山,到达俄罗斯山平台,那里是下午四点,街道上挤满了迟到的购物瞬移者。
“PyrE!”
福伊尔轰鸣着。他魔鬼般的脸庞发出血红色的光芒。他是一个骇人的景象。“PyrE。它是你们的。让他们告诉你们它是什么。”
“诺姆!”他对着追兵喊道,追兵已经赶到,然后瞬移了。
诺姆正是午餐时间,伐木工们正从锯木厂瞬移下来享用牛排和啤酒,他们被那个虎脸男人惊呆了,他把一块一磅重的碘色合金块扔到他们中间,用贫民窟的语言喊道:“PyrE!你听到我了吗,伙计?你听我说,你。PyrE!别瞎猜,你。让他们告诉你PyrE是什么,就是这样!”
对着紧随其后瞬移进来的达格纳姆、杨-尤维尔和其他人,他总是晚了几秒钟,喊道:“东京。皇居平台!”
他开枪前一瞬间消失了。
东京正值清晨九点,天气清爽宜人,皇居平台旁鲤鱼池周围早高峰的人群被一个虎脸武士惊呆了,他出现并向他们投掷了一块奇特的金属块和令人难忘的告诫。
福伊尔继续前往曼谷,那里正下着倾盆大雨;到了德里,季风肆虐……在他的疯狂追逐中始终被追赶着。在巴格达是凌晨三点,夜总会的人群和酒吧流连者——他们总是在世界各地领先关门时间半小时——被他酒精般地欢呼着。在巴黎和伦敦又是午夜,香榭丽舍大街和皮卡迪利广场的人群被福伊尔的出现和激情的劝告激起了热情。
福伊尔带领追兵在五十分钟内绕地球四分之三圈后,在伦敦让他们追上了。他任由他们把他打倒在地,从他怀里夺走I.L.I.保险箱,数了数剩余的PyrE块,然后砰地一声关上保险箱。
“剩下的足够打一场战争了。足够毁灭……毁灭……如果你敢的话。”他歇斯底里地笑着,抽泣着,带着胜利的喜悦。“数百万用于防御,但一分钱也不用于生存。”
“你意识到你做了什么吗,你这个该死的杀人犯?”达格纳姆喊道。
“我知道我做了什么。”
“九磅PyrE散落在世界各地!一个念头我们就——我们怎么能在不告诉他们真相的情况下把它弄回来?看在上帝的份上,尤,把那群人挡回去。别让他们听到这个。”
“不可能。”
“那我们瞬移吧。”
“不,”福伊尔咆哮道。“让他们听到这个。让他们听到一切。”
“你疯了,伙计。你把上了膛的枪递给了孩子们。”
“别把他们当孩子对待,他们就不会像孩子一样行事。你他妈是谁来扮演监护人?”
“你在说什么?”
“别把他们当孩子对待。给他们解释上膛的枪。把一切都公开出来。”福伊尔凶狠地笑了。“我结束了世界上最后一次星室会议。我把最后一个秘密彻底公开了。从现在起不再有秘密……不再告诉孩子们什么对他们最好……让他们都长大吧。是时候了。”
“天哪,他疯了。”
“我疯了吗?我把生与死交还给了那些活着和死去的人。普通人被像我们这样的驱使者……强迫症患者……无法克制自己鞭打世界的老虎……鞭打和领导得够久了。我们都是老虎,我们三个,但我们他妈的是谁,就因为我们有强迫症就能为世界做决定?让世界自己选择生与死吧。我们为什么要背负这个责任?”
“我们没有背负,”杨-尤维尔平静地说。“我们是被驱使的。我们被迫承担起普通人推卸的责任。”
“那就让他别再推卸了。让他别再把他的责任和罪恶扔到第一个冲上来抢夺的怪胎肩上。难道我们要永远做世界的替罪羊吗?”
“该死的你!”达格纳姆怒吼道。“难道你不明白你不能信任人民吗?他们对自己不够了解。”
“那就让他们学习或者死亡。我们都在一起。让我们一起生活或者一起死亡。”
“你想在他们的无知中死去吗?你必须想出我们如何在不把一切都彻底公开的情况下把那些块状物弄回来。”
“不。我相信他们。在我变成老虎之前,我就是他们中的一员。如果像我一样被踢醒,他们都能变得不平凡。”
福伊尔抖了抖身体,突然瞬移到了皮卡迪利广场柜台上方五十英尺处的爱神厄洛斯青铜头像上。他摇摇欲坠地栖息着,咆哮道:
“听我说,你们所有人!听着,伙计!要布道了,我。听好了,你!”
他得到了轰鸣的回应。
“你们这些猪,你们。你们像猪一样腐烂,仅此而已。你们拥有最多,却用得最少。听到我了吗,你?心里有一百万,却只花几便士。心里有天才,却想着疯事。心里有颗心,却感觉空虚。你们所有人。每一个你……”
他被嘲笑了。他继续说着,带着被附身者歇斯底里的激情。
“得打一仗才能让你们花钱。得遇到困境才能让你们思考。得遇到挑战才能让你们伟大。其余时间你们懒洋洋地坐着,你们。猪,你们!好吧,该死的你们!我挑战你们,我。要么死,要么活得伟大。要么把自己炸到基督那里去,要么来找我,格利弗·福伊尔,我让你们伟大。我给你们星星。我让你们成为男人!”
他沿着时空测地线向上瞬移到一个别处和一个别时。他到达时一片混乱。他在一个不稳定的准现在悬停了片刻,然后跌回混乱之中。
“可以做到,”他想。“必须做到。”
他再次瞬移,像一支燃烧的长矛从未知投向未知,又一次跌回了准空间和准时间的混乱之中。他迷失在虚无之中。
“我相信,”他想。“我有信念。”
他再次瞬移,又失败了。
“信仰什么?”他在混沌中漂浮着,自问。
“信仰信念本身,”他自答。“不必非要有信仰的对象。只需要相信某处存在值得信仰的东西。”
他最后一次瞬移,他愿意相信的力量将他随机目的地的准现在转化为了真实的……
现在:猎户座的参宿七,燃烧着蓝白色,距离地球五百四十光年,亮度是太阳的一万倍,一个能量的大锅,被三十七颗巨大的行星环绕……福伊尔悬挂在太空中,冰冷而窒息,面对着他所信仰、但仍然难以想象的不可思议的命运。他在太空中悬挂了耀眼的一瞬间,像地球生命黎明时期第一个从海里爬出来、在原始海滩上喘气的有鳃生物一样无助,一样惊奇,却又一样不可避免。
他进行了空间琼特,将准现在变成了……
现在:天琴座的织女星,一颗距离地球二十六光年的A0型恒星,燃烧得比参宿七更蓝,没有行星,但被成群燃烧的彗星环绕,它们气态的尾巴在蓝黑色的天幕上闪烁……
他又一次把现在变成了
现在:船底座的老人星,黄如太阳,巨大,在寂静的太空荒原中雷鸣般响亮,最终被一个曾经有鳃的生物入侵。这个生物悬挂着,在宇宙的海滩上喘气,离死亡比生命更近,离未来比过去更近,在广阔世界尽头的十里格之外。它惊奇地看着尘埃、流星和微粒组成的团块,像土星环一样,以土星轨道的宽度环绕着老人星,形成一个宽阔平坦的环……
现在:金牛座的毕宿五,一对恒星中一颗巨大的红星,其十六颗行星围绕着它们旋转的父母编织着高速椭圆轨道。他以越来越强的信心穿越时空……
现在:天蝎座的心宿二,一颗距离地球二百五十光年的MI型红巨星,像毕宿五一样成对,被二百五十颗水星大小、伊甸园气候的小行星环绕……
最后……
现在:他回到了“诺玛德”号上。
女孩莫伊拉在“诺玛德”号上的工具柜里找到了他,他蜷缩成一个紧密的胎儿姿势,脸颊凹陷,眼睛里燃烧着神圣的启示。尽管小行星早已修复并变得气密,福伊尔仍然重复着几年前那个赋予他新生的危险生存的动作。
但现在他沉睡着,冥想着,消化并包容着他所学到的壮丽。他从沉思中醒来,进入恍惚状态,漂出工具柜,用盲目的眼睛经过莫伊拉,擦过那个敬畏地退到一边跪下的女孩。他漫步穿过空荡的通道,回到工具柜的子宫。他又蜷缩起来,迷失了自我。
她碰了他一下;他一动不动。她念出了曾印在他脸上的名字。他没有回答。她转身逃向小行星内部,逃向约瑟夫统治的至圣所。
“我丈夫回到我们这里来了,”莫伊拉说。
“你丈夫?”
“那个毁灭我们的神人。”约瑟夫的脸因愤怒而阴沉下来。
“他在哪里?带我去!”
“你不会伤害他吧?”
“所有债务都必须偿还。带我去。”
约瑟夫跟着她来到“诺玛德”号上的工具柜,专注地凝视着福伊尔。他脸上的愤怒被惊奇取代了。他触摸了福伊尔并对他说话;仍然没有回应。
“你惩罚不了他,”莫伊拉说。“他快死了。”
“不,”约瑟夫平静地回答。“他在做梦。我,一个祭司,知道这些梦。很快他就会醒来,向我们,他的人民,宣读他的思想。”
“然后你会惩罚他。”
“他已经在自己身上找到了,”约瑟夫说。
他安顿在工具柜外面,准备等待觉醒。女孩莫伊拉跑上蜿蜒的走廊,几分钟后拿着一个银盆的温水和一个银托盘的食物回来。她温柔地给福伊尔洗澡,然后把托盘放在他面前作为祭品。然后她安顿在约瑟夫旁边……在世界旁边……准备等待觉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