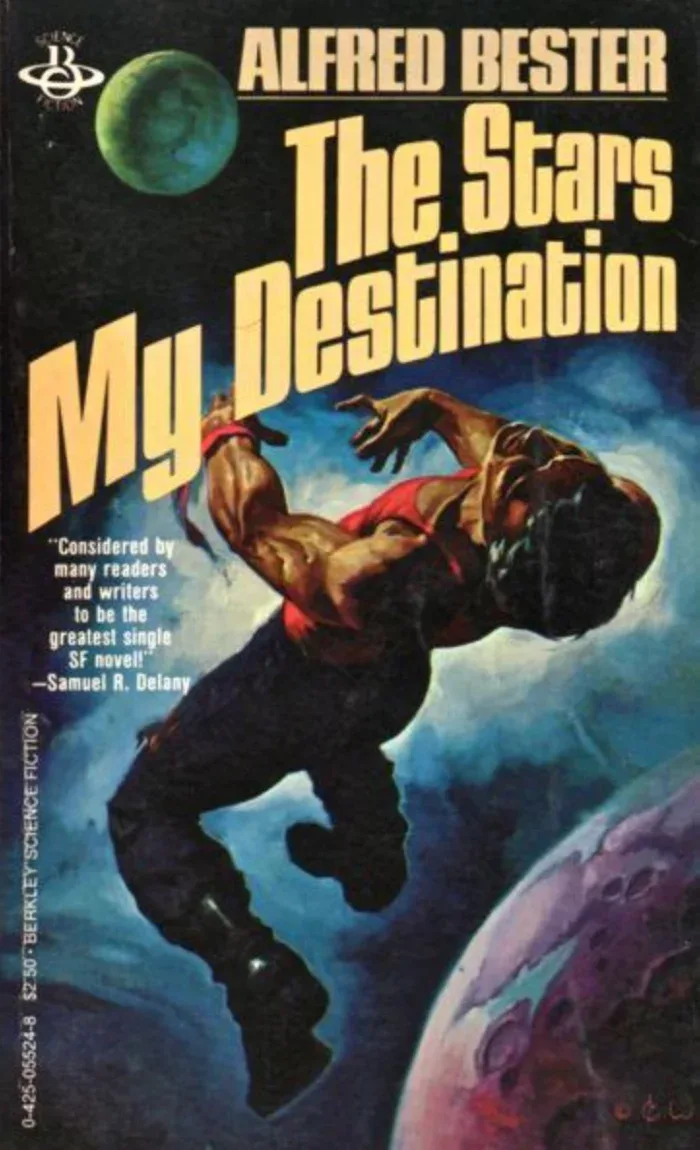第十五章
如同池塘中扩散的涟漪,意志和观念散播开来,搜寻着、触碰着、触发着PyrE那精妙的亚原子扳机。思想找到了粒子、尘埃、烟雾、蒸汽、微粒、分子。意志和观念改变了它们所有。
在西西里岛,弗兰科·托雷博士花了整整一个月时间,试图解开一块PyrE的秘密,残留物和沉淀物被倒入通往大海的下水道。许多个月来,地中海的海流将这些残留物漂移过海底。瞬间,一座高达五十英尺的驼峰状水丘追溯着这些轨迹,向东北延伸至撒丁岛,向西南延伸至的黎波里。微秒之内,地中海表面隆起,形成一条巨大蚯蚓扭曲的铸型,缠绕着潘泰莱里亚岛、兰佩杜萨岛、利诺萨岛和马耳他岛。
一些残留物被烧掉了;随着烟雾和蒸汽升入烟囱,漂流了数百英里后才沉降下来。这些微小的颗粒在摩洛哥、阿尔及利亚、利比亚和希腊最终沉降的地方,以令人目眩的针尖大小、强度难以置信的爆炸显示了它们的存在。而一些仍然漂浮在平流层的微粒,则以如同白昼星辰般的明亮闪光显露了它们的存在。
在德克萨斯州,约翰·曼特利教授对PyrE有着同样令人困惑的经历,大部分残留物都顺着一口废弃油井的井筒流下,那口井也用来容纳放射性废物。一个深层地下水位吸收了大部分物质,并将其缓慢地扩散到大约十平方英里的区域。十平方英里的德克萨斯平地像搓板一样震动起来。一个巨大的未开发天然气矿藏终于找到了出口,尖啸着冲上地表,飞溅的石头产生的火花将其点燃成一个高达两百英尺的轰鸣火炬。
一毫克PyrE沉积在一张早已被丢弃、遗忘、在废纸回收运动中收集起来、最终被制成活字模具的滤纸圆盘上,摧毁了《格拉斯哥观察家报》的整个深夜版。一小片PyrE溅在一件早已被改成碎布纸的实验室罩衫上,毁掉了一封夏普内尔夫人写的感谢信,并在此过程中额外摧毁了一吨头等邮件。
一个不小心浸入PyrE酸溶液的衬衫袖口,连同衬衫早已被遗弃,现在被一个劫掠琼特者穿在他的貂皮套装下面,像一次火焰截肢一样炸掉了那个劫掠琼特者的手腕和手。一毫克PyrE,仍然附着在一个以前用作烟灰缸的蒸发皿上,点燃了一场大火,烧焦了某个名叫贝克的、经营怪胎和供应畸形人的办公室。
行星的纵横各处,都发生了孤立的爆炸、连锁的爆炸、火线的轨迹、火的点点星光、天空中的流星闪光,巨大的坑洞和狭窄的通道,在地球上被犁开,在地球上爆炸,从地球上喷涌而出。仿佛一位愤怒的上帝再次用火与硫磺降临到祂的子民身上。
在老圣帕特里克教堂,将近十分之一克的PyrE暴露在外。其余的则被封存在惰性铅同位素保险箱内,免受意外和故意的意念点燃。由那十分之一克产生的耀眼能量爆炸炸毁了墙壁,震裂了地板,仿佛一场内部地震使建筑剧烈震动。扶壁支撑了柱子一瞬间,然后隆隆作响。塔楼、尖顶、柱子、扶壁和屋顶轰然坍塌,形成一场雷鸣般的雪崩,悬停在张开大口的地面坑洞上方,形成一个纠缠、危险的平衡状态。一阵风,一次遥远的震动,坍塌就会继续,直到坑洞被粉碎的瓦砾填满。爆炸产生的星辰般的热量点燃了一百处火焰,融化了坍塌屋顶上古老厚重的铜。如果再多一毫克PyrE暴露在爆炸中,热量会足以立刻蒸发金属。然而,它只是发出白炽的光芒,开始流动。它从坍塌屋顶的残骸上流下,开始向下搜寻穿过杂乱的石头、铁、木头和玻璃,像某种巨大的熔化模具爬行穿过缠绕的网。
达格纳姆和杨-尤维尔几乎同时到达。片刻之后,罗宾·韦恩斯伯里出现,接着是吉斯贝拉·麦昆。十几名情报人员和六名达格纳姆信使随同普雷斯蒂安的琼特卫队和警察一起抵达。他们在燃烧的街区周围形成了一条警戒线,但观众很少。除夕夜袭击的冲击之后,那一次爆炸吓得半个纽约又一次疯狂地琼特逃生。
火灾的喧嚣声骇人听闻,大量摇摇欲坠的残骸发出的沉重摩擦声令人不安。每个人都不得不大声喊叫,却又害怕震动。杨-尤维尔对着达格纳姆的耳朵咆哮着关于福伊尔和谢菲尔德的消息。
达格纳姆点点头,露出他那致命的微笑。“我们得进去,”他喊道。
“防火服,”杨-尤维尔喊道。
他消失了,又带着两套白色灾难救援队的防火服出现。看到这些,罗宾和吉斯贝拉开始歇斯底里地大声反对。两个男人没理她们,穿上惰性同位素盔甲,小心翼翼地爬进地狱般的火场。
在老圣帕特里克教堂内部,仿佛一只巨大的手搅动了一堆木头、石头和金属的 log-jam。熔化的铜舌爬行穿过每一个缝隙,缓慢向下流动,点燃木头,弄碎石头,弄碎玻璃。铜流动的地方只是发光,但倾泻的地方则飞溅着耀眼的白热金属液滴。
在原木堆下方,一个黑色的坑洞张开大口,那里曾是大教堂的地板。爆炸震裂了石板,露出了建筑深处的地窖、地下室和拱顶。这些地方也堆满了石头、横梁、管道、电线、四英里马戏团帐篷的残骸的纠结;所有这些都被小火苗断断续续地照亮。然后第一滴铜液滴落到坑洞里,用明亮的熔化飞溅照亮了它。
达格纳姆拍了拍杨-尤维尔的肩膀以引起他的注意,然后指了指。坑洞半腰处,在纠缠的混乱中躺着雷吉斯·谢菲尔德的尸体,被爆炸撕裂成了四块。杨-尤维尔拍了拍达格纳姆的肩膀,指了指。几乎在坑洞底部躺着格利弗·福伊尔,当炽热飞溅的熔铜照亮他时,他们看到他动了一下。两个男人立刻转身爬出大教堂商量对策。
“他活着。”
“这怎么可能?”
“我能猜到。你看到他附近那些帐篷碎片了吗?肯定是在大教堂另一端发生了一次奇怪的爆炸,中间的帐篷缓冲了福伊尔。然后他在其他东西砸到他之前掉进了地板下面。”
“我信这个。我们得把他弄出来。他是唯一知道PyrE在哪儿的人。”
“它会不会还在这里……没爆炸?”
“如果它在I.L.I.保险箱里,是的。那种东西对任何东西都是惰性的。现在别管那个了。我们怎么把他弄出来?”
“嗯,我们不能从上面往下弄。”
“为什么不?”
“这不是很明显吗?一步踏错,整个烂摊子就会塌下来。”
“你看到那铜水流下来了吗?”
“天哪,是的!”
“嗯,如果我们十分钟内不把他弄出来,他就会掉进一池熔化的铜水里。”
“我们能做什么?”
“我有个长线赌注。”
“什么?”
“街对面旧R.C.A.大楼的地窖和圣帕特里克教堂的一样深。”
“然后呢?”
“我们下去,试着打通。也许我们能从底部把福伊尔拉出来。”
一队人闯入了废弃并封锁了两代人的旧R.C.A.大楼。他们下到地窖拱廊,那里是几个世纪前零售商店坍塌的博物馆。他们找到了古老的电梯井,从中坠入充满电气装置、供暖设备和制冷系统的地下室。他们下到集水井地窖,齐腰深的水来自史前曼哈顿岛的溪流,那些溪流至今仍在覆盖它们的街道下流动。
当他们涉水穿过集水井地窖,向东北方向移动以到达圣帕特里克教堂拱顶对面时,他们突然发现前方漆黑的黑暗被火焰的闪烁照亮了。达格纳姆大喊一声,向前扑去。打开圣帕特里克教堂地下室的爆炸震裂了它的拱顶和R.C.A.大楼拱顶之间的隔墙。透过石头和泥土上一个锯齿状的裂口,他们可以窥视到地狱的底部。
五十英尺内是福伊尔,被困在一个由扭曲横梁、石头、管道、金属和电线组成的迷宫中。他被头顶上咆哮的光芒和周围断断续续的火焰照亮着。他的衣服着火了,脸上青紫的纹身清晰可见。他虚弱地移动着,像一只困在迷宫里困惑的动物。
“我的天!”
杨-尤维尔惊呼道。“燃烧的人!”
“什么?”
“我在西班牙阶梯上看到的那个燃烧的人。现在别管那个了。我们能做什么?”
“当然是进去。”
一团明亮的白色铜液突然渗出下来,靠近福伊尔,溅落在他下方十英尺处。紧接着是第二滴,第三滴,一股缓慢稳定的细流。一个水池开始形成。达格纳姆和杨-尤维尔封好盔甲的面罩,爬过隔墙的缺口。经过三分钟痛苦的挣扎,他们意识到无法穿过迷宫到达福伊尔。迷宫从外面锁住了,但从里面没有锁。达格纳姆和杨-尤维尔退后商量。
“我们到不了他那里,”达格纳姆喊道,“但他能出来。”
“怎么出来?他显然不能琼特,否则他就不会在这里了。”
“不。他能爬。看。他向左,然后向上,反转,沿着那根横梁转弯,从它下面滑过去,然后穿过那堆电线。电线推不进去,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到不了他那里,但它可以向外推,这就是他能出来的原因。这是一扇单向门。”
熔化的铜水池爬行向上靠近福伊尔。
“如果他再不出来,他会被活活烤死。”
“我们得把他喊出来……告诉他该怎么做。”
男人们开始喊叫:“福伊尔!福伊尔!福伊尔!”
迷宫里燃烧的人继续虚弱地移动着。嘶嘶作响的铜水倾泻而下,速度加快了。
“福伊尔!向左转。你能听到我吗?福伊尔!向左转,然后爬上去。然后——福伊尔!”
“他没在听。福伊尔!格利弗·福伊尔!你能听到我们吗?”
“派吉兹来。也许他会听她的。”
“不,罗宾。她会心灵发送。他必须听。”
“但她会做吗?救他,救所有这些人?”
“她必须做。这比仇恨更重要。这是世界上遇到过的最该死的大事。我去叫她。”
杨-尤维尔开始向外爬。达格纳姆拦住了他。
“等等,尤。看看他。他在闪烁。”
“闪烁?”
“看!他……像萤火虫一样闪烁着。看!现在你看到他,现在又看不到了。”
福伊尔的身影快速地出现、消失、再出现,如同火焰陷阱中捕获的萤火虫。“他现在在做什么?他想做什么?发生了什么?”
他试图逃跑。像一只被困的萤火虫,或某种被赤裸灯塔炽热火盆困住的海鸟,他疯狂地扑打着……一个焦黑、燃烧的生物,冲撞着未知。
声音以奇怪图案的光的形式呈现在他眼前。他看到自己被喊出的名字以生动的节奏显现:
福伊尔 福伊尔 福伊尔
福伊尔 福伊尔 福伊尔
福伊尔 福伊尔 福伊尔
福伊尔 福伊尔 福伊尔
福伊尔 福伊尔 福伊尔
福伊尔 福伊尔 福伊尔
运动以声音的形式呈现给他。他听到了火焰的扭动声,他听到了烟雾的旋转声,他听到了闪烁、嘲弄的阴影声……全都在用奇怪的语言震耳欲聋地说着:
“布鲁·加尔·瓦乌·杰尔马金?”蒸汽问道。
“阿莎。阿莎,利特-基特-迪特-齐特。姆吉德,”快速的影子回答道。
“哦哦哦。啊啊啊。嘻嘻嘻。嗞嗞嗞。呜呜呜。啊啊啊,”热浪喧闹着。“啊啊啊。嘛嘛嘛。啪啪啪。啦啦啦啦啦啦啦!”
就连他自己衣服上隐隐燃烧的火焰也在他耳边咆哮着胡言乱语。
“恶作剧鬼!”它们咆哮着。
“不可追踪的史泰因根·泽尔斯菲尔斯廷拉滕布鲁格!”
颜色对他来说是痛苦……热、冷、压力;无法忍受的高度和猛跌的深渊的感觉,巨大加速度和压碎压缩的感觉:
红色从他身边退去。
绿光袭来。
靛蓝色以令人作呕的速度起伏着,像颤抖的蛇。
触觉对他来说是味觉……木头的感觉在他嘴里是辛辣和粉状的,金属是咸的,石头尝起来酸甜,玻璃的感觉像过分油腻的糕点一样腻在他的味蕾上。
嗅觉是触觉……热石头闻起来像天鹅绒抚摸他的脸颊。烟灰是粗糙的粗花呢,摩擦着他的皮肤,几乎像湿帆布的感觉。熔化的金属闻起来像重击敲打他的心脏,而PyrE爆炸产生的电离则让空气中弥漫着臭氧,闻起来像水滴落流过他的手指。
他并非失明,并非失聪,并非失去知觉。感觉传到了他这里,但经过了一个因PyrE冲击波而扭曲和短路的神经系统过滤。他患上了联觉症,这是一种罕见的情况,感知系统接收到来自客观世界的信息并将其传递给大脑,但在大脑中,感官知觉相互混淆。因此,在福伊尔身上,声音记录为视觉,运动记录为声音,颜色变成疼痛感,触觉变成味觉,嗅觉变成触觉。他不仅被困在老圣帕特里克教堂下方地狱般的迷宫中;他还被困在自己交叉感官的万花筒中。
再次绝望,处于可怕的灭绝边缘,他放弃了所有生活的纪律和习惯;或者说,它们被从他身上剥夺了。他从一个受环境和经验条件限制的产物,退化成一个渴望逃脱和生存、并运用其拥有的每一种力量的混沌生物。两年前的奇迹再次发生。
一个完整人类有机体的、每一个细胞、纤维、神经和肌肉的未分割的能量,赋予了那种渴望力量,福伊尔再次进行了空间琼特。
他以思想的速度沿着弯曲宇宙的测地空间线飞驰,这速度远超光速。他的空间速度如此惊人,以至于他的时间轴从过去经由现在指向未来的垂直线被扭曲了。他沿着新的近乎水平的轴线,这条新的时空测地线闪烁前行,被一个不再受限于不可能概念的人类心灵的奇迹所驱动。
他又一次完成了赫尔穆特·格兰特、恩佐·丹德里奇以及其他数十名实验者未能完成的事情,因为他盲目的恐慌迫使他放弃了那些曾挫败先前尝试的时空抑制。他并非瞬移到别处,而是到了别时。但最重要的是,那种第四维度的意识,那种对时间之箭及其自身位置的完整图景——这种意识诞生于每个人心中,但被生活的琐事深深淹没——在福伊尔身上接近表面。他沿着时空测地线瞬移到别处和别时,通过一次宏伟的想象行为,将虚数单位i,即负一的平方根,转化为了现实。
他琼特了。
他身处“诺玛德”号上,漂浮在空旷冰冷的太空中。
他站在通往虚无的门前。
寒冷是柠檬的味道,真空是爪子在他皮肤上撕扯。太阳和星星是摇晃的寒颤,折磨着他的骨头。
“格洛姆哈·弗雷德尼斯·克洛莫哈马根辛!”运动在他耳边咆哮。
是一个背对着他、沿着走廊消失的身影;一个肩上扛着铜锅食物的身影;一个在自由落体中飞掠、漂浮、蠕动的身影。是格利弗·福伊尔。
——“米哈特·杰斯罗特·托·克罗纳甘·布特·弗利姆科克,”他移动的景象轰鸣着。
“啊哈!哦吼!姆吉特不要卡克,”光影的闪烁回答道。
“哦哦哦哦哦?所以哦哦哦哦?不哦哦哦哦。啊啊啊啊啊!”他身后旋转的碎片堆低语着。
他嘴里的柠檬味变得难以忍受。皮肤上爪子的撕扯成了折磨。
他琼特了。
他重新出现在老圣帕特里克教堂下方的熔炉中,距离他从那里消失还不到一秒钟。他被吸引着,就像海鸟一次又一次地被吸引回它正挣扎着逃离的火焰。他只忍受了那咆哮的熔炉片刻。
他琼特了。
他身处古夫尔·马特尔的深处。
天鹅绒般漆黑的黑暗是极乐,是天堂,是欣快感。“啊!”他如释重负地喊道。
“啊!”传来他声音的回声,而声音被转化为一道耀眼的光图案。
啊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啊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啊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燃烧的人畏缩了一下。“停!”他喊道,被噪音弄得眼花缭乱。又传来了回声那耀眼的图案:
停停停停停
停停停停停停
停停停停停停
停停停停停停停
停停停停停停停
停停停停停停
停停停停停
停停停停
远处传来一阵脚步的咔嗒声,在他眼中呈现出柔和的垂直极光条纹图案:
咔 咔 咔 咔 咔 咔
嗒 嗒 嗒 嗒 嗒 嗒
嗒 嗒 嗒 嗒 嗒 嗒
嗒 嗒 嗒 嗒 嗒 嗒
嗒 嗒 嗒 嗒 嗒 嗒
嗒 嗒 嗒 嗒 嗒 嗒
嗒 嗒 嗒 嗒 嗒 嗒
传来一声呐喊,如同
一
道
之
字
形
的
闪
电
一道光束袭来
那是来自古夫尔·马特尔医院的搜索队,正通过测震仪追踪福伊尔和吉斯贝拉·麦昆。燃烧的人消失了,但在无意中将搜索者从失踪逃犯的踪迹上引开之前没有消失。
他回到了老圣帕特里克教堂下方,在他最后一次消失后仅一瞬间重新出现。他疯狂地冲向未知,使他沿着不可避免地将他带回他试图逃离的“现在”的时空测地线向上攀爬;因为在时空倒置的马鞍曲线上,他的“现在”是曲线最深的凹陷处。
他可以驱使自己沿着测地线向上、向上、向上进入过去或未来,但不可避免地,他必须像一颗被扔上无限深坑斜坡的球一样,落回他自己的“现在”,在空中悬停片刻,然后滚回深渊。
但他仍然在绝望中冲向未知。
他又瞬移了。
他身处澳大利亚海岸的杰维斯海滩。
海浪的运动在咆哮:“伐木工-迷雾 克罗特哈文 监狱。伐木工迷雾 莫特斯拉文 傻瓜。”
海浪的翻腾让他眼前一片耀眼,如同成排的脚灯:格利弗·福伊尔和罗宾·韦恩斯伯里站在他面前。一个男人的尸体躺在沙滩上,沙子在他燃烧的嘴里感觉像醋。风拂过他的脸,尝起来像棕色纸张。
福伊尔张开嘴惊呼。声音以燃烧的星形气泡形式发出:福伊尔迈出一步。“轰隆!”运动咆哮道。
燃烧的人瞬移了。
他身处上海谢尔盖·奥雷尔医生的办公室里。
福伊尔又在他面前,用光的图案说话:
路 路 路
阻 碍 阻 碍 阻 碍
哦 呃 呜 哦 呃 呜 哦 呃 呜
他闪烁着回到老圣帕特里克教堂的痛苦中,又瞬移了。
他身处喧闹的西班牙阶梯。
他身处喧闹的西班牙阶梯。
他身处喧闹的西班牙阶梯。
他身处喧闹的西班牙阶梯。
他身处喧闹的西班牙阶梯。
他身处喧闹的西班牙阶梯。
他身处喧闹的西班牙阶梯。
他身处喧闹的西班牙阶梯。
燃烧的人瞬移了。
又冷了,带着柠檬的味道,真空用难以言喻的利爪撕扯着他的皮肤。他正透过一艘银色帆船的舷窗向外窥视。月球锯齿状的山脉在背景中高耸。透过舷窗,他能看到血液泵和氧气泵叮当作响的喧闹声,听到格利弗·福伊尔向他移动时发出的喧嚣。真空的爪子抓住了他的喉咙,带来痛苦的紧握。
时空的测地线将他卷回了“现在”的老圣帕特里克教堂下方,距离他最初开始疯狂挣扎还不到两秒钟。他又一次,像一支燃烧的长矛,将自己投向未知。
他身处火星的斯克洛茨基地下墓穴。那个像白色蛞蝓一样的林赛·乔伊斯正在他面前扭动。
“不!不!不!”她的动作尖叫着。“别伤害我。别杀我。不,求求你……求求你……求求你……”
燃烧的人张开他那老虎般的嘴巴笑了。“她疼,”他说。他声音的声音灼伤了他的眼睛。
疼 疼 疼
她 她 她
疼 疼 疼
她 她 她
疼 疼 疼
疼 疼 疼
疼 疼 疼
她 她 她
疼 疼 疼
她 她 她
疼 疼 疼
疼 疼 疼
疼 疼 疼
“你是谁?”福伊尔低语道。
谁谁谁谁谁谁谁谁谁谁谁谁谁谁谁谁谁谁谁谁谁谁谁谁谁
谁谁谁谁谁谁谁谁谁谁谁谁谁谁谁谁谁谁谁谁谁谁谁谁谁
谁谁谁谁谁谁谁谁谁谁谁谁谁谁谁谁谁谁谁谁谁谁谁谁谁
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
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
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
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
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
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
燃烧的人畏缩了一下。“太亮了,”他说。“光线弱一点。”
福伊尔向前迈出一步。“轰隆——嘎——达——嘛——哇——嘶嘶——鸣——利斯顿维斯塔!”运动咆哮道。
燃烧的人痛苦地捂住耳朵。“太吵了,”他喊道。“别动得那么响。”
扭动的斯克洛茨基人的动作仍在尖叫,恳求着:“别伤害我。别伤害我。”
燃烧的人又笑了。“听听她。她在尖叫。在乞求。她不想死。她不想受伤。听听她。”
“是奥利维亚·普雷斯蒂安下的命令。奥利维亚·普雷斯蒂安。不是我。别伤害我。奥利维亚·普雷斯蒂安。”
“她在说谁下的命令。你听不到吗?用你的眼睛听。她说奥利维亚。”
什么?什么?什么?
什么?什么?什么?
什么?什么?什么?
什么?什么?什么?
福伊尔问题的棋盘格闪光对他来说太强烈了。
“她说奥利维亚。奥利维亚·普雷斯蒂安。奥利维亚·普雷斯蒂安。奥利维亚·普雷斯蒂安!”
他琼特了。
他跌回老圣帕特里克教堂下方的深坑,突然间,他的混乱和绝望告诉他,他已经死了。这就是格利弗·福伊尔的结局。这就是永恒,而地狱是真实的。他所看到的是过去在他坍塌的感官前闪过,在死亡的最后一刻。他所忍受的,他必须忍受永恒。他死了。他知道自己死了。
他拒绝屈服于永恒。他又一次冲向未知。
燃烧的人瞬移了。
他身处一片闪闪发光的薄雾中……一簇雪花般的星星……一阵液态钻石的骤雨。皮肤上感受到蝴蝶翅膀的触碰……嘴里尝到一串凉爽珍珠的味道。
oooooooooooooooooooooooo
他那交叉混乱的万花筒般的感官无法告诉他身在何处,但他知道自己想永远留在这个虚无之地。
“你好,格利。”
“那是谁?”
“我是罗宾!”
“罗宾?”
“曾经的罗宾·韦恩斯伯里。”
“曾经的?”
“现在的罗宾·尤维尔。”
“我不明白。我死了吗?”
“不,格利。”
“我在哪里?”
“离老圣帕特里克教堂很远很远。”
“但是哪里?”
“我没时间解释了,格利。你在这里只有几分钟。”
“为什么?”
“因为你还没学会穿越时空进行琼特。你得回去学习。”
“但我知道。我肯定知道。谢菲尔德说我空间琼特到了诺玛德号……六十万英里。”
“那是当时的意外,格利,你会再做到的……在你教会自己之后……但你现在没在做。你还不知道如何坚持……如何把任何‘现在’变成现实。你一会儿就会跌回老圣帕特里克教堂。”
“罗宾,我刚想起来。我有个坏消息要告诉你。”
“我知道,格利。”
“你母亲和妹妹们都死了。”
“我早就知道了,格利。”
“多久了?”
“三十年了。”
“那不可能。”
“不,不是。这里离老圣帕特里克教堂很远很远。我一直想告诉你如何从火中自救,格利。你愿意听吗?”
“我没死?”
“没有。”
“我会听。”
“你的感官都混乱了。很快就会过去,但我不会用左右或上下的方向来指示。我会告诉你现在能理解的方式。”
“你为什么帮我……在我对你做了那些事之后?”
“那一切都已原谅和遗忘,格利。现在听我说。当你回到老圣帕特里克教堂时,转过身,直到你面对着最响亮的影子。记住了吗?”
“是的。”
“朝着噪音走,直到你皮肤上感到一阵深深的刺痛。然后停下来。”
“然后停下。”
“向着压缩和坠落感转半圈。跟着那个感觉走。”
“跟着那个感觉走。”
“你会穿过一片坚固的光幕,来到尝起来像奎宁的地方。那其实是一堆电线。径直穿过奎宁,直到你看到听起来像跳锤的东西。你就安全了。”
“你怎么知道这一切,罗宾?”
“我得到了一位专家的指点,格利。”
传来一阵笑声。“你随时都可能跌回过去。彼得和索尔在这里。他们向你道别并祝你好运。还有吉兹·达格纳姆。祝你好运,格利亲爱的……”
“过去?这是未来?”
“是的,格利。”
“我在这里吗?是……奥利维亚?”
然后他向下坠落,坠落,坠落,沿着时空线跌回可怕的“现在”深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