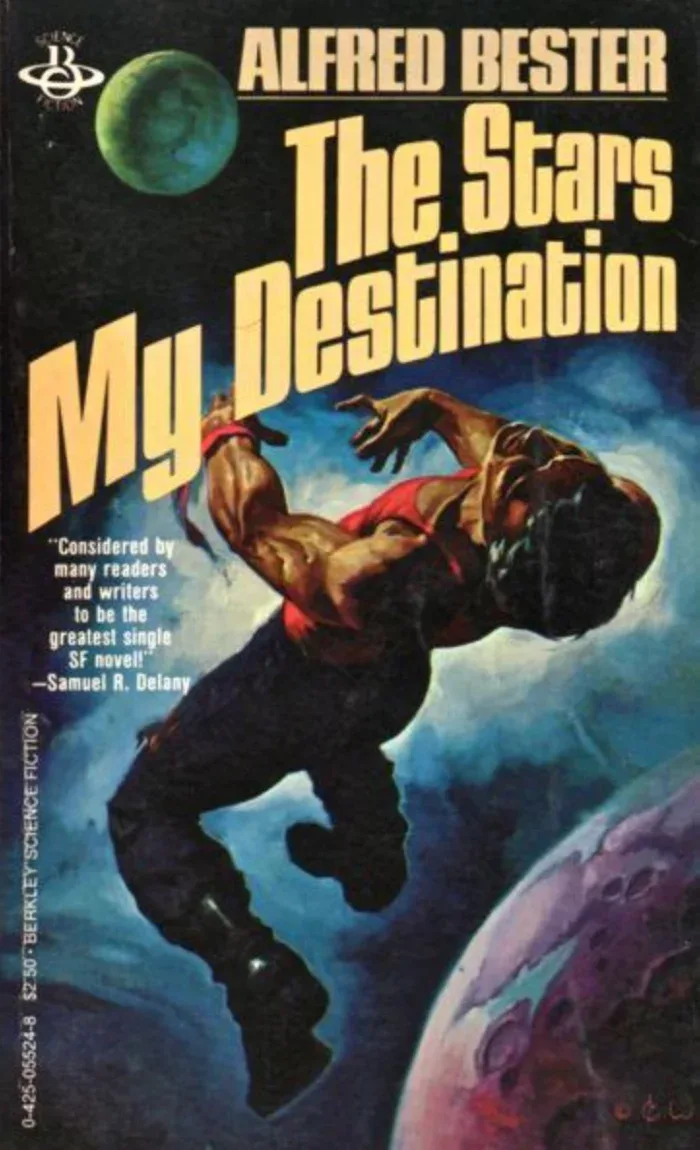正如往常一样,当雷吉斯·谢菲尔德结束在列宁格勒一场激烈的民事法庭审理返回时,他感到高兴和自满,有点像一个赢了一场硬仗、趾高气扬的拳击手。他在柏林的布莱克曼酒吧停下来喝了一杯,聊了聊战争,在奥赛码头一个法律界人士常去的酒吧喝了第二杯,聊了更多战争,在圣殿律师学院对面的“皮包骨头”酒吧进行了第三次会谈。等他到达纽约办公室时,他已经喝得微醺了。
当他大步穿过喧闹的走廊和外间办公室时,他的秘书递给他一把记忆珠迎接他。
“把贾戈-丹琴科打了个落花流水,”谢菲尔德得意洋洋地报告。“判决和全额赔偿。老D.D.气得要命。这让比分变成十一比五,我领先。”
他接过珠子,抛了抛,然后开始把它们扔进办公室里各种不太可能的容器里,包括一个目瞪口呆的职员张开的嘴巴。
“说真的,谢菲尔德先生!您喝酒了吗?”
“今天不工作了。战争消息太他妈糟了。得做点什么保持愉快。我们上街打架怎么样?”
“谢菲尔德先生!”
“有什么等不及明天处理的事吗?”
“您办公室里有位先生。”
“他让你放他进去了?”谢菲尔德看起来印象深刻。“他是谁?上帝,还是什么人?”
“他不肯说名字。他给了我这个。”
秘书递给谢菲尔德一个密封的信封。上面潦草地写着:紧急。谢菲尔德撕开信封,他那直率的面容因好奇而皱起。然后他眼睛睁大了。信封里是两张面值五万信用点的钞票。谢菲尔德一言不发地转过身,冲进了他的私人办公室。福伊尔从椅子上站起来。
“这些是真的,”谢菲尔德脱口而出。
“据我所知。”
“去年只铸造了二十张这样的钞票:全都存放在地球财政部的金库里。你是怎么弄到这两张的?”
“谢菲尔德先生?”
“还有谁?你是怎么弄到这些钞票的?”
“贿赂。”
“为什么?”
“我当时想,手头有它们可能会很方便。”
“为了什么?更多的贿赂?”
“如果律师费算贿赂的话。”
“我自己定费用,”谢菲尔德说。他把钞票扔回给福伊尔。“如果我决定接你的案子,并且如果我决定我值那个价,你可以再把它们拿出来。你有什么问题?”
“还不要说得太具体。还有……?”
“我想自首。”
“向警察?”
“为了什么罪行?”
“罪行。”
“说两个。”
“抢劫和强奸。”
“再说两个。”
“敲诈和谋杀。”
“还有别的项目吗?”
“叛国和种族灭绝。”
“你的清单就这些了吗?”
“我想是的。等我们具体谈的时候,也许能再揭露一些。”
“挺忙的,不是吗?你要么是恶棍之王,要么是疯子。”
“两者我都当过,谢菲尔德先生。”
“你为什么想自首?”
“我醒悟了,”福伊尔苦涩地回答。
“我不是那个意思。罪犯领先的时候从不投降。你显然领先。原因是什么?”
“发生在一个男人身上最该死的事情。我得了一种罕见的叫做良心的病。”
谢菲尔德哼了一声。“那常常会致命。”
“它是致命的。我意识到我一直像个禽兽一样行事。”
“现在你想净化自己?”
“不,没那么简单,”福伊尔冷酷地说。“所以我才来找你……做大手术。扰乱社会形态的人是癌症。将自己的决定置于社会之上的人是罪犯。但存在连锁反应。用惩罚来净化自己是不够的。一切都必须纠正过来。我真希望一切都能通过把我送回古夫尔·马特尔或者枪毙我来解决……”
“回来?”
谢菲尔德敏锐地插话道。
“要我说具体点吗?”
“还没。继续。听起来你像是经历了道德成长的阵痛。”
“正是如此。”
福伊尔激动地踱步,用紧张的手指揉搓着钞票。“这真是一团糟,谢菲尔德。有一个女孩必须为一桩恶毒、腐烂的罪行付出代价。我爱她的事实——不,别管那个。她是一个必须被切除的癌症……像我一样。这意味着我必须在我的清单上加上告密。我同时自首的事实并不能改变任何事情。”
“这都是些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
福伊尔转向谢菲尔德。“新年的一颗炸弹刚刚走进你的办公室,它在说:‘把一切都纠正过来。把我重新拼好,送我回家。把我夷平的城市和我粉碎的人民重新拼起来。’这就是我想雇你做的事。我不知道大多数罪犯感觉如何——”
“明智、务实;像运气不好的好商人,”谢菲尔德立刻回答道。“这是职业罪犯通常的态度。如果你真的是罪犯,那你显然是个业余爱好者。我亲爱的先生,请理智点。你来到这里,夸张地指控自己犯有抢劫、谋杀、种族灭绝、叛国以及天知道还有什么罪行。你指望我当真吗?”
邦尼,谢菲尔德的助手,瞬移进了他的私人办公室。
“头儿,”他兴奋地喊道。“出了件全新的事——一次相机瞬移。两个骗子贿赂了一个出纳员,拍下了地球信托交易所的内部照片——哎呀。抱歉。没意识到您有——”
邦尼停了下来,盯着看。“福尔迈尔!”他惊呼道。
“什么?谁?”谢菲尔德质问道。
“你不认识他吗,头儿?”邦尼结结巴巴地说。“那是谷神星的福尔迈尔。格利弗·福伊尔。”
一年多以前,雷吉斯·谢菲尔德被催眠引爆并为此刻做好了准备。他的身体被训练成无需思考即可做出反应,而反应迅如闪电。谢菲尔德在半秒钟内击中了福伊尔;太阳穴、喉咙和腹股沟。他们决定不依赖武器,因为可能没有武器可用。
福伊尔倒下了。谢菲尔德转向邦尼,把他打回办公室。然后他往手心里吐了口唾沫。他们决定不依赖药物,因为可能没有药物可用。谢菲尔德的唾液腺被训练成在刺激下分泌过敏性休克分泌物。他打开福伊尔的袖子,用指甲深深地抠进他肘窝,划开一道口子。他把唾沫按进那道粗糙的伤口,然后捏紧皮肤。
福伊尔嘴里发出一声奇怪的哭喊;纹身在他脸上显露出青紫的颜色。在目瞪口呆的助手还没来得及做出任何动作之前,谢菲尔德把福伊尔扛到肩上,瞬移了。
他到达了老圣帕特里克教堂的四英里马戏团中央。这是一个大胆但经过计算的举动。这是最不可能被预料到的地方,也是他最有可能找到PyrE的地方。他准备好了对付在教堂里可能遇到的任何人,但马戏团内部空无一人。
中殿里空荡荡的帐篷看起来破破烂烂;它们已经被洗劫过了。谢菲尔德一头扎进他看到的第一个帐篷。那是福尔迈尔的移动图书馆,里面装满了数百本书和数千颗闪闪发光的小说珠。劫掠琼特者对文学不感兴趣。谢菲尔德把福伊尔扔到地上。直到那时他才从口袋里掏出一把枪。
福伊尔的眼睑颤动着;他的眼睛睁开了。
“你被下药了,”谢菲尔德快速说道。“别试着琼特。也别动。我警告你。我准备好了应对任何事。”
福伊尔晕眩地试图站起来。谢菲尔德立刻开枪,烧伤了他的肩膀。福伊尔被猛地撞回石地板上。他麻木了,困惑了。耳边传来轰鸣声,毒药在他血液中奔流。
“我警告过你,”谢菲尔德重复道。“我准备好了应对任何事。”
“你想要什么?”福伊尔低语道。
“两样东西。二十磅PyrE,还有你。你最重要。”
“你这个疯子!你这个该死的疯子!我到你办公室是为了放弃……交出来……”
“给外围卫星?”
“给……什么?”
“外围卫星?要我给你拼出来吗?”
“不——……”福伊尔咕哝道。“我早该知道。爱国者谢菲尔德,一个外围卫星特工。我早该知道。我是个傻瓜。”
“你是世界上最有价值的傻瓜,福伊尔。我们想要你甚至超过PyrE。那对我们来说是未知的,但我们知道你是什么。”
“你在说什么?”
“我的天!你不知道,是吗?你还不知道。你一点线索都没有。”
“什么线索?”
“听我说,”谢菲尔德用砰击的声音说道。“我带你回到两年前的诺玛德号。明白吗?回到诺玛德号的死亡。我们的一艘袭击舰干掉了她,他们在残骸上找到了你。最后一个活着的人。”
“所以是外围卫星的飞船炸毁了诺玛德号?”
“是的。你不记得了?”
“我不记得任何关于那件事。我从来都记不得。”
“我告诉你原因。袭击者想出了一个聪明的主意。他们要把你变成一个诱饵……一个活靶子,明白吗?你当时半死不活,但他们把你带上船,给你包扎了一下。他们给你穿上宇航服,把你扔到太空中漂流,你的微波通讯器开着。你在每个波段广播求救信号,含糊不清地求救。他们的主意是,他们会潜伏在附近,拦截前来营救你的内行星飞船。”
福伊尔开始笑起来。“我要起来了,”他鲁莽地说。
“再开枪啊,你这个狗娘养的,但我要起来了。”他挣扎着站起来,捂着肩膀。“所以沃加号无论如何都不该来接我,”福伊尔笑着说。“我是个诱饵。谁都不该靠近我。我是个托儿,一个诱饵,死亡诱饵……这难道不是第一个讽刺吗?诺玛德号根本就没资格被营救。我根本就没资格复仇。”
“你还是不明白,”谢菲尔德猛击道。“他们把你扔到太空漂流时,离诺玛德号很远。他们离诺玛德号有六十万英里。”
“六十万——”
“诺玛德号离航线太远了。他们想让你漂到船只会经过的地方。他们把你带到向阳方向六十万英里处,然后把你扔到太空漂流。他们把你送出气闸,然后后退:看着你漂流。你的宇航服灯闪烁着,你在微波通讯器上呻吟求救。然后你消失了。”
“消失了?”
“你不见了。没有灯光,没有广播。他们回来检查。你无影无踪地消失了。我们后来得知……你回到了诺玛德号上。”
“不可能。”
“伙计,你进行了空间琼特,”谢菲尔德凶狠地说。“你当时被包扎着,神志不清,但你进行了空间琼特。你穿越了六十万英里的虚空,空间琼特回到了诺玛德号的残骸。你做了一件前所未有的事。天知道是怎么做到的。你自己都不知道;但我们会弄清楚的。我要带你回外围卫星,我们会从你身上挖出那个秘密,即使我们不得不把它撕出来。”
他用有力的手抓住福伊尔的喉咙,另一只手掂量着枪。“但首先我要PyrE。你会交出来的,福伊尔。别以为你不会。”
他用枪猛击福伊尔的额头。“为了得到它,我什么都做得出来。别以为我不会。”
他再次冷酷而高效地猛击福伊尔。“如果你在寻求净化,伙计,你找到了。”
邦尼从五点公共琼特平台跳下,像只受惊的兔子一样冲进中央情报局纽约办公室的正门。他冲过最外层的警戒线,穿过防护迷宫,进入内部办公室。他身后跟了一串兴奋的追兵,发现自己正面对着那些更有经验的警卫,他们已经平静地瞬移到他前面等着了。
邦尼开始喊道:“尤维尔!尤维尔!尤维尔!”
仍然跑着,他绕过办公桌,踢翻椅子,制造出难以置信的喧嚣。他继续喊叫:“尤维尔!尤维尔!尤维尔!”
就在他们准备结果他之前,杨-尤维尔出现了。
“这都是怎么回事?”他厉声说道。“我下令韦恩斯伯里小姐必须绝对安静。”
“尤维尔!”邦尼喊道。
“那是谁?”
“谢菲尔德的助手。”
“什么……邦尼?”
“福伊尔!”
邦尼嚎叫着。“格利弗·福伊尔。”
杨-尤维尔用精确的一点六六秒覆盖了他们之间五十英尺的距离。“福伊尔怎么了?”
“谢菲尔德抓到他了,”邦尼喘着气说。
“谢菲尔德?什么时候?”
“半小时前。”
“他为什么没把他带到这里来?”
“不知道……有个想法……可能是外围卫星特工……”
“你为什么不立刻过来?”
“谢菲尔德带着福伊尔瞬移了……把他打得像条死鱼一样然后消失了。我去找了。到处找。碰碰运气。二十分钟里肯定瞬移了五十次……”
“业余!”杨-尤维尔恼怒地惊呼道。“你为什么不把这事交给专业人士?”
“找到了。”
“你找到他们了?在哪儿!”
“老圣帕特里克教堂。谢菲尔德在追查那个——”
但杨-尤维尔已转过身,沿着走廊飞奔回去,喊叫着:“罗宾!罗宾!停下!停下!”
然后他们的耳朵被雷鸣般的轰鸣声震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