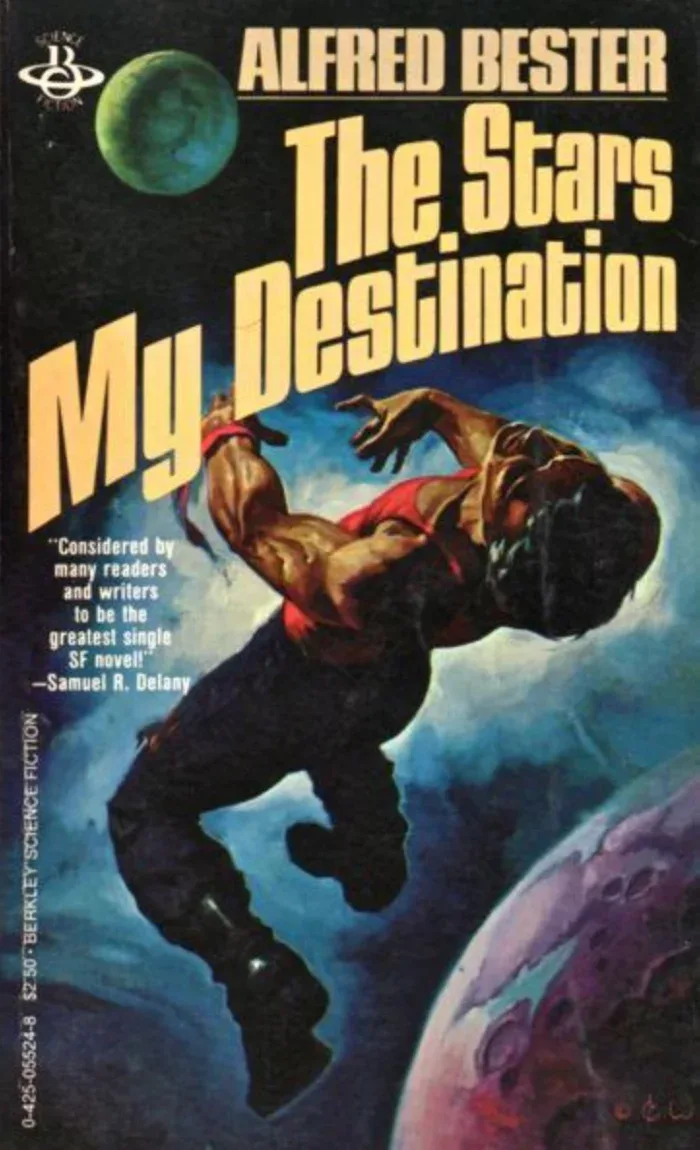索尔·达格纳姆离开了黑暗的卧室。片刻之后,随着一面墙壁亮起,房间被光线淹没。看起来像一面巨大的镜子反射着吉斯贝拉的卧室,但有一个奇怪的扭曲。吉斯贝拉独自躺在床上,但在倒影中,索尔·达格纳姆独自坐在床边。那面镜子实际上是一块隔开相同房间的铅玻璃。达格纳姆刚刚照亮了他那边。
“按时钟恋爱,”达格纳姆的声音通过扬声器传来。“恶心。”
“不,索尔。绝不。”
“令人沮丧。”
“也不是那个。”
“但不快乐。”
“不。你太贪婪了。满足于你所拥有的吧。”
“天知道,这比我拥有过的任何东西都多。你太棒了。”
“你太夸张了。现在去睡觉吧,亲爱的。我们明天滑雪。”
“不,计划有变。我得工作。”
“哦,索尔……你答应过我的。不再工作、烦恼和奔波了。你难道不打算信守承诺吗?”
“战争期间我不能。”
“管他妈的战争。你在蒂科沙滩牺牲得够多了。他们不能再要求你什么了。”
“我有一件工作要完成。”
“我帮你完成它。”
“不。你最好别掺和这事,吉斯贝拉。”
“你不信任我。”
“我不想你受伤。”
“没什么能伤害我们。”
“福伊尔可以。”
“什——什么?”
“福尔迈尔就是福伊尔。你知道的。我知道你知道。”
“但我从未——”
“不,你从未告诉我。你太棒了。以同样的方式对我保持忠诚,吉斯贝拉。”
“那你怎么发现的?”
“福伊尔露馅了。”
“怎么露馅的?”
“那个名字。”
“谷神星的福尔迈尔?他买下了谷神星公司。”
“但是杰弗里·福尔迈尔呢?”
“他编的。”
“他以为是他编的。他记起来了。杰弗里·福尔迈尔是他们在墨西哥城联合医院夸大狂测试中使用的名字。我试图撬开福伊尔的嘴时,对他使用了夸大狂模式。那个名字一定埋藏在他的记忆里。他把它挖了出来,还以为是原创的。这提醒了我。”
“可怜的格利。”
达格纳姆笑了笑,“是的,无论我们如何防御外部,我们总是被内部的东西打败。没有防御背叛的方法,而我们都背叛了自己。”
“你打算怎么做,索尔?”
“做?当然是干掉他。”
“为了二十磅PyrE?”
“不:为了赢得一场已经输掉的战争。”
“什么?”吉斯贝拉走到隔开房间的玻璃墙前。“你,索尔?爱国?”
他点点头,几乎是内疚地,“这很荒谬。怪诞。但我确实是。你彻底改变了我。我又是一个理智的人了。”
他也把脸贴到墙上,他们隔着三英寸厚的铅玻璃亲吻着。
月球的云海非常适合厌氧细菌、土壤微生物、噬菌体、稀有霉菌以及所有那些对医药和工业至关重要的、需要无氧培养的微小生命形式的生长。“细菌公司”是一个由培养场组成的巨大马赛克,其间穿插着人行步道,围绕着中央一簇营房、办公室和工厂。每个培养场都是一个巨大的玻璃缸,直径一百英尺,高十二英寸,厚度不超过两个分子。
在日出线爬行穿过月球表面到达云海的前一天,培养缸里装满了培养基。日出时分,在无空气的月球上,日出突然而耀眼,培养缸被播种,接下来的十四天连续日照期间,它们被照料、遮蔽、调节、培育……田间工人们穿着宇航服在人行步道上艰难地来回。当
日落线爬行靠近云海时,培养缸被收获,然后留在月球长达两周的霜冻夜晚中冷冻和消毒。
琼特在这种繁琐的、一步一步的培养中毫无用处。因此,细菌公司雇佣了无法琼特的不幸者,付给他们奴隶般的工资。这是最低等的劳动,是太阳系的渣滓和败类;而在为期两周的休工期内,细菌公司的营房就像地狱一般。福伊尔进入3号营房时发现了这一点。
他被眼前的骇人景象惊呆了。巨大的房间里有两百个男人;还有妓女和她们冷酷的皮条客,职业赌徒和他们的便携式赌桌,毒贩,放高利贷者。空气中弥漫着刺鼻的烟雾和酒精与类比药的恶臭。家具、床上用品、衣服、不省人事的身体、空瓶子、腐烂的食物散落在地板上。完全是霍加斯式的景象。
一声咆哮挑战了福伊尔的出现,但他已准备好应对这种情况。他对第一个凑到他面前的毛茸茸的脸说话。
“肯普西?”他平静地问道。
他得到了粗暴的回答。尽管如此,他还是咧嘴一笑,递给那人一张100信用点的钞票。
“肯普西?”他又问了一个。他受到了侮辱。他又付了钱,继续沿着营房闲逛,平静地分发着100信用点的钞票,以感谢侮辱和谩骂。在营房中央,他找到了他的关键人物,显然是营房的恶霸,一个像怪物一样的男人,赤身裸体,没有毛发,抚摸着两个鸨母,由谄媚者喂他威士忌。
“肯普西?”福伊尔用古老的贫民窟语言问道。“我在找罗杰·肯普西。”
“我正挖着让你破产呢,”那人回答道,伸出一只巨大的爪子要福伊尔的钱。“给我。”
人群中爆发出欣喜的嚎叫。福伊尔笑了笑,朝他眼睛里吐了口唾沫。一片死寂。那个没毛的男人扔下鸨母,涌上来要消灭福伊尔。五秒钟后,他卑躬屈膝地趴在地上,福伊尔的脚踩在他的脖子上。
“还在挖肯普西,”福伊尔温柔地说。“挖得很卖力,伙计。你最好指认他,伙计,否则你就完了,就是这样。”
“洗手间!”那个没毛的男人嚎叫道。“躲起来了。洗手间。”
“现在你让我破产了,”福伊尔说。他把剩下的钱扔在那个没毛的男人面前的地板上,然后快步走向洗手间。
肯普西畏缩在一个淋浴间的角落里,脸贴着墙壁,发出沉闷的呻吟声,这表明他已经这样持续了好几个小时。
“肯普西?”呻吟声回答了他。
“怎么了,你?”
“衣服,”肯普西哭泣着。“衣服。到处都是衣服。像污秽,像病态,像肮脏。衣服。到处都是衣服。”
“起来,伙计。起来。”
“衣服。到处都是衣服。像污秽,像病态,像肮脏……”
“肯普西,听我说,伙计。奥雷尔派我来的。”
肯普西停止了哭泣,把湿漉漉的脸转向福伊尔。“谁?谁?”
“谢尔盖·奥雷尔派我来的。我带来了你的释放令。你自由了。我们走吧。”
“什么时候?”
“现在。”
“哦,上帝!上帝保佑他。保佑他!”
肯普西开始疲惫地欢欣雀跃起来。那张青肿浮肿的脸裂开,露出一种类似笑声的表情。他笑着,跳跃着,福伊尔领着他走出了洗手间。但在营房里,他又尖叫着哭泣起来,当福伊尔领着他走过长长的房间时,那些赤身裸体的鸨母们抱起一堆堆脏衣服,在他眼前晃动着。肯普西口吐白沫,胡言乱语。
“怎么了,他?”
福伊尔用贫民窟的方言向那个没毛的男人询问。
那个没毛的男人现在即使不是朋友,也是一个恭敬的中立者了。“天知道,”他回答道。“他总是那样。给他看旧衣服,他就抽搐。伙计!”
“为什么,已经?”
“为什么?疯了,就是这样。”
在主办公室的气闸处,福伊尔给肯普西和自己穿好宇航服,然后领他出去到火箭发射场,那里二十几束反重力光束从发射坑向上伸出苍白的手指,指向悬挂在夜空中的凸起的地球。他们进入一个发射坑,进入福伊尔的帆船并解开宇航服。福伊尔从一个柜子里拿出一瓶酒和一个毒刺安瓿。他倒了一杯酒递给肯普西。他掂量着手里的安瓿,微笑着。
肯普西喝着威士忌,仍然晕眩,仍然欢欣鼓舞。“自由了,”他咕哝道。“上帝保佑他!自由了。天哪,我经历了什么。”
他又喝了一口。“我还是不敢相信。这就像一场梦。你为什么不走,伙计?我——”
肯普西呛住了,扔掉了杯子,惊恐地盯着福伊尔。“你的脸!”他惊呼道。“我的天,你的脸!它怎么了?”
“是你干的好事,你这个狗娘养的!”福伊尔喊道。他跳起来,脸上燃烧着老虎般的印记,像扔刀一样扔出安瓿。安瓿刺穿了肯普西的脖子,颤抖着悬在那里。肯普西倒下了。
福伊尔加速,模糊地冲到尸体旁,在它下落中途将其接住,并将其抬到船尾的右舷特等舱。帆船上有两个主特等舱,福伊尔事先都准备好了。右舷房间已被清空,变成了一间手术室。福伊尔将尸体绑在手术台上,打开一箱手术器械,开始了他那天早上通过催眠训练学到的精细手术……这种手术只有在他五比一的加速状态下才可能完成。
他切开皮肤和筋膜,锯开胸腔,暴露出心脏,将其解剖出来,并将静脉和动脉连接到桌旁复杂的血液泵上。他启动了泵。客观时间过去了二十秒。他给肯普西戴上氧气面罩,打开了氧气泵交替的吸气和打嗝功能。
福伊尔减速,检查了肯普西的体温,给他注射了一系列抗休克药物,然后等待着。血液汩汩地流过泵和肯普西的身体。五分钟后,福伊尔取下了氧气面罩。呼吸反射仍在继续。肯普西没有心脏,却还活着。福伊尔坐在手术台旁边等待着。烙印仍然显现在他脸上。
肯普西仍然昏迷不醒。
福伊尔等着。
肯普西醒了,尖叫着。
福伊尔跳起来,勒紧带子,俯身在那个没有心脏的人身上。
“你好,肯普西,”他说。
肯普西尖叫起来。
“看看你自己,肯普西。你死了。”
肯普西昏了过去。福伊尔用氧气面罩把他弄醒。
“看在上帝的份上,让我死吧!”
“怎么了?疼吗?我死了六个月,都没抱怨。”
“让我死吧。”
“到时候会让你死的。到时候,如果你听话的话。你在2336年9月16日登上了沃加号?”
“看在基督的份上,让我死吧。”
“你在沃加号上?”
“是的。”
“你经过了太空中的一艘残骸。诺玛德号的残骸。她发出了求救信号,而你却从她身边经过了。是吗?”
“是的。”
“为什么?”
“基督!哦,基督救我!”
“为什么?”
“哦,耶稣!”
“我在诺玛德号上,肯普西。你为什么让我腐烂?”
“亲爱的耶稣救我!基督,救救我!”
“我会救你的,肯普西,如果你回答问题的话。你为什么让我腐烂?”
“不能接你。”
“为什么不?”
“船上有难民。”
“哦!那我猜对了。你们当时正从木卫四偷渡难民?”
“是的。”
“多少人?”
“六百。”
“那很多,但你们本可以再腾出一个位置。为什么不接我?”
“我们正在处决难民。”
“什么!”
福伊尔喊道:“扔到船外……全部……六百人……剥光他们的衣服……拿走他们的衣服、钱、珠宝、行李……分批把他们送进气闸。天哪!衣服扔得到处都是……尖叫声和——耶稣!要是我能忘记就好了!那些赤裸的女人……蓝色的……爆裂开来……在我们身后旋转……衣服扔得到处都是……六百人……处决了!”
“你这个狗娘养的!这是个骗局?你收了他们的钱,根本没打算把他们带到地球?”
“是个骗局。”
“所以你才没来接我?”
“反正也得把你处理掉。”
“谁下的命令?”
“船长。”
“名字?”
“乔伊斯。林赛·乔伊斯。”
“地址?”
“斯克洛茨基殖民地,火星。”
“什么!”
福伊尔惊呆了。“他是个斯克洛茨基人?你的意思是,追捕了他一年之后,却不能碰他……伤害他……让他感受我所感受的?”
他从桌上那个受尽折磨的人身边转开,自己同样因沮丧而备受折磨。“一个斯克洛茨基人!我唯一没算到的……在为他准备好左舷特等舱之后……我该怎么办?看在上帝的份上,我该怎么办?”他愤怒地咆哮着,脸上显露出鲜红的烙印。
肯普西一声绝望的呻吟把他拉了回来。他回到桌前,俯身看着那具被解剖的身体。“最后一次弄清楚。是这个斯克洛茨基人,林赛·乔伊斯,下令处决难民的?”
“是的。”
“并且让我腐烂?”
“是的。是的。看在上帝的份上,够了。让我死吧。”
“活下去,你这猪猡……肮脏无情的混蛋!没有心脏也要活下去。活着受苦。我会让你永远活下去,你——”一道刺眼的光芒吸引了福伊尔的注意。他抬起头。他燃烧的影像正透过特等舱宽大的方形舷窗窥视着。当他跳向舷窗时,燃烧的人消失了。
福伊尔离开特等舱,冲到前方主控室,那里的观察气泡给了他二百七十度的视野。燃烧的人无处可寻。
“这不是真的,”他咕哝道。“不可能是真的。这是个预兆;一个好运的预兆……一个守护天使。它在西班牙阶梯上救了我。它在告诉我继续前进,找到林赛·乔伊斯。”
他把自己绑在驾驶员座椅上,点燃了帆船的喷气发动机,猛地加速到最大。
“林赛·乔伊斯,斯克洛茨基殖民地,火星,”他想,被深深地压进气动座椅。“一个斯克洛茨基人……没有感官,没有快乐,没有痛苦。斯多葛派逃避现实的极致。我该怎么惩罚他?折磨他?把他关进左舷特等舱,让他感受我在诺玛德号上所感受的?该死!这就像他死了。他确实死了。我必须想出办法来打败一具尸体,让它感受到痛苦。离终点如此之近,却被拒之门外……复仇那该死的挫败感。复仇只存在于梦中……绝不存在于现实。”
一小时后,他从加速和狂怒中解脱出来,解开座椅上的安全带,想起了肯普西。他走到船尾的手术室。起飞时的极端加速度已经足以扼杀血液泵,杀死了肯普西。突然,福伊尔被一种新奇而强烈的自我厌恶感淹没了。他无助地与之抗争。
“怎么了,你?”他低语道。“想想那六百个被处决的人……想想你自己……你是不是变成了一个脸色苍白的地下室基督徒,转过另一边脸颊,抱怨宽恕?奥利维亚,你对我做了什么?给我力量,不是懦弱……”
尽管如此,当他处理尸体时,还是避开了目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