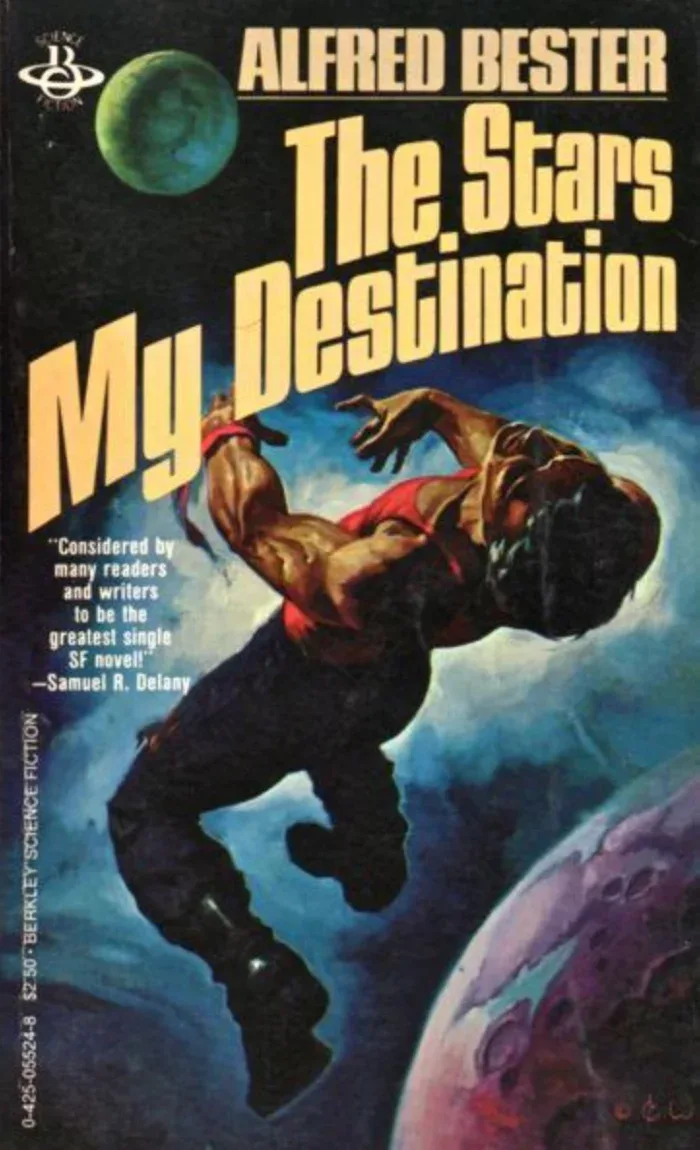随着琼特的穷人抛弃贫民窟,在平原和森林中非法占据土地,掠夺牲畜和野生动物,爆发了土地骚乱。住宅和办公建筑发生了革命,必须引入迷宫和掩蔽装置以防止通过琼特非法闯入。随着前琼特时代的产业失败,出现了崩溃、恐慌、罢工和饥荒。
随着琼特的流浪者将疾病和害虫带入毫无防备的国家,瘟疫和大流行病肆虐。疟疾、象皮病和断骨热向北传播到格陵兰;狂犬病在消失三百年后重返英国。日本甲虫、柑橘蚧、栗枯病和榆蛀虫蔓延到世界的每一个角落,而在一处被遗忘的婆罗洲疫源地,长期被认为已灭绝的麻风病再次出现。
犯罪浪潮席卷了行星和卫星,因为黑社会利用琼特昼夜不停地环绕地球作案,而警察则毫不留情地与他们战斗,手段残忍。随着社会用礼仪和禁忌来对抗琼特的性与道德危险,出现了维多利亚时代最严酷的虚伪道德的可怕回归。内行星——金星、地球和火星——与外围卫星之间爆发了一场残酷而恶毒的战争……这场战争是由心灵传送带来的经济和政治压力引发的。
在琼特时代到来之前,三颗内行星(以及月球)与七颗有人居住的外围卫星——木星的伊俄、欧罗巴、盖尼米得和卡利斯托;土星的瑞亚和泰坦;以及海王星的拉塞尔——一直处于微妙的经济平衡之中。联合外围卫星为内行星的工厂提供原材料,并为其成品提供市场。十年之内,这种平衡被琼特打破了。
外围卫星,这些正在形成中的原始年轻世界,购买了内行星交通运输产量的百分之七十。琼特终结了这一点。它们购买了内行星通讯产量的百分之九十。琼特也终结了这一点。结果,内行星对外围卫星原材料的购买量下降。随着贸易交换的破坏,经济战争不可避免地退化为武装冲突。内行星卡特尔拒绝向外围卫星运送制造设备,试图保护自己免受竞争。外围卫星没收了已经在其世界上运行的工厂,撕毁了专利协议,无视版税义务……战争爆发了。
这是一个怪胎、怪物和怪诞形象的时代。整个世界都以奇妙而邪恶的方式扭曲变形。憎恨这个时代的古典主义者和浪漫主义者并未意识到二十四世纪潜在的伟大。他们对进化的冷酷事实视而不见……即进步源于对立极端的激烈融合,源于顶尖怪胎的联姻。古典主义者和浪漫主义者都未意识到,太阳系正处在一场人类大爆发的边缘,这场爆发将改变人类,使之成为宇宙的主宰。
正是在这二十四世纪沸腾的背景下,格利·福伊尔复仇的历史开始了。
第一章
他在死亡线上挣扎了一百七十天,但尚未死去。他以陷阱中野兽般的热情为生存而战。他神志不清,身体腐烂,但偶尔,他那原始的心智会从生存的灼热噩梦中浮现,进入一种类似清醒的状态。那时,他会抬起他那张沉默的脸,对着永恒低语:“怎么了,我?帮帮忙,你们这群浑蛋。帮帮忙,就是这样。”
亵渎对他来说轻而易举;这构成了他一半的言语,他全部的生活。他是在二十四世纪的贫民窟学校里长大的,除了贫民窟的语言,什么也不会说。在世上所有的野蛮人中,他是活着最没价值,却最可能活下去的一个。所以他挣扎着求生,并用亵渎来祈祷;但偶尔,他那混乱的思绪会跃回三十年前的童年,记起一首童谣:
格利·福伊尔是我的名
地球是我的国家。
深空是我的居所
死亡是我的终点。
他是格利弗·福伊尔,三级机械师助手,三十岁,骨架大,性情粗犷……在太空中漂流了一百七十天。他是格利·福伊尔,加油工、擦拭工、燃料工;太随和而惹不起麻烦,太迟钝而无趣,太空虚而交不到朋友,太懒惰而不懂爱。他性格中懒散的轮廓甚至在官方商船队的记录中都有体现:
福伊尔,格利弗 – AS-128/127:006
教育程度:无
技能:无
功绩:无
推荐:无
(人事评语)
体格强壮,智力潜力因缺乏抱负而受阻。最低限度激发活力。典型的普通人。某种意外的冲击或许能唤醒他,但心理部门找不到钥匙。不建议进一步晋升。福伊尔已达死胡同。
他确实走到了死胡同。三十年来,他满足于像某种重甲生物一样,在存在的每个瞬间漂流,迟钝而冷漠……格利·福伊尔,典型的普通人;但现在,他在太空中漂流了一百七十天,而唤醒他的钥匙已在锁孔中。很快,它将转动,开启通往大灾难之门。
“诺玛德”号飞船漂浮在火星和木星之间的半途。无论是什么战争灾难摧毁了它,都将一艘长一百码、宽一百英尺的光滑钢制火箭,扭曲成了一副骨架,上面还残留着船舱、货舱、甲板和舱壁的残骸。船体上的巨大裂口在向阳面是耀眼的光斑,在背阴面则是星辰的霜冻斑点。“诺玛德”号飞船是一个失重的虚空,充满刺目的阳光和漆黑的阴影,冰冷而寂静。
残骸中充满了漂浮的冰冻碎片混合物,它们悬挂在被毁的飞船内部,像是一张爆炸瞬间的照片。碎石块之间微小的引力正缓慢地将它们聚集成簇,但这些簇又周期性地被残骸上唯一幸存者的穿行所撕裂,他就是格利弗·福伊尔,AS-128/I27:006。
他住在残骸中唯一完好无损的气密房间里,那是主甲板走廊的一个工具柜。柜子宽四英尺,深四英尺,高九英尺。它有巨人棺材那么大。六百年前,将一个人囚禁在如此大小的笼子里几周,曾被认为是最高级的东方酷刑。然而福伊尔在这个没有光亮的笼子里生存了五个月,二十天零四小时。
“你是谁?”
“格利·福伊尔是我的名。”
“你来自哪里?”
“地球是我的国家。”
“你现在在哪里?”
“深空是我的居所。”
“你要去哪里?”
“死亡是我的终点。”
在他为生存而战的第一百七十一天,福伊尔回答了这些问题并醒了过来。他的心怦怦直跳,喉咙灼烧。他在黑暗中摸索着与他同处一棺的气瓶,检查了一下。气瓶空了。必须立刻搬进另一个。因此,这一天将以一场额外的与死亡的小冲突开始,福伊尔以沉默的忍耐接受了这一切。
他在工具柜的架子上摸索,找到了一件破损的宇航服。这是“诺玛德”号上唯一的一件,福伊尔已不记得是在哪里或如何找到它的。他用应急喷雾封住了裂口,但无法重新填充或更换背上的空氧气筒。福伊尔穿上了宇航服。它能从工具柜里吸纳足够的空气,让他在真空中支撑五分钟……仅此而已。
福伊尔打开柜门,冲入太空的黑色冰霜中。柜子里的空气随他一起喷出,湿气凝结成一小片雪云,飘落到破损的主甲板走廊。福伊尔用力拖拽那个耗尽的气瓶,让它漂出柜子,然后弃之不顾。一分钟过去了。
他转身,推动自己穿过漂浮的碎片,朝压载舱的舱口移动。他没有跑;他的步态是自由落体和失重状态下独特的移动方式……用脚、肘和手对着甲板、墙壁和角落发力,像水下的蝙蝠一样在太空中缓慢地飞掠。福伊尔冲过舱口,进入背阴面的压载舱。两分钟过去了。
像所有飞船一样,“诺玛德”号用其气罐的质量作为压载物和加固物,这些气罐沿其龙骨纵向铺设,如同一个长长的木筏,两侧由迷宫般的管件连接。福伊尔花了一分钟断开一个气罐。他无法知道它是满的还是已经耗尽;是否会把它搬回他的工具柜后才发现它是空的,他的生命就此终结。每周一次,他都忍受着这场太空扑克游戏。
他耳边传来轰鸣声;宇航服里的空气正迅速变质。他猛地将沉重的气缸拉向压载舱口,低下头让它从头顶飞过,然后自己也跟了上去。他把气罐甩过舱口。四分钟过去了,他浑身颤抖,眼前发黑。他引导着气罐沿着主甲板走廊移动,把它推进了工具柜。
他猛地关上柜门,锁好,从架子上找到一把锤子,对着冰冻的气罐敲了三下以松开阀门。福伊尔冷酷地转动把手。他用尽最后的力气打开宇航服的头盔密封,以免在工具柜充满空气(如果这个罐子里有空气的话)时窒息在宇航服内……他昏了过去,就像他以前经常昏过去一样,从不知道这是否就是死亡。
“你是谁?”
“格利·福伊尔。”
“你来自哪里?”
“地球。”
“你现在在哪里?”
“太空。”
“你要去哪里?”
他醒了过来。他还活着。他没有浪费时间祈祷或感谢,而是继续着生存的事业。在黑暗中,他摸索着存放口粮的柜架。只剩下几包了。既然他已经穿着那件打补丁的宇航服,不如再冒一次真空的险,补充一下他的给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