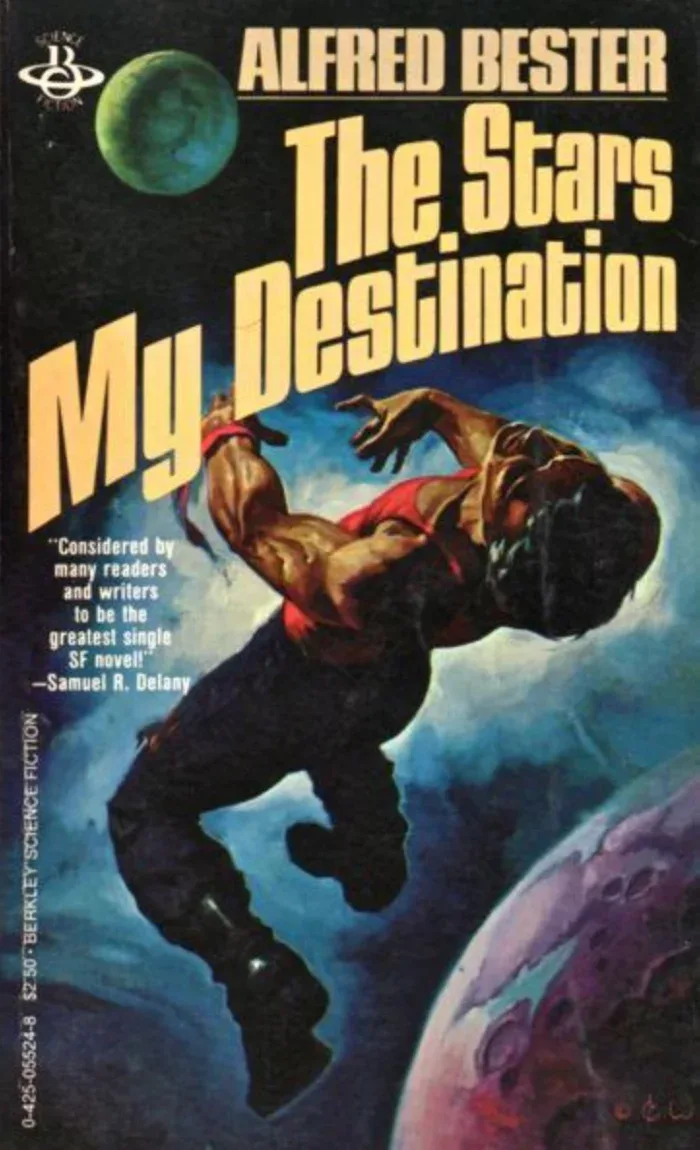第十一章
普雷斯蒂安家族位于中央公园的宅邸为迎接新年而灯火辉煌。迷人的古董电灯泡,灯丝呈之字形,尖端뾰족,散发着黄色的光芒。防瞬移迷宫已被移除,为这个特殊的场合敞开了大门。房屋内部通过门内一扇镶嵌珠宝的屏风与外面人群的目光隔开。
当氏族和分支中著名和近乎著名的人物乘车、乘马车、乘轿子,以各种形式的豪华交通工具抵达时,围观者们嗡嗡作响,惊叹不已。普雷斯蒂安家族的普雷斯蒂安本人站在门前,铁灰色头发,英俊,露出他那毒蛇般的微笑,欢迎社会各界人士光临他的开放日。一位名人刚踏进门,消失在屏风后,另一位更有名的人就乘坐着更神话般的交通工具嘎吱作响地驶来。
可乐家族乘坐一辆宣传车抵达。埃索家族(六子三女)乘坐一辆玻璃顶的灰狗巴士,气派非凡。但灰狗家族紧随其后(乘坐一辆爱迪生电动马车)抵达,门口传来阵阵笑声和戏谑。然而,当西屋公司的爱迪生从他那辆以埃索为燃料的汽油马车上下来,画上一个圆圈时,台阶上的笑声变成了轰鸣。
就在一群客人转身准备进入普雷斯蒂安家时,远处一阵骚动吸引了他们的注意。那是一阵隆隆声,气动冲头的剧烈咔嗒声,以及令人发指的金属咆哮声。它迅速逼近。围观人群的最外层让开了一条宽阔的通道。一辆重型卡车沿着通道隆隆驶来。六个人正从卡车后面往下扔木材。跟着他们的是二十人的队伍,将木材整齐地排成行。
普雷斯蒂安和他的客人们惊讶地看着。一架巨大的机器,咆哮着,砰击着,爬过枕木靠近。它身后留下了焊接钢制的平行铁轨。工人们用大锤和气动冲头将铁轨钉在木枕上。轨道以一个横扫的弧线铺设到普雷斯蒂安的门口,然后弯曲离开。咆哮的引擎和工人们消失在黑暗中。
“天哪!”普雷斯蒂安清晰地被听到说道。客人们从房子里涌出来观看。
远处传来尖锐的汽笛声。铁轨上走来一个人,骑着一匹白马,举着一面大红旗。他身后气喘吁吁地跟着一辆蒸汽机车,拉着一节观景车厢。火车停在普雷斯蒂安门前。一位列车员从车厢里跳下来,后面跟着一位普尔曼搬运工。搬运工摆好台阶。一位穿着晚礼服的女士和一位绅士走了下来。
“不会太久的,”绅士告诉列车员。“一小时后回来接我。”
“天哪!”普雷斯蒂安再次惊呼。
火车噗噗地开走了。那对夫妇走上台阶。
“晚上好,普雷斯蒂安,”绅士说道。“非常抱歉那匹马弄脏了您的场地,但纽约的老特许权仍然坚持火车前面要挂红旗。”
“福尔迈尔!”客人们喊道。
“谷神星的福尔迈尔!”围观者欢呼道。普雷斯蒂安的派对现在肯定成功了。
在巨大的天鹅绒和毛绒接待大厅里,普雷斯蒂安好奇地审视着福尔迈尔。福伊尔平静地承受着那锐利的铁灰色目光,同时点头微笑着回应着从堪培拉到纽约一路获得的狂热崇拜者。
‘控制,’他想。‘血液、内脏和大脑。在我疯狂地试图攻击沃加号之后,他在办公室里审问了我一个小时。他会认出我吗?你的脸很熟悉,普雷斯蒂安,’福尔迈尔说。‘我们以前见过面吗?’
“我至今晚才有幸见到一位福尔迈尔,”普雷斯蒂安含糊地回答道。福伊尔训练自己读懂人心,但普雷斯蒂安坚硬、英俊的脸庞难以捉摸。两人面对面站着,一个超然而被迫,另一个矜持而坚定,他们看起来像一对即将熔化的白热青铜雕像。
“我听说你吹嘘自己是个暴发户,福尔迈尔。”
“是的。我效仿了第一位普雷斯蒂安。”
“真的吗?”
“你会记得,他吹嘘说是在第三次世界大战期间靠血浆黑市发家致富的。”
“那是第二次战争,福尔迈尔。但我们家族的伪君子从不承认他。那时的名字是佩恩。”
“我不知道。”
“在你改名为福尔迈尔之前,你那不幸的名字是什么?”
“是普雷斯蒂安。”
“真的吗?”那毒蛇般的微笑承认了这一击。“你声称与我们家族有关系?”
“到时候我会声称的。”
“什么程度的关系?”
“比如说……血缘关系。”
“真有趣。我察觉到你对血有某种迷恋,福尔迈尔。”
“毫无疑问是家族弱点,普雷斯蒂安。”
“你乐于玩世不恭,”普雷斯蒂安带着几分玩世不恭说道,“但你说的是实话。我们一直对血和金钱有着致命的弱点。这是我们的恶习。我承认。”
“我也一样。”
“对血和金钱的热情?”
“确实如此。非常热情。”
“毫无怜悯,毫无宽恕,毫无虚伪?”
“毫无怜悯,毫无宽恕,毫无虚伪。”
“福尔迈尔,你真是个深得我心的年轻人。如果你不声称与我们家族有关系,我将被迫收养你。”
“你太迟了,普雷斯蒂安。我已经收养你了。”
普雷斯蒂安挽住福伊尔的胳膊。“你必须被介绍给我的女儿,奥利维亚夫人。请允许我?”
他们穿过接待大厅。胜利感在福伊尔心中涌动:他不知道。他永远不会知道。接着疑虑袭来:但我永远不知道他是否知道。他是坩埚钢。他可以教我一两招控制术。
熟人们向福尔迈尔打招呼。
“你在上海搞的那场骗局真是精彩。”
“罗马的狂欢节太棒了,不是吗?你听说那个出现在西班牙阶梯上的燃烧的人了吗?”
“我们在伦敦找过你。”
“那入口真是太棒了,”哈里·舍温-威廉姆斯喊道。“把我们都比下去了,天哪。让我们看起来像一群该死的小气鬼。”
“你失态了,哈里,”普雷斯蒂安冷冷地说。“你知道我家里不允许说脏话。”
“对不起,普雷斯蒂安。马戏团现在在哪儿,福尔迈尔?”
“我不知道,”福伊尔说。“稍等。”
人群聚集起来,咧嘴笑着期待着最新的福尔迈尔傻事。他掏出一块白金表,啪地一声打开表盖。表盘上出现了一个仆人的脸。
“啊……不管你叫什么……我们现在住在哪儿?”
回答声细小而尖锐。“您下令将纽约作为您的永久住所,福尔迈尔。”
“哦?我说了吗?然后呢?”
“我们买下了圣帕特里克大教堂,福尔迈尔。”
“那在哪儿?”
“老圣帕特里克教堂,福尔迈尔。在第五大道和以前的博斯街。我们把营地搭在里面了。”
“谢谢。”
福尔迈尔合上白金猎表。“我的地址是纽约老圣帕特里克教堂:对于那些被取缔的宗教,有一点可以说……至少他们建造的教堂足够大,可以容纳一个马戏团。”
奥利维亚·普雷斯蒂安坐在一个讲台上,被仰慕者们簇拥着。她是一位雪女,一位冰公主,有着珊瑚色的眼睛和珊瑚色的嘴唇,傲慢,遥不可及,美丽动人。福伊尔看了她一眼,在她那只能看见电磁波和红外线的盲目目光前,困惑地低下了眼睛。他的心开始跳得更快。
“别傻了!”他绝望地想。“控制住自己。这可能很危险……”
他被介绍了;一个沙哑、银铃般的声音对他说话;一只冰凉、纤细的手递给了他;但这只手似乎在他手中爆炸,带来一阵电击。这几乎是一种相互认出的开始。
‘什么的?她是个象征。梦中公主……遥不可及……控制!’
他挣扎得太厉害,以至于几乎没意识到自己已被优雅而冷漠地打发走了。他简直不敢相信。他站在那里,像个乡巴佬一样张口结舌。
“什么?你还在这里,福尔迈尔?”
“我简直不敢相信我被解雇了,奥利维亚夫人。”
“很难说,但我恐怕你挡着我朋友们的路了。”
“我习惯不了被解雇。(不。不。全错了。)至少被一个我想当作朋友的人。”
“别烦人了,福尔迈尔。请下去吧。”
“我怎么得罪你了?”
“得罪我?现在你变得荒谬了。”
“奥利维亚夫人……(天哪!我说不出任何正确的话吗?罗宾在哪里?)我们能重新开始吗,请?”
“如果你想表现得笨拙,福尔迈尔,你做得非常成功。”
“请再给我你的手。谢谢。我是谷神星的福尔迈尔。”
“好吧。”她笑了。“我承认你是个小丑。现在请下去吧。我相信你能找到人逗乐。”
“这次发生了什么事?”
“说真的,先生,你想让我生气吗?”
“不。(是的,我是。想以某种方式触动你……穿透那层冰。)第一次我们握手时……很激烈。现在什么都没有了。发生了什么事?”
“福尔迈尔,”奥利维亚疲惫地说,“我承认你有趣、有独创性、机智、迷人……什么都行,只要你肯走开。”
他踉跄着走下讲台。“婊子。婊子。婊子。不。她就是我梦中的那个梦。那座冰封的山峰,等待被围攻和占领。围攻……侵入……蹂躏……逼她下跪……”
他迎面撞上了索尔·达格纳姆。
他僵住了,强行控制着血液和内脏。
“啊,福尔迈尔,”普雷斯蒂安说。“这位是索尔·达格纳姆。他只能给我们三十分钟,而且他坚持要花其中一分钟和你在一起。”
他知道吗?他是不是派人去叫达格纳姆来确认?攻击。永远大胆。
“你脸上怎么了,达格纳姆?”福尔迈尔带着超然的好奇问道。
死神般的头颅笑了笑。“我还以为我很有名呢。辐射中毒。我发热了。曾经有人说‘比手枪还烫’。现在他们说‘比达格纳姆还烫’。”致命的眼睛扫视着福伊尔。“你那个马戏团背后是什么?”
“对臭名昭著的热情。”
“我自己也是伪装的老手。我认得那些迹象。你的勾当是什么?”
“迪林杰会告诉卡彭吗?”
福伊尔回以微笑,开始放松下来,抑制着胜利的喜悦。“我把他们俩都比下去了。你看起来更开心了,达格纳姆。”
他立刻意识到自己失言了。
达格纳姆立刻抓住了话柄。“什么时候更开心?我们以前在哪儿见过?”
“不是比什么时候开心;是比我开心。”
福伊尔转向普雷斯蒂安。“我疯狂地爱上了奥利维亚夫人!”
“索尔,你的半小时到了。”
达格纳姆和普雷斯蒂安,分别站在福伊尔的两侧,转过身。一位高挑的女人走近,穿着翠绿色的晚礼服,她红色的头发闪闪发光。是吉斯贝拉·麦昆。他们的目光相遇了。在震惊的情绪涌上他脸庞之前,福伊尔转身,跑了六步到他看到的第一扇门,打开门冲了进去。
门在他身后砰地关上了。他身处一条短而盲目的走廊。传来一声咔哒声,停顿了一下,然后一个罐装的声音礼貌地说:“您已侵入本住宅的私人区域。请退后。”
福伊尔喘着气,挣扎着。
“您已侵入本住宅的私人区域。请退后。”
“我从不知道……以为她死在那儿了……她认出我了……”
“您已侵入本住宅的私人区域。请退后。”
“我完了……她永远不会原谅我……肯定现在就告诉达格纳姆和普雷斯蒂安了。”
接待大厅的门开了,一瞬间,福伊尔以为看到了自己燃烧的影像。接着他意识到自己看到的是吉斯贝拉燃烧的头发。她一动不动,只是站在那里,带着狂怒胜利的微笑看着他。他挺直了身子。
“天哪,我不会抱怨着倒下的。”
福伊尔从容地走出走廊,挽起吉斯贝拉的手臂,带她回到接待大厅。他甚至懒得环顾寻找达格纳姆或普雷斯蒂安。他们会在适当的时候,带着武力和武器出现。他对吉斯贝拉微笑;她也回以微笑,仍然带着胜利的神情。
“谢谢你跑掉,格利。我从没想过会这么令人满意。”
“逃跑?我亲爱的吉兹!”
“嗯?”
“我无法告诉你今晚你看起来有多美。我们从古夫尔·马特尔走了很长一段路,不是吗?”福伊尔示意舞厅。“跳舞吗?”
她惊讶于他的镇定,睁大了眼睛。她任由他护送她到舞厅,并将她拥入怀中。
“顺便问一下,吉兹,你是怎么设法逃离古夫尔·马特尔的?”
“达格纳姆安排的。所以你现在跳舞了,格利?”
“我跳舞,说四种蹩脚的语言,学习科学和哲学,写可怜的诗歌,用愚蠢的实验把自己炸飞,像个傻瓜一样击剑,像个丑角一样拳击……总之,我是臭名昭著的谷神星福尔迈尔。”
“不再是格利弗·福伊尔了。”
“只对你,亲爱的,还有你告诉过的任何人。”
“就达格纳姆。你后悔我搞砸了吗?”
“你和我一样身不由己。”
“不,我没有。你的名字就从我嘴里冒出来了。你会付多少钱让我闭嘴?”
“别傻了,吉兹。这次意外会让你赚大约一千七百九十八万信用点。”
“你什么意思?”
“我告诉过你,等我了结沃加之后,剩下的都给你。”
“你结束了沃加?”她惊讶地说。
“不,亲爱的,是你结束了我。但我会信守承诺。”
她笑了。“慷慨的格利弗·福伊尔。真正慷慨些吧。格利。跑吧。逗我乐一下。”
“像老鼠一样尖叫?我不知道怎么做,吉兹。我受过狩猎训练;仅此而已。”
“而我杀了那只老虎。给我一个满足感吧,格利。说你离沃加很近了。我在你离终点只有半步之遥时毁了你。是吗?”
“我真希望可以,吉兹,但我不能。我毫无头绪。我今晚本来想在这里找到另一条线索。”
“可怜的格利。也许我能帮你摆脱这个困境。我可以说……哦……我弄错了……或者开个玩笑……你其实不是格利弗·福伊尔。我知道怎么迷惑索尔。我能做到,格利……如果你还爱我的话。”
他低头看着她,摇了摇头。“我们之间从来都不是爱,吉兹。你知道的。我太专一了,只能做一个猎人。”
“太专一了,只能做个傻瓜!”
“你是什么意思,吉兹……‘达格纳姆安排让你离开古夫尔·马特尔’……‘你知道怎么迷惑索尔·达格纳姆’?你跟他有什么关系?”
“我为他工作。我是他的信使之一。”
“你的意思是他敲诈你?威胁说如果你不……就把你送回去?”
“不。我们一见面就合得来。他开始是抓我;我最后是抓住了他。”
“你什么意思?”
“你猜不到吗?”
他盯着她。她的眼睛蒙着一层纱,但他明白了。“吉兹!和他?”
“是的。”
“但是怎么会?他——”
“有预防措施。这……我不想谈这个,格利。”
“对不起。他回来得真慢。”
“回来?”
“达格纳姆。带着他的军队。”
“哦。是的,当然。”吉斯贝拉又笑了起来,然后用低沉而愤怒的语气说道。“你不知道你一直走在什么样的钢丝上,格利。如果你乞求、贿赂或者试图讨好我……天哪,我会毁了你。我会告诉全世界你是谁……向屋顶大声尖叫。”
“你在说什么?”
“索尔不会回来了。他不知道。你可以自己下地狱去。”
“我不信你。”
“你觉得他需要这么长时间才能抓到你吗?索尔·达格纳姆?”
“但你为什么不告诉他?在我那样抛弃你之后……”
“因为我不想他和你一起下地狱。我说的不是沃加。我说的是别的东西,PyrE。那就是他们追捕你的原因。那就是他们想要的东西。二十磅PyrE。”
“那是什么?”
“你打开保险箱时,里面有没有一个小盒子?用I.L.I.做的……同位素铅合金?”
“是的。”
“I.L.I.盒子里是什么?”
“二十块看起来像压缩碘晶体的块状物。”
“你把那些块状物怎么处理了?”
“送了两块出去分析。没人能弄清它们是什么。我正试着在我的实验室里分析第三块……当我不为公众扮小丑的时候。”
“哦,你是吗?为什么?”
“我在长大,吉兹。”福伊尔温和地说。“没费多大劲就弄明白那是普雷斯蒂安和达格纳姆想要的东西。”
“你把剩下的块状物藏在哪儿了?”
“在一个安全的地方。”
“它们不安全。它们永远不可能安全。我不知道PyrE是什么,但我知道那是通往地狱的路,我不想索尔走上那条路。”
“你那么爱他?”
“我那么尊敬他。他是第一个向我展示双重标准借口的男人。”
“吉兹,PyrE到底是什么?你知道。”
“我猜到了。我把我听到的暗示拼凑起来了。我有个想法。我可以告诉你,格利,但我不会。”她脸上火热的神情光彩照人。“这次我抛弃你。我让你在黑暗中无助地悬着。尝尝滋味吧,小子!享受吧!”
她挣脱开他,横扫过舞厅地板。就在这时,第一批炸弹落了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