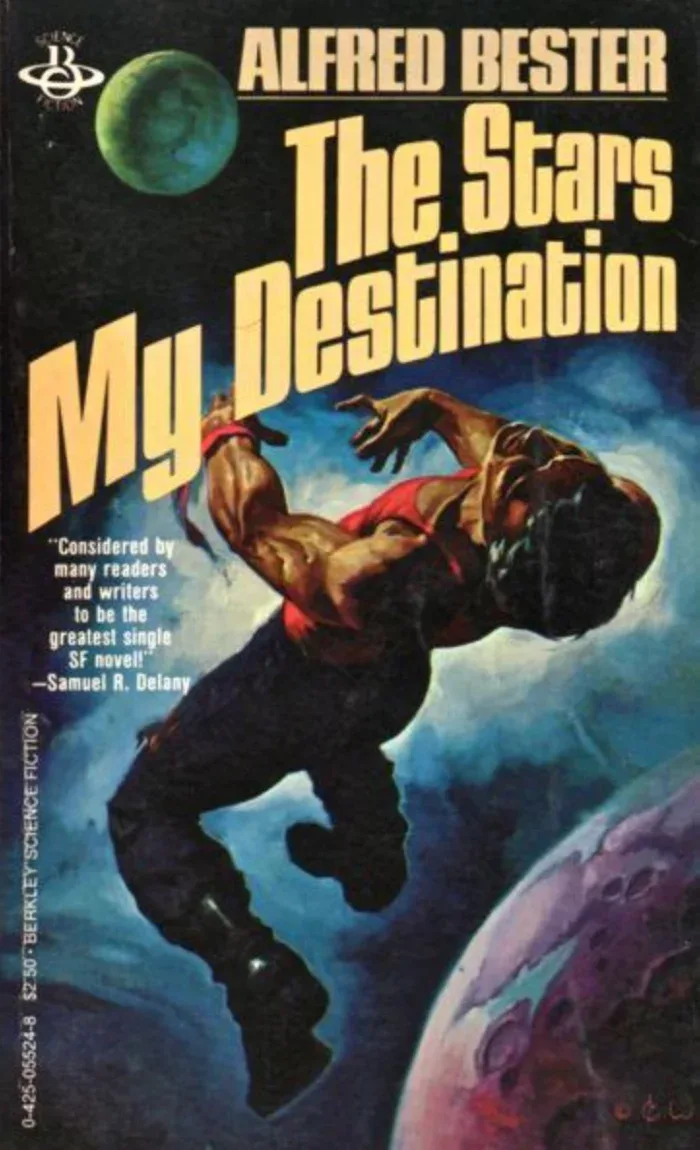第十章
“在上海的化装舞会上,谷神星的福尔迈尔以丢勒的《死神与少女》中的死神形象出现,与一位身着透明面纱的耀眼尤物一同登场,令社会为之震动。一个将女性禁锢在深闺之中、并将佩内明德家族1920年代的礼服视为过度大胆的维多利亚时代社会受到了冲击。但当福尔迈尔透露那女性是一个华丽的人造人时,舆论立刻反转,对他有利。社会对这种欺骗感到高兴。裸体在人类身上是可耻的,在人造人身上仅仅是一种无性的好奇。”
午夜时分,福尔迈尔将人造人拍卖给了舞会上的绅士们。
“钱捐给慈善机构吗,福尔迈尔?”
“当然不。你知道我的口号:一分钱也不给熵。这位昂贵可爱的生物有人出一百信用点吗?一百,先生们?她美丽动人,适应性强。两百?谢谢。三百五?谢谢。我出——五百?八百?谢谢。还有人出价吗,为这个四英里马戏团常驻天才的非凡产品?她会走路。她会说话。她会适应。她被调教成会对最高出价者做出回应。九百?还有人出价吗?都结束了吗?都完了吗?成交,耶鲁勋爵以九百信用点购得。”
掌声雷动,同时传来惊骇的计算声:“天哪!那样的人造人肯定花了九万!他怎么负担得起?”
“请把钱交给那个人造人吧,耶鲁勋爵?她会做出适当的回应。女士们先生们,直到我们在罗马再会……午夜时分在博尔盖塞宫。新年快乐。”
福尔迈尔早已离开,耶鲁勋爵才发现,令他和其他单身汉们欣喜的是,一个双重骗局被实施了。那个人造人实际上是一个活生生的人类,美丽动人且适应性极强。她对九百信用点做出了极好的回应。这个诡计成了年度吸烟室里的热门故事。男士们急切地等待着向福尔迈尔表示祝贺。
但福伊尔和罗宾·韦恩斯伯里正经过一个用七种语言写着“加倍你的琼特或加倍退款”的招牌,进入了谢尔盖·奥雷尔博士——天界颅脑能力放大器——的商场。
候诊室里装饰着色彩鲜艳的大脑图表,展示奥雷尔医生如何用膏药、拔罐、香脂和电解法使大脑容量加倍,否则双倍退款。他还用抗热泻药使记忆力加倍,用滋补强壮剂提升道德,并用奥雷尔的生肌药膏调整所有痛苦的心灵。
候诊室空无一人。福伊尔冒险打开一扇门。他和罗宾瞥见了一个长长的医院病房:福伊尔厌恶地咕哝了一声。
“一个‘雪’窝点。早该知道他也会经营一个毒品窝点。”
这个窝点迎合的是“疾病收集者”,最无可救药的神经症成瘾者。他们躺在病床上,轻微地患着非法诱发的副麻疹、副流感、副疟疾;穿着浆得笔挺的白色制服的护士们尽心尽力地照顾着他们,而他们则贪婪地享受着非法疾病和由此带来的关注。
“看看他们,”福伊尔轻蔑地说。“恶心。如果说有什么比宗教瘾君子更肮脏的,那就是疾病鸟。”
“晚上好,”一个声音在他们身后说道。
福伊尔关上门转过身。谢尔盖·奥雷尔医生鞠躬行礼。这位好医生穿着医疗家族经典的白色帽子、长袍和外科口罩,显得干练而无菌,尽管他只是冒名顶替属于这个家族。他身材矮小,皮肤黝黑,橄榄色的眼睛,仅凭名字就能认出是俄罗斯人。一个多世纪的琼特使得世界各地的人口如此混杂,以至于种族特征正在消失。
“没想到除夕夜你还开门营业,”福伊尔说。
“我们的俄罗斯新年要晚两周,”奥雷尔医生回答道。“请这边走。”
他指了指一扇门,然后“砰”地一声消失了。门后是一段长长的楼梯。当福伊尔和罗宾开始上楼时,奥雷尔医生出现在他们上方。“这边请。哦……稍等。”
他消失了,又出现在他们身后。“你忘了关门。”
他关上门,再次瞬移。这次他重新出现在楼梯的最高处。“请进。”
“炫耀,”福伊尔咕哝道:“加倍你的瞬移或加倍退款。不过,他速度确实很快。我得更快些。”
他们进入了诊疗室。那是一个玻璃屋顶的顶层公寓。墙壁上挂满了华丽但过时的医疗器械:一个镇静浴盆,一把用于对精神分裂症患者进行电击治疗的电椅,一台用于追踪精神病模式的心电图分析仪,旧的光学和电子显微镜。
那个江湖医生在办公桌后等着他们。他瞬移到门口,关上门,瞬移回办公桌前,鞠躬,示意坐下,瞬移到罗宾身后为她拉开椅子,瞬移到窗前调整百叶窗,瞬移到电灯开关处调整灯光,然后重新出现在办公桌后。
“一年前,”他微笑着说,“我根本不会琼特。然后我发现了秘密,那有益健康的清洁剂,它……”
福伊尔用舌头触碰连接在他牙齿神经末梢的控制板。他加速了。他从容起身,走向办公桌后那个慢动作的人影——“布洛克-呼-瓦-啊-呜呜呜”,掏出一根沉重的警棍,科学地猛击奥雷尔的额头,震荡了他的额叶,击晕了他的琼特中枢。他把那个江湖医生抱起来,绑在电椅上。这一切大约花了五秒钟。对罗宾·韦恩斯伯里来说,那是一片模糊的动作。
福伊尔减速了。那个江湖医生睁开眼睛,动了动,发现自己身在何处,又惊又怒地跳了起来。
“你是谢尔盖·奥雷尔,沃加号上的药剂师助手,”福伊尔平静地说。“你在2336年9月16日登上了沃加号。”
愤怒和困惑变成了恐惧。
“九月十六日,你经过一艘残骸。在小行星带附近。那是诺玛德号的残骸。她发出了求救信号,而沃加号却从她身边经过。你任由她漂流等死。为什么?”
奥雷尔转动着眼珠,但没有回答。
“是谁下令从我身边经过的?是谁愿意让我腐烂等死?”
奥雷尔开始胡言乱语。
“沃加号上有谁?谁和你一起出海的?谁是船长?我会得到答案的。别以为我不会,”福伊尔带着冷静的凶残说道。“我会买下来,或者从你身上把它撕下来。为什么我被留下等死?谁让你让我死的?”
奥雷尔尖叫起来。“我不能谈论——等等!我会告诉——”他瘫软下去。
福伊尔检查了尸体。“死了,”他咕哝道。“就在他准备开口的时候。就像福雷斯特一样。”
“被谋杀了。”
“不。我从未碰过他。是自杀。”福伊尔毫无幽默感地咯咯笑起来。
“你疯了。”
“不,是觉得好笑。我没有杀死他们;我迫使他们自杀。”
“这算什么胡话?”
“他们被施加了交感神经阻滞。你知道S.B.s吗,姑娘?情报部门用它们对付间谍特工。拿走某部分你不想被泄露的信息。把它和控制自动呼吸和心跳的交感神经系统连接起来。一旦对象试图泄露那些信息,阻滞就会发生,心脏和肺停止跳动,人就死了,你的秘密就保住了。特工不必担心为了避免酷刑而自杀;这已经替他做好了。”
“对这些人也这么做了?”
“显然。”
“但是为什么?”
“我怎么知道。偷渡难民不是答案。沃加号肯定在经营比那更糟糕的勾当,才会采取这种预防措施。但我们有个问题。我们最后的线索是罗马的波吉。安吉洛·波吉,沃加号上的厨师助手。我们怎么能从他那里获取信息而不——”他停了下来。
他的影像站在他面前,沉默着,不祥地,脸燃烧着血红色,衣服冒着火焰。
福伊尔瘫痪了。他吸了口气,用颤抖的声音说。“你是谁?你——”影像消失了。
福伊尔转向罗宾,舔了舔嘴唇。“你看到了吗?”
她的表情回答了他。
“是真的吗?”
她指向谢尔盖·奥雷尔的办公桌,影像曾站在桌旁。桌上的纸张着火了,正噼啪作响地燃烧着。福伊尔后退一步,仍然惊恐而困惑。他用手擦了擦脸。手上湿漉漉的。
罗宾冲到桌前,试图扑灭火焰。她拿起一沓沓纸张和信件,无助地拍打着。福伊尔一动不动。
“我灭不了,”她最后喘着气说。“我们得离开这里。”
福伊尔点点头,然后强打精神,恢复了力量和决心。“罗马,”他嘶哑地说。“我们瞬移到罗马。这一切一定有什么解释。我会找到的,天哪!在此期间我不会放弃。罗马。走,姑娘!瞬移!”
自中世纪以来,西班牙阶梯一直是罗马腐败的中心。从西班牙广场向上延伸至博尔盖塞别墅花园,形成一条宽阔而漫长的阶梯,西班牙阶梯上,过去是,现在是,将来也永远充斥着罪恶。皮条客们懒散地倚靠在阶梯上,妓女、变态者、女同性恋者、娈童。他们傲慢无礼,炫耀着自己,嘲笑着偶尔经过的正派人士。
西班牙阶梯在二十世纪末的核战争中被摧毁。它们被重建,又在二十一世纪的世界复兴战争中再次被摧毁。它们再次被重建,这一次覆盖上了防爆水晶,将阶梯变成了一个阶梯状的拱廊。拱廊的穹顶遮挡了济慈故居临终房间的视线。游客再也无法透过狭窄的窗户看到垂死诗人眼中最后的景象。现在他们看到的是西班牙阶梯烟雾缭绕的穹顶,透过它看到下方索多玛和蛾摩拉扭曲的身影。
阶梯拱廊夜间灯火通明,这个除夕夜更是混乱不堪。一千年来,罗马一直以轰炸的方式迎接新年……鞭炮、火箭、鱼雷、枪声、瓶子、鞋子、旧锅旧盆。罗马人会积攒数月的垃圾,以便在午夜钟声敲响时从顶楼窗户扔出去。阶梯内部烟花的轰鸣声,以及碎片撞击拱廊屋顶的噼啪声震耳欲聋,此时福伊尔和罗宾·韦恩斯伯里正从博尔盖塞宫的狂欢节上下来。
他们仍然穿着戏服;福伊尔穿着切萨雷·博尔贾那鲜艳的红黑色紧身裤和短上衣,罗宾则穿着卢克雷齐娅·博尔贾那镶嵌着银饰的长袍。他们戴着怪诞的天鹅绒面具。他们文艺复兴时期的服装与周围现代服饰的对比引来了嘲笑和嘘声。就连经常光顾西班牙阶梯的洛博人——那些不幸的惯犯,他们四分之一的大脑因前额叶切除术而被烧毁——也从他们沉闷的冷漠中被惊醒,凝视着。当这对夫妇走下拱廊时,人群在他们周围沸腾着。
“波吉,”福伊尔平静地喊道。“安吉洛·波吉?”
一个鸨母对他大声喊着解剖学上的污言秽语。
“波吉?安吉洛·波吉?”福伊尔面无表情。“我听说晚上能在阶梯上找到他。安吉洛·波吉?”
一个妓女诽谤了他的母亲。
“安吉洛·波吉?谁带我找到他,给十个信用点。”
福伊尔被伸出的手环绕着,有的肮脏,有的芬芳,全都贪婪。他摇了摇头。“先让我看到。”
罗马人的怒火在他周围噼啪作响。
“波吉?安吉洛·波吉?”
在西班牙阶梯上闲逛了六周之后,彼得·杨-尤维尔上尉终于听到了他希望听到的话。六周来,他乏味地冒充安吉洛·波吉——沃加号上早已死去的厨师助手——的身份,终于有了回报。这本是一场赌博,最初的风险始于情报部门向杨-尤维尔上尉报告说,有人正在谨慎地打听普雷斯蒂安·沃加号船员的情况,并为此支付高昂的费用。
“这是个长线赌注,”杨-尤维尔曾说过,“但格利弗·福伊尔,AS-128/127:006,确实疯狂地试图炸毁沃加号。而二十磅PyrE值得冒这个长线风险。”
现在他摇摇摆摆地走上楼梯,走向那个穿着文艺复兴服装、戴着面具的男人。他用腺体注射增加了四十磅体重。他通过饮食调理使肤色变深。他的面容,从未带有东方特征,反而更像古代美洲印第安人的鹰隼线条,稍加肌肉控制就轻易地呈现出一种不可靠的模式。
这位情报人员摇摇摆摆地走上西班牙阶梯,一个身材肥胖、面带盗窃神情的厨师。他向福伊尔递出一包脏兮兮的信封。
“淫秽图片,先生?地下室基督徒,跪着,祈祷,唱圣歌,亲吻十字架?非常下流。非常淫秽,先生。招待您的朋友……刺激女士们。”
“不,”福伊尔推开色情物品。“我在找安吉洛·波吉。”
杨-尤维尔微不可察地发出信号。他在阶梯上的手下开始拍摄和记录这次访谈,同时并未停止拉皮条和卖淫。内行星武装部队情报堂的暗语像一阵微小的抽搐、吸气、手势、姿态、动作的冰雹一样围绕着福伊尔和罗宾挥舞着。那是古老的中国手语,通过眼睑、眉毛、指尖和极其细微的身体动作来表达。
“先生?”杨-尤维尔喘着气说。
“安吉洛·波吉?”
“是的,先生。我是安吉洛·波吉。”
“沃加号上的厨师助手?”
福伊尔预料到对方会像福雷斯特和奥雷尔那样惊恐万分——他终于明白了原因——于是伸出手抓住了杨-尤维尔的手肘。
“是吗?”
“是的,先生,”杨-尤维尔平静地回答。“我能为您效劳吗?”
“也许这一个能挺过去,”福伊尔对罗宾低语道。“他不害怕。也许他知道绕过障碍的方法。”
“我想从你这里得到信息,波吉。我想买下你所有的信息。任何你有的信息。开个价吧。”
“但是,先生!我已年迈,经验丰富。我不是可以批量购买的。我必须逐项收费。请您选择,我会报价。您想要什么?”
“你在2336年9月16日登上了沃加号?”
“这件东西的价格是十信用点。”
福伊尔毫无笑意地笑了笑,付了钱。
“是的,先生。”
“我想知道你经过小行星带附近时遇到的一艘船。诺玛德号的残骸。你在九月十六日经过了她。诺玛德号发出了求救信号,而沃加号却从她身边经过。是谁下的命令?”
“啊,先生!”
“是谁下的那个命令,为什么?”
“您为什么问,先生?”
“别管我为什么问。开价,然后说。”
“我必须知道问题的原因才能回答,先生。”杨-尤维尔油腻地笑了笑。“为了谨慎起见,我会降价。您为什么对沃加号和诺玛德号以及这起令人震惊的太空遗弃事件感兴趣?难道您就是那个遭受如此残酷对待的不幸者吗?”
‘他不是意大利人!他的口音完美,但是,说话模式完全不对。没有意大利人会那样组织句子。’罗宾提示道。
福伊尔警觉地绷紧了身体。杨-尤维尔的眼睛,经过训练能够从细微之处察觉和推断,捕捉到了态度的变化。他立刻意识到自己不知何故露了马脚。他急切地向他的手下发出信号。
一场白热化的斗殴在西班牙阶梯上爆发了。瞬间,福伊尔和罗宾被卷入尖叫、挣扎的人群中。情报堂的成员们是这种OP-I战术的大师,这种战术旨在智胜一个瞬移的世界。他们分秒不差的时机可以打乱任何人的阵脚,并剥光他以进行身份识别。他们的成功建立在一个简单的事实上:在意外攻击和防御反应之间总会有一个识别滞后。在那个滞后的时间内,情报堂保证能阻止任何人自救。
在五分之三秒内,福伊尔被打、被膝撞、额头被猛击、摔倒在台阶上并被摆成大字形。面具被扯掉,部分衣服被撕破,他赤裸裸地、无助地等待着身份识别摄像机的蹂躏。然后,在堂口历史上第一次,他们的计划被打断了。
一个人出现了,跨立在福伊尔的身体上……一个巨大的男人,脸上纹着可怕的图案,衣服冒着烟,燃烧着。这个幽灵如此骇人,以至于队员们都停下来呆呆地看着。阶梯上的人群对着这可怕的景象发出一阵嚎叫。
“燃烧的人!看!燃烧的人!”
“但那是福伊尔,”杨-尤维尔低语道。
大约四分之一分钟,那个幽灵站在那里,沉默着,燃烧着,用盲目的眼睛凝视着。然后它消失了。那个被摆成大字形躺在地上的人也消失了。他变成了一道闪电般的模糊动作,穿梭于队员之间,定位并摧毁了摄像机、录音机以及所有身份识别设备。然后那模糊的身影抓起穿着文艺复兴礼服的女孩,消失了。
西班牙阶梯再次恢复生机,痛苦地,仿佛从噩梦中挣扎出来。困惑的情报人员围拢在杨-尤维尔周围。
“看在上帝的份上,那是什么,尤?”
“我想那是我们的人。格利弗·福伊尔。你看到那张纹身脸了。”
“还有那燃烧的衣服!全能的基督!”
“看起来像火刑柱上的女巫。”
“但如果那个燃烧的人是福伊尔,我们刚才到底在浪费时间对付谁?”
“我不知道。突击队有没有一个他们没告诉我们的情报部门?”
“为什么是突击队,尤?”
“你看到那个好好先生加速的样子了,不是吗?他毁掉了我们做的每一份记录。”
“我还是不敢相信我的眼睛。”
“哦,你当然可以相信你没看到的。那是最高机密的突击队技术。他们把人拆开,重新布线,重新调整。我得和火星总部核实一下,看看突击队是不是在进行平行调查。”
“陆军会告诉海军吗?”
“他们会告诉情报部门,”杨-尤维尔愤怒地说。“这个案子已经够紧急了,不能再有管辖权争执。还有一件事:在演习中没有必要粗暴对待那个女孩。那是没有纪律的,也是不必要的。”
杨-尤维尔停顿了一下,这一次没有注意到周围人意味深长的目光。“我必须查明她是谁,”他梦幻般地补充道。
“如果她也被重新改装过,那就有意思了,尤,”一个平淡的声音说道,明显没有任何暗示。“男孩遇见突击队员。”
杨-尤维尔脸红了。“好吧,”他脱口而出。“我很透明。”
“只是重复,尤。你所有的罗曼史都以同样的方式开始。‘没必要粗暴对待那个女孩……’然后是多莉·奎克,简·韦伯斯特,格温·罗杰,玛丽昂——”
“请不要提名字!”一个震惊的声音打断道。“罗密欧会告诉朱丽叶吗?”
“你们明天都要去执行厕所任务,”杨-尤维尔说。“我绝不容忍这种下流的违抗命令。不,不是明天;但一旦这个案子结束。”
他鹰隼般的脸沉了下来。“我的天,真是一团糟!你们能忘记福伊尔像个燃烧的火把一样站在那里吗?但他现在在哪里?他在干什么?这一切意味着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