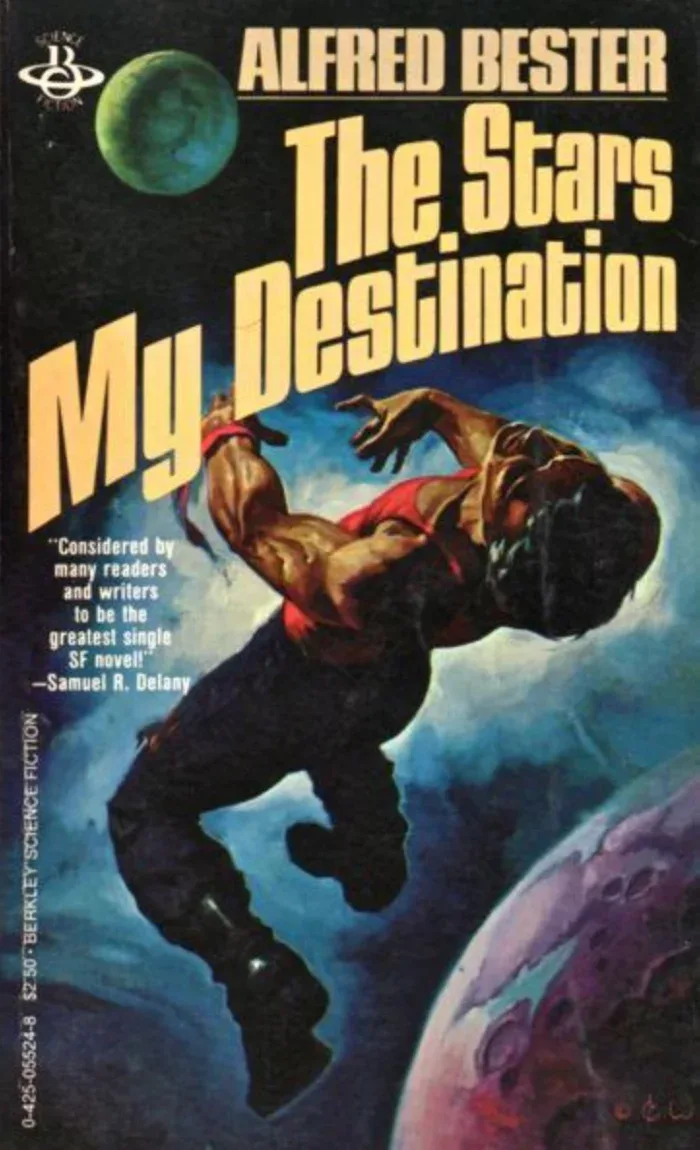第九章
除夕夜,谷神星的杰弗里·福尔迈尔向社会发起了冲击。他首先出现在堪培拉总督府的舞会上,午夜前还有半小时。这是一场极其正式的活动,充满了色彩和盛况,因为在正式场合,社会人士习惯穿着其家族创立或商标注册那年流行的晚礼服。
因此,莫尔斯家族(电话和电报)穿着十九世纪的长礼服,女人们则穿着维多利亚时代的裙撑裙。斯科达家族(火药和枪支)则追溯到十八世纪晚期,穿着摄政时期的紧身裤和衬裙。大胆的佩内明德家族(火箭和反应堆),起源于1920年代,穿着燕尾服,女人们则毫无羞耻地穿着古董沃斯和曼波切尔礼服的低胸装,露出腿、胳膊和脖子。
谷神星的福尔迈尔身着晚礼服出现,非常现代,非常黑,唯一的点缀是他肩上的白色旭日图案,那是谷神星家族的商标。与他同来的是罗宾·韦恩斯伯里,穿着闪闪发光的白色礼服,纤细的腰肢紧束在鲸骨胸衣里,礼服的臀垫突显出她修长笔直的背部和优雅的步伐。
黑白对比如此引人注目,以至于一名勤务兵被派去在《贵族与专利年鉴》中核查旭日商标。他回来报告说,那是谷神星矿业公司的商标,成立于2250年,旨在开采谷神星、帕拉斯和小行星灶神星的矿产资源。
资源从未显现,谷神星家族曾一度衰落,但从未灭绝。显然,它现在正在复兴。
“福尔迈尔?那个小丑?”
“是的。四英里马戏团。大家都在谈论他。”
“那是同一个人吗?”
“不可能。他看起来像人。”
社会人士好奇而警惕地围拢在福尔迈尔周围。
“他们来了,”福伊尔对罗宾低语道。
“放松。他们想要轻松愉快的氛围。只要有趣,他们什么都能接受。保持联系。”她提示道。
“你就是那个带着马戏团的可怕男人吗,福尔迈尔?”
“当然是你。微笑。”她提示道。
“是我,夫人。您可以摸摸我。”
“哎呀,你居然还挺自豪的。你为你的坏品味感到自豪吗?”
“如今的问题在于是否有任何品味可言。”她提示道。
“今天的问题在于是否有任何品味可言。我想我很幸运。”
“幸运但极其不雅。”
“不雅但并非乏味。”
“而且可怕但令人愉快。你现在为什么不蹦蹦跳跳呢?”
“我正‘受影响’呢,夫人。”
“哦,天哪。你喝醉了吗?我是夏普内尔夫人。你什么时候能清醒过来?”
“我正受您的影响,夏普内尔夫人。”
“你这个坏小子。查尔斯!查尔斯,过来救救福尔迈尔。我快把他毁了。”
“那是R.C.A.维克多的维克多。”她提示道。
“福尔迈尔,是吗?很高兴认识你。你那个随从队伍要花多少钱?”
“告诉他实话。”她提示道。
“四万,维克多。”
“天哪!一周?”
“一天。”
“我的天!你到底想花那么多钱干什么?”
“实话!”她提示道。
“为了出名,维克多。”
“哈!你是认真的吗?”
“我告诉过你他很坏,查尔斯。”
“真他妈提神。克劳斯!过来一下。这个无礼的年轻人一天花四万;就为了出名,如果你信的话。”
“斯科达家的斯科达。”她提示道。
“晚上好,福尔迈尔。我对这个名字的复兴很感兴趣。您或许是谷神星公司最初创始董事会的旁系后裔?”
“给他真相。”她提示道。
“不,斯科达。这是买来的头衔。我买下了公司。我是个暴发户。”
“好。永远大胆!”
“我的天,福尔迈尔!你真坦率。”
“告诉过你他很无礼。非常提神。有不少该死的暴发户,年轻人,但他们不承认。伊丽莎白,来见见谷神星的福尔迈尔。”
“福尔迈尔!我一直渴望见到你。”
“伊丽莎白·雪铁龙夫人。”
“你真的带着一个便携式大学旅行吗?”
“这里要轻松点。”她提示道。
“一个便携式高中,伊丽莎白夫人。”
“但是看在上帝的份上,福尔迈尔,为什么?”
“哦,夫人,现在花钱太难了。我们得找最傻的借口。要是有人能发明一种新的奢侈就好了。”
“你应该带个便携式发明家旅行,福尔迈尔。”
“我有一个。我没有吗,罗宾?但他把时间浪费在永动机上。我需要的是一个常驻挥霍者。你们哪个家族愿意借给我一个次子?”
“欢迎,天哪!而且很多家族都愿意花钱摆脱他们。”
“永动机对你来说还不够挥霍吗,福尔迈尔?”
“不。那是惊人的浪费钱。奢侈的全部意义在于像个傻瓜一样行事,感觉像个傻瓜,但要享受它。永动机有什么乐趣?熵有什么奢侈可言?百万用于胡闹,但一分钱也不给熵。这是我的口号。”
他们笑了,围拢在福尔迈尔周围的人群越来越多。他们既高兴又觉得有趣。他是个新玩意儿。然后午夜到了,随着大钟敲响新年钟声,聚会的人们准备随着午夜环绕世界瞬移。
“跟我们去爪哇吧,福尔迈尔。雷吉斯·谢菲尔德正在举办一场精彩的法律派对。我们要玩‘让法官清醒’。”
“香港,福尔迈尔。”
“东京,福尔迈尔。香港下雨了。来东京吧,带上你的马戏团。”
“谢谢,不了。我去上海。苏维埃大教堂。我承诺,第一个发现我服装骗局的人将获得丰厚的奖励。两小时后见。准备好了吗,罗宾?”
“不要瞬移。没礼貌。走出去。慢慢地。慵懒是时髦。向总督致敬……向专员致敬……向他们的夫人们……好。别忘了给服务员小费。不是他,白痴!那是副总督。好了,你成功了。你被接受了。现在怎么办?”
“现在我们该做来堪培拉要做的事了。”
“我以为我们是来参加舞会的。”
“舞会和一个叫福雷斯特的人。”
“那是谁?”
“本·福雷斯特,沃加号上的太空人。我有三条线索指向那个下令让我等死的人。三个名字。罗马一个叫波吉的厨师;上海一个叫奥雷尔的江湖医生;还有这个人,福雷斯特。这是一次联合行动……社交和搜索。明白吗?”
“我明白。”
“我们有两个小时把福雷斯特撕开。你知道澳洲罐头厂的坐标吗?那个公司镇?”
“我不想参与你的沃加复仇。我在寻找我的家人。”
“这是一次联合行动……各方面都是,”他带着一种超然的野蛮说道,让她畏缩了一下,立刻瞬移走了。当福伊尔到达他在杰维斯海滩的四英里马戏团帐篷时,她已经在换旅行装了。福伊尔看着她。尽管为了安全起见他强迫她住在他帐篷里,但他再也没有碰过她。罗宾注意到他的目光,停止换衣服,等着。
他摇了摇头。“那都结束了。”
“真有趣。你放弃强奸了?”
“穿好衣服,”他说,控制着自己。“告诉他们,他们有两个小时把营地搬到上海。”
当福伊尔和罗宾到达澳洲罐头厂公司镇的前台时,已经是十二点半了。他们申请了身份识别标签,受到了镇长本人的接待。
“新年快乐,”他欢快地说。“快乐!快乐!快乐!来访?很高兴开车带你们转转。请允许我。”
他把他们塞进一架豪华直升机,然后起飞了。“今晚有很多访客。我们镇很友好。世界上最友好的公司镇。”
飞机盘旋在巨大的建筑物上空。“那是我们的冰宫……左边是游泳馆……大圆顶是滑雪跳台。全年有雪……那个玻璃屋顶下是热带花园。棕榈树、鹦鹉、兰花、水果。那是我们的市场……剧院……我们也有自己的广播公司。3D-SS。看看那个足球场。我们有两个小伙子今年入选了全美最佳阵容。特纳在右洛克尼,科瓦尔斯基在左赫菲尔芬格。”
“真的吗,”福伊尔低声说道。
“是的,先生,我们应有尽有。应有尽有。你不必瞬移环游世界寻找乐趣。澳洲罐头厂把世界带给你。我们的小镇是一个小宇宙。世界上最快乐的小宇宙。”
“看来你们有旷工问题。”
镇长拒绝在他的推销辞令中动摇。“看看下面的街道。看到那些自行车了吗?摩托车?汽车?我们人均能负担得起的豪华交通工具比地球上任何其他城镇都多。看看那些住宅。豪宅。我们的人民富有而快乐。我们让他们富有而快乐。”
“但你留得住他们吗?”
“你什么意思?我们当然——”
“你可以告诉我们真相。我们不是求职者。你留得住他们吗?”
“天哪,我们留不住他们超过六个月,”镇长呻吟道。“这真是个头疼的问题,麦克。我们给他们一切,但就是留不住他们。他们产生了流浪癖,然后就琼特走了。旷工使我们的产量下降了百分之十二。我们留不住稳定的劳动力。”
“没人能。”
“应该有法律规定。福雷斯特,你说的?就在这里。”
他把他们降落在一座瑞士木屋前,木屋坐落在一英亩的花园中,然后起飞了,自言自语着。福伊尔和罗宾走到木屋门前,等着监视器捕捉到他们并通报。然而,门闪烁着红色,上面出现了一个白色的骷髅和交叉骨。一个罐装的声音说道:
“警告。此住宅已由瑞典致命防御公司布设人体陷阱。编号:R:77-23。您已被合法通知。”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福伊尔咕哝道。“除夕夜?友好的家伙。我们试试后面。”
他们绕着木屋走着,骷髅和交叉骨间歇性地闪烁着追随着他们,还有那罐装的警告声。在一侧,他们看到一个地下室窗户的顶部明亮地照亮着,并听到里面传来模糊的吟唱声:“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至缺乏……”
“地下室基督徒!”
福伊尔惊呼道。他和罗宾透过窗户窥视。三十名不同信仰的信徒正在庆祝新年,举行着一场联合且高度非法的仪式。二十四世纪尚未废除上帝,但它废除了有组织的宗教。
“难怪这房子布满了人体陷阱,”福伊尔说。“像那样的肮脏行为。看,他们有一个牧师和一个拉比,他们后面那个东西是十字架。”
“你有没有想过咒骂是什么意思?”罗宾平静地问道。“你说‘耶稣’和‘耶稣基督’,你知道那是什么吗?”
“就是骂人,仅此而已。就像‘哎哟’或‘呸’。”
“不,那是宗教。你不知道,但那些词背后有两千年的意义。”
“现在不是说脏话的时候,”福伊尔不耐烦地说。“留着以后再说。来吧。”
木屋的后部是一整面玻璃墙,一间光线昏暗、空无一人的客厅的落地窗。
“趴下,”福伊尔命令道。“我要进去了。”
罗宾俯卧在大理石露台上。福伊尔触发身体,加速成一道闪电般的模糊身影,在玻璃墙上砸出一个洞。在声谱的低端,他听到了沉闷的爆炸声。是枪声。快速的射弹向他袭来。福伊尔扑倒在地板上,调整耳朵,从低音扫到超音速,直到最终捕捉到人体陷阱控制机制的嗡嗡声。他轻轻转动头部,通过双耳测向精确定位,穿过枪林弹雨,摧毁了那个机制。他减速了。
“快进来!”
罗宾颤抖着和他一起进入客厅。地下室基督徒们正从房子某处涌上来,发出殉道者的声音。
“在这儿等着,”福伊尔咕哝道。他加速,模糊地穿过房子,定位了那些摆着僵硬逃跑姿势的地下室基督徒,并对他们进行了分类。他回到罗宾身边并减速。
“他们都不是福雷斯特,”他报告说。“也许他在楼上。趁他们从前面出去,我们走后门。来吧!”
他们飞奔上后楼梯。在楼梯平台上,他们停下来确定方位。
“得快点干活,”福伊尔咕哝道。“枪声和宗教骚乱之间,全世界和他老婆都会瞬移过来问东问西——”他停了下来。楼梯顶端一扇门后传来低沉的喵喵声。福伊尔嗅了嗅。
“类比药!”他惊呼道。“肯定是福雷斯特。怎么样?地下室搞宗教,楼上吸毒。”
“你在说什么?”
“我稍后解释。在这里。我只希望他别发疯。”
福伊尔像一辆柴油拖拉机一样冲过门。他们身处一个宽敞、空荡的房间。天花板上悬挂着一根粗绳。一个赤裸的男人缠绕在半空中的绳子上。他沿着绳子上下扭动,发出喵喵声和一股麝香气味。
“蟒蛇,”福伊尔说。“运气不错。别靠近他。他碰着你就会把你的骨头碾碎。”
楼下传来喊叫声:“福雷斯特!怎么回事,枪声四起?新年快乐,福雷斯特!庆祝活动到底在哪儿?”
“他们来了,”福伊尔咕哝道。“得把他瞬移出去。在海滩见。走。”
他从口袋里掏出一把刀,割断绳子,把那个扭动的男人甩到背上,然后瞬移了。罗宾比他早一刻到达空旷的杰维斯海滩。福伊尔到达时,那个扭动的男人像蟒蛇一样缠绕在他的脖子和肩膀上,用可怕的拥抱挤压着他。血红的烙印突然出现在福伊尔脸上。
“辛巴达,”他用窒息的声音说。“海上的老人。快,姑娘!右边口袋。三个往下。两个往右。毒刺安瓿。随便给他来一——”
他的声音被扼住了。
罗宾打开口袋,找到一包玻璃珠拿了出来。每颗珠子都有一个蜂刺般的末端。她将一根安瓿的刺扎进扭动男人的脖子里。他瘫倒了。
福伊尔把他甩开,从沙滩上站起来。“天哪!”他咕哝着,按摩着喉咙。他深吸一口气。“血和内脏。控制,”他说着,恢复了他那超然冷静的神态。血红色的纹身从他脸上褪去。
“那恐怖的一切是什么?”罗宾问道。
“类比药。给精神病患者用的精神药物。非法的。精神病人总得释放自己;回归原始。他认同某种特定的动物;大猩猩、灰熊、种牛、狼……吃了药就变成他崇拜的动物。福雷斯特看来对蛇情有独钟。”
“你怎么知道这一切?”
“告诉过你我一直在学习……为沃加做准备。这是我学到的东西之一。如果你胆子不小,再给你看看我学到的另一件事。如何让一个精神病人从类比药状态中清醒过来。”
福伊尔打开他战斗连体服的另一个口袋,开始对福雷斯特下手。罗宾看了一会儿,然后发出一声惊恐的哭喊,转身走到水边。她站在那里,盲目地凝视着海浪和星星,直到喵喵声和扭动停止,福伊尔叫她。
“你现在可以回来了。”
罗宾回来时,发现一个破碎的生物正直挺挺地坐在沙滩上,用呆滞、清醒的眼睛凝视着福伊尔。
“你是福雷斯特?”
“你他妈是谁?”
“你是本·福雷斯特,一级太空人。以前在普雷斯蒂安·沃加号上服役。”
福雷斯特惊恐地叫喊起来。
“你在2336年9月16日登上了沃加号。”
那人抽泣着,摇着头。
“九月十六日,你经过一艘残骸。在小行星带附近。诺玛德号的残骸,你的姐妹船。她发出了求救信号。沃加号从她身边经过。任由她漂流等死。沃加号为什么从她身边经过?”
福雷斯特开始歇斯底里地尖叫。
“是谁下令从她身边经过的?”
“耶稣,不!不!不!”
“记录都从博内斯和尤伊格的文件里消失了。有人在我之前拿到了它们。那是谁?沃加号上有谁?谁和你一起出海的?我要军官和船员。谁是船长?”
“不,”福雷斯特尖叫道。“不!”
福伊尔在那歇斯底里的男人面前举着一沓钞票。“我会为信息付钱。五万。够你余生吸类比药了。是谁下令让我等死的,福雷斯特?谁?”
那人猛地打掉福伊尔手中的钞票,跳起来沿着海滩跑去。福伊尔在浪边将他扑倒。福雷斯特一头栽倒,脸埋在水里。福伊尔把他按在那里。
“谁指挥的沃加号,福雷斯特?谁下的命令?”
“你快淹死他了!”罗宾喊道。
“让他受点苦。水比真空容易多了。我受了六个月的苦。谁下的命令,福雷斯特?”
那人咕噜着,呛着水。福伊尔把他的头抬出水面。“你是什么人?忠诚?疯了?害怕?你这种人五千块就能出卖一切。我出五万。五万换信息,你这个狗娘养的,不然你就慢慢痛苦地死去。”
纹身出现在福伊尔脸上。他把福雷斯特的头按回水里,按住那个挣扎的男人。罗宾试图把他拉开。
“你是在谋杀他!”
福伊尔把可怕的脸转向罗宾。“把你的手拿开,婊子!谁和你一起上船的,福雷斯特?谁下的命令?为什么?”
福雷斯特扭过头,挣脱出水面。“沃加号上有十二个人,”他尖叫道。“基督救我!有我和肯普——”他痉挛地抽搐了一下,然后瘫软下去。福伊尔把他的尸体从浪里拖出来。“继续说。你和谁?肯普?还有谁?说。”
没有回应。福伊尔检查了尸体。“死了,”他低吼道。
“哦,我的天!我的天!”
“一条线索完蛋了。就在他要开口的时候。真他妈倒霉。”
他深吸一口气,像披上铁斗篷一样恢复了冷静。纹身从他脸上消失了。他调整手表,设定为东经120度。
“上海快午夜了。走吧。也许我们在上海药剂师助手谢尔盖·奥雷尔那里运气会好些。别那么害怕。只是谋杀。走吧,姑娘。琼特!”
罗宾喘着气。他看到她正难以置信地盯着他肩膀后面。福伊尔转过身:一个燃烧的身影出现在海滩上,一个穿着燃烧衣服、脸上纹着可怕图案的巨人。那是他自己。
“天哪!”福伊尔惊呼道。他向自己燃烧的影像迈出一步,突然间它消失了。
他转向罗宾,脸色苍白,浑身颤抖。“你看到了吗?”
“是的。”
“那是什么?”
“你。”
“看在上帝的份上!我?怎么可能?怎么——”
“是你。”
“但是——”他结结巴巴地说,力量和狂怒的占有欲都从他身上消失了。“那是幻觉吗?幻觉?”
“我不知道。我也看到了。”
“全能的基督!看到你自己……面对面……衣服着火了。你看到了吗?看在上帝的份上那是什么?”
“是格利弗·福伊尔,”罗宾说,“在地狱里燃烧。”
“好吧,”福伊尔愤怒地脱口而出。“是我在地狱里,但我还是要坚持下去。如果我在地狱里燃烧,沃加也会和我一起燃烧。”
他拍打着手掌,激励自己恢复力量和决心。
“我还是要坚持下去,天哪!下一站上海。琼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