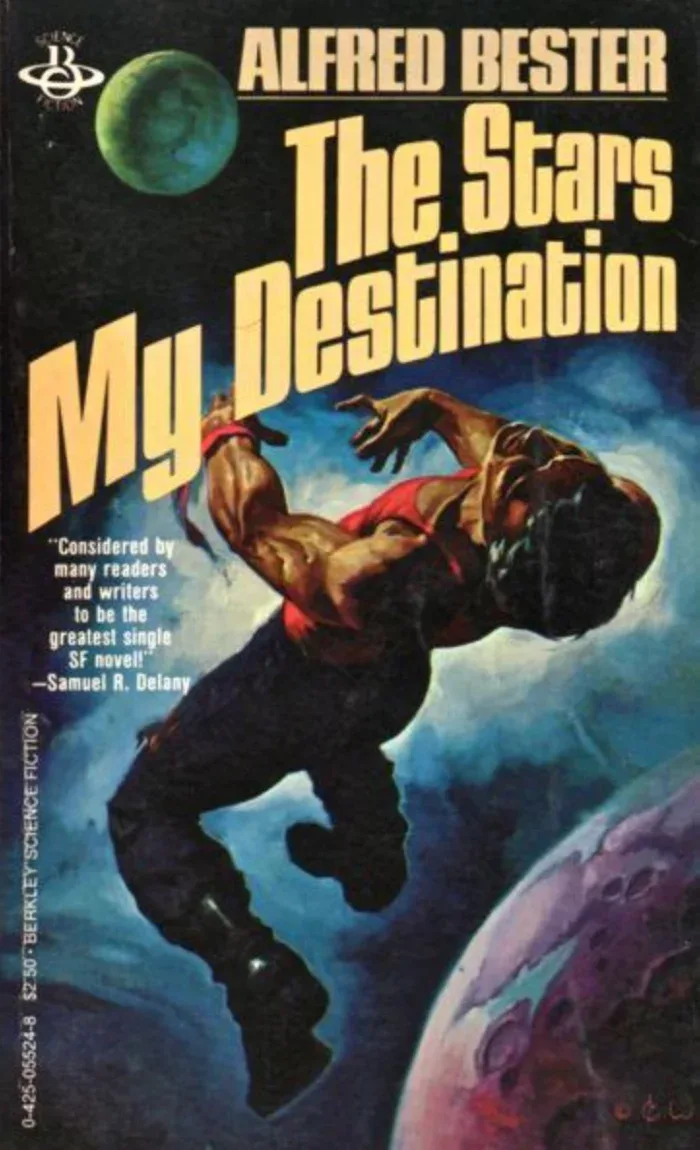第二部
怀着一颗狂怒幻想的心
我是它的主宰,
驾驭燃烧的长矛和空气的骏马,
我向荒野漫游。
与鬼魂和阴影的骑士
我被召唤去比武,
在广阔世界尽头的十里格之外
我想那并非旅程。
——汤姆疯子
第八章
旧岁在瘟疫毒害行星之际变得酸楚。战争势头增强,从遥远的太空浪漫突袭和小规模冲突演变成一场酝酿中的大灾难。显而易见,最后的世界大战已经结束,第一次太阳系战争已经开始。
交战双方缓慢地集结人员和物资,准备进行大破坏。外围卫星实行了普遍征兵制,内行星被迫效仿。工业、贸易、科学、技能和专业都被征召;随之而来的是规章制度和压迫。陆军和海军进行征用和指挥。
商业界服从了,因为这场战争(像所有战争一样)是一场商业斗争的武装阶段。但民众反抗了,逃避征兵的琼特和逃避劳役的琼特成了严重问题。间谍恐慌和入侵恐慌蔓延开来。歇斯底里的人变成了告密者和私刑者。一种不祥的预感瘫痪了从巴芬岛到福克兰群岛的每一个家庭。垂死的这一年,唯一的生气来自四英里马戏团的到来。
这是谷神星的杰弗里·福尔迈尔那怪诞随从队伍的流行绰号,他是一位来自最大小行星的富有年轻丑角。谷神星的福尔迈尔极其富有;他也极其有趣。他是典型的资产阶级绅士,是所有时代中那个暴发户。他的随从队伍介于乡村马戏团和保加利亚小国王的滑稽宫廷之间,正如这次在威斯康星州格林贝的典型到场所示。
清晨,一位戴着法律家族高筒礼帽的律师出现了,手里拿着一张营地名单,口袋里揣着一小笔财富。他在密歇根湖畔选定了一片四英亩的草地,并以高昂的费用租了下来。紧随其后的是一群来自梅森和迪克森家族的测量员。二十分钟内,测量员们就规划好了营地,四英里马戏团即将到来的消息也传开了。来自威斯康星、密歇根州和明尼苏达州的当地人前来观看热闹。
二十名粗工瞬移进来,每人背上都背着一个帐篷包。传来一阵巨大的命令声、喊叫声、咒骂声和压缩空气的痛苦尖叫声。二十顶巨大的帐篷向上膨胀,它们涂着漆和乳胶的表面在冬日阳光下干燥时闪闪发光。观众们欢呼起来。
一架六引擎直升机缓缓降下,悬停在一个巨大的蹦床上空。它的腹部打开,一连串家具倾泻而下。仆人、贴身男仆、厨师和服务员瞬移进来。他们布置和装饰了帐篷。厨房开始冒烟,煎、烤、烘焙的气味弥漫在营地。福尔迈尔的私人警察已经上岗,巡逻着四英亩的场地,将庞大的人群挡在后面。
然后,乘飞机、乘汽车、乘公共汽车、乘卡车、骑自行车和通过琼特,福尔迈尔的随从们来了。图书管理员和书籍,科学家和实验室,哲学家、诗人、运动员。剑和马刀的架子竖起来了,还有柔道垫和一个拳击台。一个五十英尺的游泳池被挖入地下,并用泵从湖里抽水填满。两个壮实的运动员就游泳池是应该加热游泳还是冷冻滑冰发生了有趣的争执。
音乐家、演员、杂耍演员和杂技演员抵达了。喧嚣声震耳欲聋。一群机械师融化了一个检修坑,开始发动福尔迈尔收藏的老式柴油收割机。最后来的是营地的追随者:妻子、女儿、情妇、妓女、乞丐、骗子和敲诈者。到了上午时分,马戏团的喧嚣声在四英里外都能听到,因此得名。
中午时分,福尔迈尔·刻瑞斯以一种极其奢华、足以让七年忧郁症患者捧腹大笑的炫耀性交通方式抵达。一架巨大的水陆两用飞机从南方轰鸣而来,降落在湖面上。一艘登陆艇驳船从飞机中驶出,嗡嗡地穿过水面到达岸边。它的前壁砰地一声放下,变成一座吊桥,一辆二十世纪的参谋车驶了出来。观众们惊奇连连,因为那辆参谋车只行驶了二十码就停在了营地中央。
“接下来会是什么?自行车?”
“不,旱冰鞋。”
“他会骑弹簧单高跷出来。”
福尔迈尔超出了他们最疯狂的猜测。一门马戏团大炮的炮口从参谋车里伸出来。一声黑火药爆炸的巨响,谷神星的福尔迈尔以优美的弧线从炮口射出,正好落到他帐篷门口,被四个贴身男仆用网接住。迎接他的掌声在六英里外都能听到。福尔迈尔爬上他贴身男仆的肩膀,示意安静。
“哦,天哪!它要发表演讲了。”
“它?你是说‘他’,对吧?”
“不;是它。它不可能是人。”
“朋友们,罗马人,同胞们,”福尔迈尔认真地开始说。“请听我说。莎士比亚。1564-1616。该死!”
四只白鸽从福尔迈尔的袖子里抖落出来,扑腾着飞走了。他惊讶地看着它们,然后继续说道,“朋友们,问候,致敬,你好,时髦,美食家,旅途愉快,好——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福尔迈尔的口袋着火了,喷射出罗马焰火。他试图扑灭自己。彩带和五彩纸屑从他身上迸发出来。“朋友们……闭嘴!我会把这篇演讲弄清楚。安静!朋友们——!”
福尔迈尔沮丧地低头看着自己。他的衣服正在融化,露出鲜红色的内衣。“克莱因曼!”他愤怒地咆哮道。“克莱因曼!你那该死的催眠训练怎么了?”
一个毛茸茸的脑袋从帐篷里探出来。“你昨晚为这篇演讲学习了吗,福尔迈尔?”
“该死,当然。学了两个小时。我的脑袋一直没离开过催眠炉,克莱因曼的戏法。”
“不,不,不!”那个毛茸茸的男人吼道。“我要告诉你多少次?戏法不是演讲。是魔术。笨蛋!!你接受了错误的催眠!”
鲜红的内衣开始融化。福尔迈尔从他颤抖的仆人肩膀上摔下来,消失在他的帐篷里。传来一阵哄堂大笑和欢呼声,四英里马戏团进入高速运转状态。厨房里滋滋作响,烟雾弥漫。吃喝永无止境。歌舞杂耍永不停止。
在他的帐篷里,福尔迈尔换了衣服,改变了主意,又换了一次,又脱光了衣服,踢了他的仆人,然后用一种混杂着法语、梅费尔口音和做作腔调的语言叫来了他的裁缝。刚穿上一半新西装,他想起自己忘了洗澡。他打了裁缝一巴掌,命令将十加仑香水倒入游泳池,然后诗兴大发。他召来了他的常驻诗人。
“记下来,”福尔迈尔命令道。“国王死了,那些——等等。什么词和‘月亮’押韵?”
“六月,”他的诗人建议道。“低吟,很快,沙丘,潜鸟,中午,符文,曲调,恩惠……”
“我忘了我的实验!”福尔迈尔惊呼道。“博恩博士!博恩博士!”
他半裸着身子,慌乱地冲进实验室,把自己和他的常驻化学家博恩博士炸飞了半个帐篷。当化学家试图从地板上爬起来时,他发现自己被一个极其痛苦和尴尬的锁喉动作扼住了。
“野口!”福尔迈尔喊道。“嗨!野口!我刚发明了一种新的柔道锁技。”
福尔迈尔站起来,举起那个窒息的化学家,瞬移到柔道垫上,那个小个子日本人检查了一下锁技,摇了摇头。
“不,请。”他礼貌地嘶嘶说道。“嗯嗯嗯嗯。气管受压并非永远致命。这里我给你演示一下,请。”
他抓住那个晕头转向的化学家,旋转他,把他放在垫子上,摆出一个永久性自我窒息的姿势。“请您观察,福尔迈尔?”
但福尔迈尔正在图书馆里用布洛赫的《性生活》(八磅九盎司重)猛击他的图书管理员,因为那个不幸的人无法拿出关于制造永动机的文本。他冲到他的物理实验室,毁坏了一个昂贵的计时器来试验齿轮,瞬移到乐队指挥台,抓住指挥棒把管弦乐队带入混乱,穿上溜冰鞋掉进了充满香气的游泳池,被拖了出来,对着缺乏冰块大声咒骂,并被听到表示渴望独处。
“我想和自己交流一下,”福尔迈尔说着,朝四面八方踢他的仆人。在最后一个仆人跛着脚走到门口并关上门之前,他已经打起了鼾。
鼾声停止了,福伊尔站起身。“今天就这样吧,”他咕哝道,然后走进他的更衣室。他站在镜子前,深吸一口气屏住,同时观察着自己的脸。一分钟后,脸上仍然没有瑕疵。他继续屏住呼吸,保持着对脉搏和肌肉的严格控制,以钢铁般的冷静克服着压力。两分二十秒时,烙印出现了,血红色。福伊尔呼出气。老虎面具褪去了。
“好多了,”他低声说道。“好多了。那个老苦行僧说得对,瑜伽就是答案。控制。脉搏、呼吸、肠道、大脑。”
他脱光衣服,检查自己的身体。他身体状况极佳,但皮肤上仍然从脖子到脚踝布满了精致的银色接缝网络。它们看起来像是有人把神经系统的轮廓刻进了福伊尔的肉体。那是一次手术的疤痕,尚未褪去。
这次手术花了福伊尔二十万信用点贿赂火星突击队的外科主任,将他变成了一台非凡的战斗机器。每一个神经丛都被重新布线,微型晶体管和变压器被埋入肌肉和骨骼中,一个微小的白金插座显露在他脊柱的底部。福伊尔将一个豌豆大小的电源包固定在这个插座上并打开开关。他的身体开始产生一种几乎是机械的内部电子振动。
“与其说是人,不如说是机器,”他想。他穿好衣服,拒绝了谷神星福尔迈尔的奢华服饰,换上了匿名的黑色行动连体服。
他瞬移到罗宾·韦恩斯伯里在威斯康星松林中那栋孤零零建筑里的公寓。这是四英里马戏团出现在格林贝的真正原因。他瞬移着,到达时一片漆黑,空无一物,立刻向下坠落。
“天哪!”他想。“瞬移错了?”
一根断裂椽子的末端狠狠地撞了他一下,他重重地摔在一片破碎的地板上,落在一具正在腐烂的尸体上。
福伊尔带着冷静的厌恶跳了起来。他用舌头使劲顶住右上第一颗臼齿。那次将他半个身体变成电子机器的手术,把控制开关板设在了他的牙齿里。福伊尔用舌头顶了一下牙齿,他视网膜的边缘细胞被激发,发出柔和的光芒。他顺着两道苍白的光束向下看去,看到一具男人的尸体。
尸体躺在罗宾·韦恩斯伯里公寓下面的单元里。它被掏空了内脏。福伊尔抬起头。他上方是一个十英尺的洞,那里曾是罗宾客厅的地板。整栋楼弥漫着火灾、烟雾和腐烂的气味。
“被洗劫了,”福伊尔轻声说。“这地方被洗劫了。发生了什么事?”
琼特时代将世界上的流浪汉、浪子和游民凝聚成一个新的阶层。它追随着黑夜从东到西,总是在黑暗中,总是在寻找战利品、灾难的遗留物、腐肉。如果地震震毁了一个仓库,他们第二天晚上就会去洗劫。如果火灾烧开了一座房子或爆炸摧毁了一家商店的防御,他们就会琼特进去搜刮。他们自称为“劫掠琼特者”。他们是豺狼。
福伊尔爬上废墟,来到楼上的走廊。劫掠琼特者在那里扎营。一头整只小牛在火堆前烤着,火星通过屋顶的裂缝向上飞溅。火堆周围有十几个男人和三个女人,粗野、危险,用伦敦东区押韵俚语喋喋不休。他们穿着不配套的衣服,用香槟杯喝着土豆啤酒。
当那个穿着黑色衣服、目光专注、眼中射出苍白光束的高大男人从废墟中走上来时,福伊尔的出现引起了一阵不祥的愤怒和恐惧的低吼。他平静地穿过骚动的人群,来到罗宾·韦恩斯伯里公寓的入口处。他养成的铁一般的控制力给了他一种超然的气质。
“如果她死了,”他想,“我就完了。我必须利用她。但如果她死了……”
罗宾的公寓像楼里其他地方一样被洗劫一空。客厅是一个椭圆形的地板,围绕着中央锯齿状的洞。福伊尔寻找着尸体。卧室的床上躺着两个男人和一个女人。男人们咒骂着。女人对着这个幽灵尖叫。男人们向福伊尔扑来。他后退一步,用舌头顶住上门牙。神经回路嗡嗡作响,他身体的每一个感官和反应都加速了五倍。
效果是瞬间将外部世界降低到极度缓慢的动作。声音变成了深沉的含混不清,颜色向下移动到光谱的红色端。两个袭击者似乎带着梦幻般的慵懒向他飘来。对世界其他地方来说,福伊尔变成了一团模糊的动作。他侧身躲过向他缓慢袭来的拳头,绕到那人身后,举起他,把他扔向客厅的坑洞。他扔了第二个男人。在福伊尔加速的感官中,他们的身体似乎缓慢地漂浮着,仍然保持着跨步的姿势,拳头缓慢向前,张开的嘴巴发出沉重凝滞的声音。
福伊尔猛地转向床上畏缩的女人。
“尸体在哪?”模糊的身影问道。
女人尖叫起来。
福伊尔再次按下上门牙,切断了加速。外部世界从慢动作中挣脱出来,恢复正常。声音和颜色跃上光谱,两个豺狼消失在坑洞中,坠入下面的公寓。
“有尸体吗?”福伊尔轻柔地重复道。“一个黑人女孩?”
女人语无伦次。他抓住她的头发摇晃着,然后把她扔进了客厅地板上的坑洞。
他寻找罗宾命运线索的行动被大厅里涌来的人群打断了。他们手持火把和临时制作的武器。劫掠琼特者并非职业杀手。他们只会折磨毫无防备的猎物致死。“别烦我,”福伊尔平静地警告道,专心地在壁橱和翻倒的家具下搜寻着。
他们被一个穿着貂皮套装、戴着三角帽的流氓煽动着,又被楼下传来的咒骂声鼓舞着,慢慢靠近。戴三角帽的男人向福伊尔扔了一个火把。火把烧到了他。福伊尔再次加速,劫掠琼特者们变成了活生生的雕像。福伊尔捡起半把椅子,平静地用它敲打着那些慢动作的人影。他们仍然站立着。他把戴三角帽的男人按倒在地,跪在他身上。然后他减速了。
外部世界再次恢复生机。豺狼们当场倒下,被击晕了。戴着三角帽、穿着貂皮套装的男人咆哮着。
“这里有尸体吗?”福伊尔问道。“黑人女孩。非常高。非常漂亮。”
那人扭动着身体,试图抠福伊尔的眼睛。
“你留意尸体,”福伊尔温柔地说。“你们有些豺狼喜欢死女孩胜过活女孩。你在这里找到她的尸体了吗?”
没有得到满意的答复,他拿起一个火把点燃了貂皮套装。他跟着那个劫掠琼特者进入客厅,带着超然的兴趣注视着他。那人嚎叫着,翻过坑洞边缘,燃烧着坠入下面的黑暗中。
“有尸体吗?”
福伊尔平静地向下喊道。他对答案摇了摇头。“不太灵巧,”他低声说道。“我得学会如何套取信息。达格纳姆可以教我一两招。”
他关掉了电子系统,然后瞬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