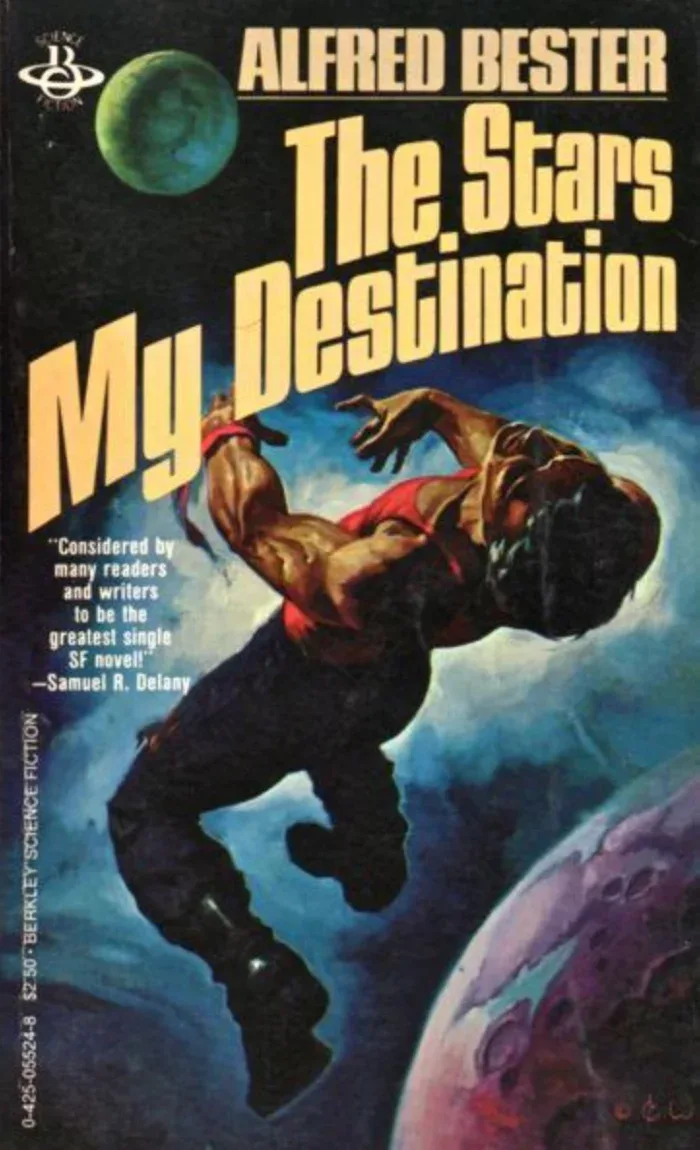“所以我没杀了他们,”福伊伊尔咕哝道。“他们已经退回小行星内部……可能在深处生活,同时修复其余部分。”
“你会帮他们吗,格利?”
“为什么?”
“是你造成的破坏。”
“管他们去死。我有我自己的问题。不过这倒是个安慰。他们不会来烦我们了。”
他再次绕小行星飞行一圈,将“周末客”号降落在新坑洞的入口处。
“我们就从这里开始工作,”他说。“穿上宇航服,吉兹。走吧!走吧!”
他驱赶着她,急不可耐;他也驱赶着自己。他们穿好宇航服,离开“周末客”号,在坑洞的碎片中跌跌撞撞地进入小行星荒凉的内部。这就像在巨大蠕虫洞穴的爬行隧道中蠕动。福伊尔打开他的微波宇航服通讯器,对吉兹说。
“在这里很容易迷路。跟着我。靠近点。”
“我们去哪里,格利?”
“追诺玛德号。我记得我离开时他们正把它用水泥固定在小行星里。不记得在哪里了。得找到她。”
通道没有空气,他们的前进悄无声息,但震动通过金属和岩石传递。他们在一个古老战舰布满坑洞的船体旁停下喘了口气。当他们靠在上面时,感觉到了来自内部的信号震动;有节奏的敲击声。
福伊尔冷酷地笑了笑。“那是里面的约瑟夫和科学族,”他说。“请求说几句话。我会给他们一个含糊的回答。”
他敲了两下船体。“现在给我的妻子捎个私人信息。”
他脸色一沉。他愤怒地猛击船体,然后转身离开。“来吧。走吧。”
但当他们继续搜索时,信号一直跟着他们。很明显,小行星的外围已被遗弃;部落已经撤退到中心。然后,在一条由敲打过的铝制成的深井下方,一个舱口打开了,光芒四射,约瑟夫穿着一件由玻璃纤维布制成的古老宇航服出现了。他站在那个笨重的袋子里,魔鬼般的脸凝视着,双手紧握着恳求,魔鬼般的嘴巴做着动作。
福伊尔凝视着那个老人,向他迈出一步,然后停了下来,拳头紧握,喉咙因愤怒而抽动。而吉斯贝拉看着福伊尔,惊恐地叫喊起来,因为他脸上旧的纹身又出现了,血红色映衬着苍白的皮肤,猩红色代替了黑色,无论是颜色还是图案,都真正像一张老虎面具。
“格利!”她喊道。“我的天!你的脸!”
福伊尔没理她,只是瞪着约瑟夫,而那个老人则做着恳求的手势,示意他们进入小行星内部,然后消失了。直到那时,福伊尔才转向吉斯贝拉问道:“什么?你刚才说什么?”
透过头盔清晰的球罩,她能清楚地看到他的脸。随着福伊尔内心的愤怒消退,吉斯贝拉看到那血红色的纹身逐渐褪去并消失了。
“你看到那个小丑了吗?”福伊尔质问道。“那是约瑟夫。你看到他在对我做了那些事之后还在乞求和恳求吗……?你刚才说什么?”
“你的脸,格利。我知道你的脸发生了什么事。”
“你在说什么?”
“你想要点什么能控制你,格利。你得到了。你的脸。它——”
吉斯贝拉歇斯底里地笑了起来。“你现在必须学会控制了,格利。你再也不能屈服于任何情感……任何情感……因为——”但他正凝视着她身后,突然他大叫一声冲上铝制竖井。他在一扇敞开的门前猛地停下,开始得意地欢呼。门通向一个工具柜,四英尺乘四英尺乘九英尺。柜子里有架子,还有一堆旧食品和废弃容器。那是福伊尔在“诺玛德”号上的棺材。
约瑟夫和他的弟兄们在福伊尔逃脱的大灾难使进一步工作变得不可能之前,成功地将残骸封入了他们的小行星。飞船内部几乎未受触动。福伊尔拉着吉斯贝拉的手臂,带她快速参观了飞船,最后来到事务长储物柜,福伊尔在那里撕扯着残骸和碎片的窗户,直到露出了一个巨大、空白、无法穿透的钢制保险箱。
“我们有两个选择,”他喘着气说。“要么我们把保险箱从船体里拆出来,运回地球,在那里处理它,要么我们就在这里打开它。我投票选在这里。也许达格纳姆在撒谎。一切都取决于萨姆在‘周末客’号上有什么工具。回船上去,吉兹。”
他从未注意到她的沉默和心事重重,直到他们回到“周末客”号上,他完成了紧急寻找工具的任务。
“什么都没有!”他不耐烦地惊呼道。“船上连把锤子或钻头都没有。只有开瓶子和口粮的玩意儿。”
吉斯贝拉没有回答。她一直盯着他的脸。
“你为什么那样盯着我?”福伊尔质问道。
“我被迷住了,”吉斯贝拉慢慢地回答。
“被什么?”
“我要给你看点东西,格利。”
“什么?”
“我有多么鄙视你。”
吉斯贝拉抽了他三个耳光。被击打刺痛,福伊尔猛地愤怒地站起来。吉斯贝拉拿起一面手镜,举到他面前。
“看看你自己,格利,”她平静地说。“看看你的脸。”
他看了看。他看到旧的纹身印记在皮肤下燃烧着血红色,把他的脸变成了一张猩红和白色的老虎面具。他被这骇人的景象吓得浑身发冷,怒气顿消,同时面具也消失了。
“我的天……”他低语道。“哦,我的天……”
“我得让你发脾气才能给你看。”吉斯贝拉说。
“这是什么意思,吉兹?贝克搞砸了吗?”
“我不这么认为。我想你皮肤下有疤痕,格利……来自最初的纹身,然后又来自漂白。针疤。通常情况下它们不显现,但当你的情绪激动、心脏开始泵血时……当你愤怒、害怕、热情或被附身时……它们就会显现出来,血红色。你明白吗?”
他摇摇头,仍然凝视着自己的脸,困惑地触摸着它。
“你说过你希望把我装在口袋里,在你失控时扎你。你得到了比那更好的东西,格利,或者更糟,可怜的宝贝。你得到了你的脸。”
“不!”他说。“不!”
“你永远不能失控,格利。你永远不能喝太多酒,吃太多,爱太多,恨太多……你必须用铁腕控制自己。”
“不!”他绝望地坚持道。“可以修复的。贝克可以做到,或者别人。我不能害怕感受任何东西,因为那会把我变成一个怪物!”
“我不认为这能修复,格利。”
“植皮……”
“不行。疤痕太深,无法植皮。你永远摆脱不了这个烙印,格利。你必须学会与它共存。”
福伊尔猛地扔掉镜子,勃然大怒,血红色的面具再次在他皮下燃起。他冲出主舱,来到主舱口,拉下备用宇航服,开始往里钻。
“格利!你去哪儿?你要干什么?”
“拿工具,”他喊道。“给那该死的保险箱拿工具。”
“哪里?”
“在小行星里。他们有几十个仓库,塞满了失事飞船上的工具。那里肯定有钻头;我需要的一切。别跟我来。可能会有麻烦。我现在该死的脸怎么样了?显出来了吗?天哪,我希望有麻烦!”
他封好宇航服,进入小行星。他找到一个隔开有人居住核心区和外部虚空的舱口。他砰砰地敲着门。他等着,又敲了一次,持续着这专横的召唤,直到舱口最终被打开。手臂伸出来把他拽了进去,舱口在他身后关上了。它没有气闸。
他在光线下眨了眨眼,对着聚集在他面前的约瑟夫和他那些无辜的、脸上纹着可怕图案的弟兄们皱起了眉头。他知道自己的脸一定燃烧着红白相间的颜色,因为他看到约瑟夫吃了一惊,看到那魔鬼般的嘴巴念出了“诺玛德”的音节。
福伊尔大步穿过人群,粗暴地驱散他们。他用戴着铁甲的拳头反手给了约瑟夫一击。他搜寻着有人居住的走廊,模糊地认出它们,最后来到那个半是天然洞穴、半是古董大厅的房间,那里存放着工具。
他翻箱倒柜,搜集着钻头、金刚石钻头、酸液、铝热剂、结晶剂、炸药胶、引信。在轻微旋转的小行星上,这些设备的总重量减少到不足一百磅。他把它们堆成一团,用缆绳粗略地捆在一起,然后开始走出储藏洞穴。
约瑟夫和他的弟兄们正等着他,像跳蚤等着狼一样。他们向他扑来,他猛冲过去,被围攻着,欣喜着,野蛮着。宇航服的盔甲保护他免受他们的攻击,他沿着通道走下去,寻找一个通往虚空的舱口。
吉斯贝拉的声音传来,耳机里声音细小而激动:“格利,你能听到我吗?我是吉兹。格利,听我说。”
“说吧。”
“两分钟前又来了一艘船。它正漂浮在小行星的另一边。”
“什么!”
“上面标着黄黑相间的颜色,像只大黄蜂。”
“达格纳姆的颜色!”
“那我们被跟踪了。”
“还能是什么?达格纳姆可能从我们逃出古夫尔·马特尔起就一直跟着我。我真是个傻瓜,没想到这一点。他是怎么跟踪我的,吉兹?通过你?”
“格利!”
“算了。只是开个玩笑。”
他毫无笑意地笑了笑。“我们得快点干活,吉兹。穿上宇航服,到诺玛德号上见我。事务长室。走,姑娘。”
“但是,格利……”
“结束通话。他们可能在监听我们的波段。走!”
他冲进小行星,到达一个闩着的舱口,冲破守卫,砸开舱门,进入外部通道的虚空。科学族急于关上舱门,无暇阻止他。但他知道他们会跟着他;他们正怒火中烧。
他拖着沉重的设备,七拐八弯地来到“诺玛德”号的残骸处。吉斯贝拉正在事务长室等他。她准备打开微波通讯设备,福伊尔阻止了她。他把自己的头盔紧贴着她的头盔喊道:“不用短波。他们会监听,会用测向仪定位我们。这样你能听到我,对吧?”
她点点头。
“好的。我们大概只有一个小时的时间,达格纳姆就会找到我们。我们大概只有一个小时的时间,约瑟夫和他那帮人就会来找我们。我们处境非常糟糕。我们必须快点。”
她又点点头。
“没时间打开保险箱运走金条了。”
“如果它在那里的话。”
“达格纳姆不是来了吗?这就是证据。我们得把整个保险箱从诺玛德号上切割下来,弄进周末客号。然后我们引爆。”
“但是——”
“听我说,照我说的做。回周末客号去。把里面清空。扔掉所有我们不需要的东西……除了应急口粮以外的所有补给。”
“为什么?”
“因为我不知道这个保险箱有多重,回到重力环境下船可能承受不了。我们得提前留出余量。这意味着回程会很艰难,但值得。把船清空。快!走,姑娘。走!”
他推开她,看也不看她一眼,开始攻击保险箱。它被嵌入船体的结构钢中,是一个直径约四英尺的巨大钢球。它在十二个不同的点被焊接在“诺玛德”号的纵梁和肋骨上。福伊尔依次用酸液、钻头、铝热剂和制冷剂攻击每一个焊点。他运用的是结构应变理论……加热、冷冻和蚀刻钢材,直到其晶体结构扭曲,物理强度被破坏。他在使金属疲劳。
吉斯贝拉回来了,他意识到已经过去了四十五分钟。他浑身湿透,颤抖着,但保险箱的球体已经脱离船体自由悬挂,表面有十几个粗糙的突起。福伊尔急切地向吉斯贝拉示意,她和他一起用力推着保险箱。他们俩合力也无法移动它的质量。就在他们精疲力竭、绝望地退后时,一道快速的阴影遮蔽了透过“诺玛德”号船体裂缝倾泻而入的阳光。他们抬头望去。一艘宇宙飞船正在距离不到四分之一英里的小行星周围盘旋。
福伊尔把头盔紧贴着吉斯贝拉的头盔。“达格纳姆,”他喘着气说。“在找我们。可能派了一队人下来找我们了。他们一跟约瑟夫联系上就会来。”
“哦,格利……”
“我们还有机会。也许他们转几圈之前发现不了萨姆的‘周末客’号。它藏在那个坑里。也许我们能在此期间把保险箱弄上船。”
“怎么弄,格利?”
“我不知道,该死的!我不知道。”
他沮丧地捶打着拳头。“我完了。”
“我们不能把它炸出去吗?”
“炸……?什么;用炸弹代替脑子?这是心理学家麦昆在说话吗?”
“听着。用爆炸物炸它。那就像火箭喷射一样……给它一个推力。”
“是的,我明白了。但然后呢?我们怎么把它弄进船里,姑娘?不能一直炸。没时间了。”
“不,我们把船开到保险箱那里。”
“什么?”
“把保险箱直接炸进太空。然后把船开过来,让保险箱直接飞进主舱口。就像用帽子接球一样。明白吗?”
他明白了。“天哪,吉兹,我们能做到。”
福伊尔跳到那堆设备前,开始分拣炸药棒、胶状炸药、引信和雷管。
“我们得用短波。一个人留在保险箱旁;一个人驾驶飞船。留在保险箱旁的人引导驾驶飞船的人就位。对吧?”
“对。你最好驾驶,格利。我来引导。”
他点点头,把炸药固定在保险箱表面,装上雷管和引信。然后他把头盔紧贴着她的。“真空引信,吉兹。定时两分钟。我通过短波下令后,你只要拔掉引信头,然后赶紧躲开。明白吗?”
“明白。”
“守着保险箱。一旦你把它引导进船里,立刻跟上来。别等任何事。时间会很紧。”
他拍了拍她的肩膀,回到了“周末客”号。他让外舱门开着,气闸的内门也开着。飞船里的空气立刻排空了。被吉斯贝拉清空后,它看起来凄凉而孤寂。
福伊尔直接走向控制台,坐下,打开了他的微波通讯设备。“准备好,”他咕哝道。“我现在就出来。”
他点燃了喷气发动机,侧向喷气口喷射了三秒钟,然后是前向喷气口。“周末客”号轻松升起,像鲸鱼浮出水面一样抖落背上和两侧的碎片。当它向上滑行并后退时,福伊尔喊道:“炸药,吉兹!现在!!”
没有爆炸;没有闪光。他下方的小行星上出现了一个新坑洞,一朵碎石花向上绽放,迅速超过了一个悠闲地跟在后面、疲惫旋转着的暗淡钢球。
“慢点,”吉斯贝拉的声音透过耳机传来,冰冷而干练。“你后退得太快了。顺便说一句,麻烦来了。”
他用尾部喷气口刹车,惊恐地向下看去。小行星表面覆盖着一群大黄蜂。那是达格纳姆的手下,穿着黄黑相间的宇航服。他们正嗡嗡地围着一个穿着白色宇航服的身影,那身影躲闪旋转,避开了他们。那是吉斯贝拉。
“保持稳定,”吉兹平静地说,尽管他能听到她呼吸急促。“再放松一点……转四分之一圈。”
他几乎是下意识地服从了她,仍然注视着下面的搏斗。周末客号的侧翼挡住了保险箱接近他时轨迹的视线,但他仍然能看到吉斯贝拉和达格纳姆的人。她点燃了她的宇航服火箭……他能看到她背部喷出的小火焰……然后她从小行星表面飞了上来。达格纳姆的手下背部也喷出二十几道火焰,紧随其后。六七个人放弃了追逐吉斯贝拉,转而追向周末客号。
“会很接近的,格利,”吉斯贝拉现在喘着粗气,但她的声音仍然稳定。“达格纳姆的船在另一边降落了,但他们现在可能已经通知他了,他很快就会过来。保持你的位置,格利。大约还有十秒钟……”
大黄蜂们逼近,吞没了那套小小的白色宇航服。
“福伊尔!你能听到我吗?福伊尔!”
达格纳姆的声音模糊地传来,最后清晰了。“我是达格纳姆,正在你的频段呼叫。请回答,福伊尔!”
“吉兹!吉兹!你能摆脱他们吗?”
“保持你的位置,格利……她来了!一杆进洞,孩子!”
当保险箱缓慢而沉重地撞入主舱口时,一股毁灭性的冲击震动了“周末客”号。与此同时,那个穿着白色宇航服的身影冲出了那群黄色黄蜂的包围。它像火箭一样冲向“周末客”号,后面紧追不舍。
“来吧,吉兹!来吧!”
福伊尔嚎叫着。“来吧,姑娘!来吧!”
当吉斯贝拉消失在“周末客”号侧翼后面时,福伊尔设定好控制器,准备进行最大加速度。
“福伊尔!你回答我好吗?我是达格纳姆。”
“去你的,达格纳姆,”福伊尔喊道。“你一上船就告诉我一声,吉兹,抓紧了。”
“我上不去了,格利。”
“来吧,姑娘!”
“我上不了船。保险箱挡住了舱口。它卡在半路了……”
“吉兹!”
“我告诉你没路进去了,”她绝望地喊道。“我被挡在外面了。”
他疯狂地环顾四周。达格纳姆的人正带着专业袭击者的威胁性意图登上“周末客”号的船体。达格纳姆的飞船正越过小行星短暂的地平线,直冲着他而来。他开始头晕目眩。
“福伊尔,你完了。你和那个女孩。但我愿意提出一个交易……”
“格利,帮帮我。做点什么,格利。我迷路了!”
“沃加,”他用窒息的声音说道。他闭上眼睛,扳动了控制器。尾部喷气口咆哮起来。“周末客”号摇晃着,向前颤抖着。它挣脱了达格纳姆的登船者,挣脱了吉斯贝拉,挣脱了警告和恳求。它将福伊尔压回驾驶员座椅,承受着10G加速度带来的昏厥,这种加速度比驱使他的激情更不紧迫,更不痛苦,更不危险。
当他从视线中消失时,他脸上浮现出他被附身的血红色烙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