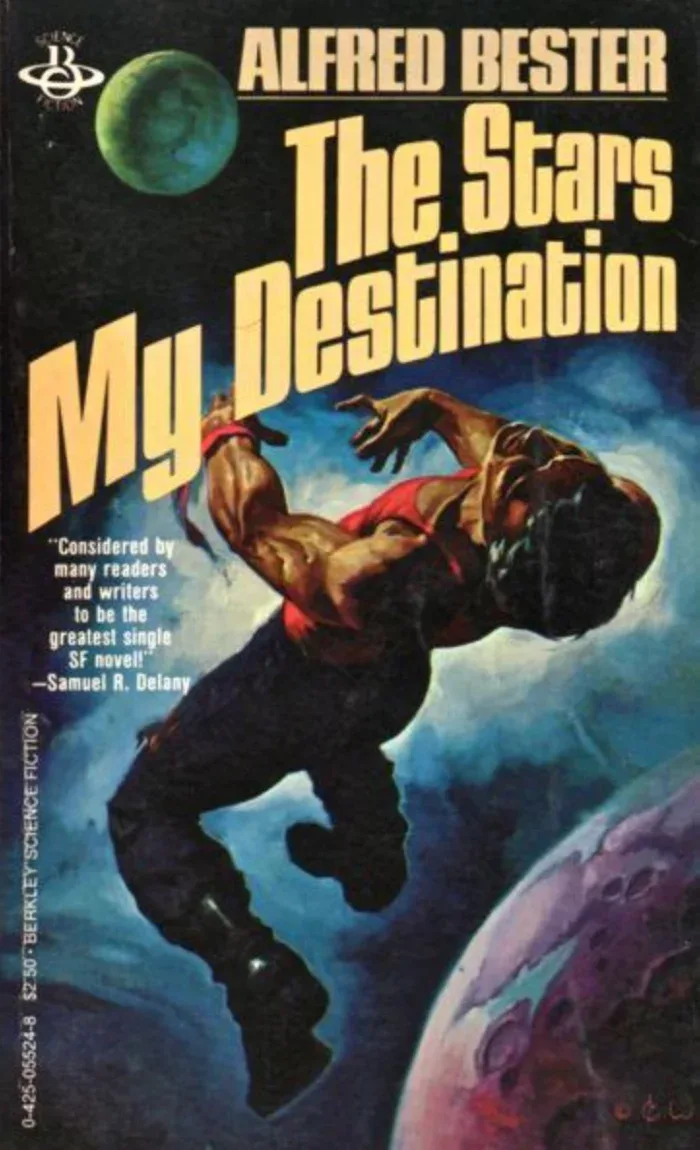第六章
哈利·贝克医生在华盛顿-俄勒冈州有一个小小的全科诊所,这是合法的,收入勉强够支付他每个周末参加撒哈拉流行的老式拖拉机拉力赛所消耗的柴油。他真正的收入来自他在特伦顿的怪胎工厂,贝克每周一、三、五晚上都会瞬移到那里。在那里,贝克收取巨额费用,不问任何问题,为娱乐业制造畸形怪物,并为黑社会重塑皮肤、肌肉和骨骼。
贝克看起来像个男接生婆,坐在他斯波坎豪宅凉爽的阳台上,听着吉兹·麦昆讲完她逃跑的故事。
“一旦我们逃到古夫尔·马特尔外的开阔地带就容易多了。我们找到一个猎人小屋,闯了进去,弄到些衣服。那里还有枪……漂亮的旧式钢制玩意儿,用炸药杀人的那种。我们拿了枪卖给了一些当地人。然后我们买了车票到我们记住的最近的琼特平台。”
“哪个?”
“比亚里茨。”
“夜里旅行,嗯?”
“当然。”
“对福伊尔的脸做了什么处理吗?”
“我们试过化妆,但没用。那该死的纹身还是会透出来。然后我买了深色的皮肤替代品喷了上去。”
“那管用了吗?”
“没有,”吉兹愤怒地说。“你必须保持脸部平静,否则替代品会开裂脱落。福伊尔控制不住自己。他总是这样。简直是地狱。”
“他现在在哪儿?”
“萨姆·夸特带着他呢。”
“我以为萨姆已经退出江湖了。”
“是的,”吉斯贝拉冷酷地说。“但他欠我一个人情。他照看着福伊尔。他们正在琼特线路上兜圈子,以躲避警察。”
“有趣,”贝克低声说道。“我这辈子都没见过纹身病例。以为那是一种失传的艺术。我想把他加入我的收藏。你知道我收集奇物,吉兹?”
“谁都知道你特伦顿那个动物园,贝克。真可怕。”
“我上个月弄到了一个真正的同胞囊肿,”贝克热情地开始说。
“我不想听这个,”吉兹厉声说道。“我也不想让福伊尔进你的动物园。你能把他脸上的脏东西弄掉吗?清理干净?他说综合医院的人束手无策。”
“他们可没有我的经验,亲爱的。嗯。我好像记得在哪儿读到过什么……在哪儿呢——”
“等一下。”贝克站起来,伴随着一声轻微的砰声消失了。吉斯贝拉在阳台上愤怒地踱步,直到二十分钟后他重新出现,手里拿着一本破旧的书,脸上带着胜利的表情。
“找到了,”贝克说。“三年前在加州理工学院的书库里看到的。你可以钦佩我的记忆力。”
“去你的记忆力。他脸上的事怎么样?”
“可以做到。”贝克翻动着脆弱的书页,沉思着。“是的,可以做到。靛蓝二磺酸。我可能得合成这种酸,但是……”贝克合上书,果断地点点头。“我能做到。只是,如果那张脸真像你描述的那么独特,动手脚似乎有点可惜。”
“你能不能别提你的爱好了,”吉斯贝拉恼怒地惊呼道。“我们现在是通缉犯,明白吗?第一个从古夫尔·马特尔逃出来的人。警察不会罢休,直到把我们抓回去。这对他们来说是特别重要的案子。”
“但是——”
“你觉得福伊尔顶着那张纹身脸到处跑,我们能在古夫尔·马特尔外面待多久?”
“你为什么这么生气?”
“我没生气。我在解释。”
“他在动物园里会很开心的,”贝克劝说道。“而且在那里他也能躲起来。我会把他安排在独眼女孩隔壁的房间——”
“动物园不行。这事没得商量。”
“好吧,亲爱的。但你为什么担心福伊尔被抓回去?那跟你没关系。”
“你为什么要担心我担心?我请你做个活儿。我付钱。”
“会很贵的,亲爱的,而且我喜欢你。我想帮你省钱。”
“不;你不是。”
“那我就是好奇。”
“那就当我是感激吧。他帮了我;现在我帮他。”
贝克玩世不恭地笑了笑。“那我们就帮他换张全新的脸吧。”
“不。”
“我就知道。你想清理他的脸,因为你对他那张脸感兴趣。”
“该死的,贝克,你到底做不做?”
“五千块。”
“细分一下。”
“一千合成酸。三千手术费。还有一千——”
“满足你的好奇心?”
“不,亲爱的。”他又笑了笑。
“一千给麻醉师。”
“为什么要麻醉?”贝克重新打开那本古老的书。
“看起来手术很疼。你知道他们怎么纹身吗?他们拿一根针,蘸上染料,然后敲进皮肤里。要漂白那些染料,我得用针在他脸上一点一点地过,一针一针地把靛蓝二磺酸敲进去。会很疼的。”
吉斯贝拉眼睛一亮。“你能不用麻药做吗?”
“我可以,亲爱的,但是福伊尔——”
“管他妈的福伊尔。我付四千。不用麻药,贝克。让福伊尔受罪。”
“吉兹!你不知道你让他承受什么。”
“我知道。让他受罪。”她笑得如此狂怒,把贝克都吓了一跳。“让他的脸也让他受罪。”
贝克的怪胎工厂占据了特伦顿火箭发射场后面一座五层楼的厂房,那里曾是A.C.W.公司的地铁车厢制造厂,后来琼特技术终结了城市地铁的需求。厂房的后窗正对着发射场的圆形坑口,反重力光束向上射出,贝克的病人们可以看着宇宙飞船在光束中静静地上上下下,舷窗闪耀,识别信号闪烁,船体因大气带走外太空积累的静电荷而泛起圣艾尔摩之火的涟漪。
工厂的地下室是贝克的解剖奇物动物园,里面有买来的、雇来的、绑架来的、诱拐来的天生怪胎和畸形人。贝克,像他那个世界的其他人一样,狂热地迷恋这些不幸的生物,花大量时间与他们待在一起,沉浸在他们扭曲形态的景象中,就像其他人沉醉于艺术之美一样。工厂的中间楼层是术后病人的卧室、实验室、员工休息室和厨房。顶层是手术室。
在其中一间手术室,一个通常用于视网膜实验的小房间里,贝克正在处理福伊尔的脸。在一排刺眼的灯光下,他俯身在手术台上,用一把小钢锤和一根白金针细致地工作着。贝克沿着福伊尔脸上旧纹身的图案,找出皮肤上每一个微小的疤痕,并将针刺入其中。福伊尔的头被夹具固定着,但他的身体没有被捆绑。每次锤子敲击时,他的肌肉都会扭动,但他从未移动身体。他紧紧抓住手术台的两侧。
“控制,”他咬着牙说。“你想让我学会控制,吉兹。我正在练习。”他畏缩了一下。
“别动,”贝克命令道。
“我这是在逗乐呢。”
“你做得不错,孩子,”萨姆·夸特说着,脸色难看。他斜眼瞥了一眼吉斯贝拉愤怒的脸。“你说呢,吉兹?”
“他在学习。”
贝克继续蘸着针,敲打着。
“听着,萨姆,”福伊尔含糊不清地咕哝道。“吉兹告诉我你有一艘私人飞船。犯罪有回报,嗯?”
“是的。犯罪有回报。我有个小小的四人座。双喷气引擎。那种他们叫‘土星周末客’的。”
“为什么叫土星周末客?”
“因为土星上的一个周末会持续九十天。她能携带三个月的食物和燃料。”
“正合我意,”福伊尔咕哝道。他扭动着身体,控制住了自己。“萨姆,我想租你的船。”
“干什么用?”
“棘手的事。”
“合法的?”
“不。”
“那就不适合我了,孩子。我已经失去勇气了。跟你一起在电路上瞬移,领先警察一步,让我明白了这一点。我已经彻底退休了。我只想安宁。”
“我付五万。你不要五万吗?你可以星期天数钱玩。”
针无情地敲打着。福伊尔的身体每次撞击都在抽搐。
“我已经有五万了。我在维也纳一家银行里有十倍于此的现金,”夸特从口袋里掏出一串闪闪发光的放射性钥匙。“这是银行的钥匙。这是我在约翰内斯堡住所的钥匙。二十个房间;二十英亩地。这儿是我的‘周末客’在蒙托克的钥匙。你诱惑不了我,孩子。我在领先的时候就退出了。我要瞬移回约翰内斯堡,安度余生。”
“让我用‘周末客’吧。你可以安安稳稳地坐在约翰内斯堡收钱。”
“什么时候收?”
“等我回来。”
“你想要我的船,凭信任和一句承诺?”
“担保。”
夸特哼了一声。
“什么担保?”
“这是小行星带里的一个打捞任务。船名叫诺玛德号。”
“诺玛德号上有什么?是什么让打捞有回报?”
“我不知道。”
“你在撒谎。”
“我不知道,”福伊尔固执地咕哝道。“但一定有什么值钱的东西。问吉兹。”
“听着,”夸特说,“我要教你点东西。我们做的是合法的,明白吗?我们不砍不抢。我们不隐瞒。我知道你在想什么。你手上有好东西,但你不想让别人分一杯羹。这就是你求情的原因……”
福伊尔在针下扭动着,但仍被自己的执念所控制,被迫重复道:“我不知道,萨姆。问吉兹。”
“如果你有个诚实的交易,就提出一个诚实的建议,”夸特愤怒地说。“别像只该死的纹身老虎一样四处徘徊,盘算着怎么扑上去。我们是你唯一的朋友。别想耍手段——”
夸特被福伊尔嘴里迸出的一声惨叫打断了。
“别动,”贝克心不在焉地说。“你脸一抽搐,我就控制不住针了。”他严厉地看了吉斯贝拉很久。她的嘴唇颤抖着。突然,她打开钱包,拿出两张面值500信用点的钞票。她把它们放在酸液烧杯旁边。
“我们在外面等,”她说。
她晕倒在大厅里。夸特把她拖到一把椅子上,找来一个护士用芳香氨水让她苏醒过来。她开始剧烈地哭泣,把夸特都吓坏了。他遣散了护士,在一旁徘徊,直到抽泣声平息。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他质问道。“那钱是什么意思?”
“那是血汗钱。”
“为了什么?”
“我不想谈这个。”
“你没事吧?”
“没事。”
“我能做些什么吗?”
“不能。”
沉默了很久。然后吉斯贝拉用疲惫的声音问道:“你打算和格利做那笔交易吗?”
“我?不。听起来像千分之一的机会。”
“诺玛德号上一定有什么值钱的东西。否则达格纳姆不会追着格利不放。”
“我还是没兴趣。你呢?”
“我?也没兴趣。我不想再和格利弗·福伊尔扯上任何关系。”
又停顿了一下,夸特问道:“我现在可以回家了吗?”
“你日子过得挺艰难的,是吧,萨姆?”
“我想我大概死了一千次,在电路上照顾那只老虎。”
“对不起,萨姆。”
“这是我应得的,毕竟你在孟菲斯被抓时我对你做了那样的事。”
“抛弃我是人之常情,萨姆。”
“我们总是做自然而然的事,但有时我们不该这样做。”
“我知道,萨姆。我知道。”
“然后你用余生去弥补。我想我运气不错,吉兹。今晚我能弥补了。我现在可以回家了吗?”
“回约翰内斯堡过幸福生活?”
“嗯哼。”
“别丢下我一个人,萨姆。我为自己感到羞耻。”
“为什么?”
“虐待哑巴动物。”
“那是什么意思?”
“别在意。再待一会儿。跟我说说幸福生活。幸福生活有什么好幸福的?”
“嗯,”夸特沉思着说。“就是拥有你小时候想要的一切。如果你五十岁时能拥有十五岁时想要的一切,你就幸福了。现在,当我十五岁的时候……”夸特滔滔不绝地描述着他童年时的象征、抱负和挫折,他现在正在满足这些,直到贝克走出手术室。
“结束了?”吉斯贝拉急切地问道。
“结束了。我给他麻醉后,工作速度快多了。他们现在正在给他包扎脸。他几分钟后就出来了。”
“虚弱吗?”
“当然。”
“绷带多久能拆掉?”
“六七天。”
“他的脸会干净吗?”
“我以为你对他那张脸不感兴趣呢,亲爱的。应该会干净。我想我没有漏掉一点色素。你可以钦佩我的技术,吉斯贝拉……还有我的精明。我准备支持福伊尔的打捞之旅。”
“什么?”
夸特笑了。“你要冒千分之一的风险赌一把,贝克?我以为你很聪明。”
“我是。他在麻醉状态下说话了。诺玛德号上有两千万的白金条。”
“两千万!”萨姆·夸特脸色一沉,转向吉斯贝拉。但她也怒火中烧。
“别看我,萨姆。我不知道。他也瞒着我。发誓说他从不知道达格纳姆为什么追着他不放。”
“是达格纳姆告诉他的,”贝克说。“他也把这个漏了出来。”
“我要杀了他,”吉斯贝拉说。“我要亲手把他撕碎,你不会在他尸体里找到任何东西,除了黑色的腐烂物。他会成为你动物园里的奇物,贝克;我真希望当初让你得到他!”
手术室的门开了,两个勤务兵推着一辆手推车出来,福伊尔躺在上面,轻微抽搐着。他整个头颅都被白色的绷带包裹着,像一个白色的手套。
“他有意识吗?”夸特问贝克。
“我来处理,”吉斯贝拉脱口而出。“我会跟这个混蛋——福伊尔!”
福伊尔透过绷带面罩微弱地回答。就在吉斯贝拉愤怒地吸气准备发动攻击时,医院的一面墙壁消失了,随之而来的是一声雷鸣般的巨响,将他们震倒在地。整栋建筑在反复的爆炸中摇晃,穿着制服的人开始从外面的街道瞬移进来,穿过墙壁的缺口,像乌鸦般扑向战场的腹地。
“突袭!”贝克喊道。“突袭!”
“耶稣基督!”夸特颤抖着。
穿着制服的人蜂拥而至,遍布整个地方,喊叫着:“福伊尔!福伊尔!福伊尔!福伊尔!”
贝克砰的一声消失了。服务员们也瞬移走了,丢下了手推车,福伊尔在上面虚弱地挥舞着胳膊和腿,发出微弱的声音。
“这是他妈的突袭!”
夸特摇晃着吉斯贝拉。“走,姑娘!走!”
“我们不能丢下福伊尔!”吉斯贝拉喊道。
“醒醒,姑娘!走!”
“我们不能抛弃他。”
吉斯贝拉抓住手推车,沿着走廊跑去。夸特在她旁边跑着。医院里的咆哮声越来越响:“福伊尔!福伊尔!福伊尔!”
“看在上帝的份上,别管他了!”
夸特催促道。“让他们抓走他。”
“不。”
“如果我们被抓到,对我们来说就是脑叶切除术,姑娘。脑叶切除术,吉兹!”
“我们不能抛弃他。”
他们滑过一个拐角,撞进一群尖叫着的术后病人中,有扑扇着翅膀的鸟人,像海豹一样拖着身体在地板上爬行的美人鱼,阴阳人,巨人,侏儒,双头双胞胎,半人马,还有一个喵喵叫的斯芬克斯。他们惊恐地抓挠着吉斯贝拉和夸特。
“把他从手推车上弄下来,”吉斯贝拉喊道。
夸特猛地把福伊尔从手推车上拽下来。福伊尔站起来,摇晃了一下。吉斯贝拉扶住他的胳膊,萨姆和吉兹两人把他拖过一扇门,进入一个病房,里面住满了贝克的时间怪胎……有着加速时间感的病人,像蜂鸟一样以闪电般的速度在病房里飞掠,发出刺耳的蝙蝠般的尖叫声。
“把他瞬移出去,萨姆。”
“在他试图欺骗和剥削我们之后?”
“我们不能抛弃他,萨姆。你现在应该知道了。把他瞬移出去。凯斯特的地方!”
吉斯贝拉帮助夸特把福伊尔扛到肩上。时间怪胎似乎用尖叫的条纹填满了整个病房。病房门被撞开。十几发气动枪的子弹呼啸着穿过病房,击中了正在旋转的时间病人。夸特被猛地撞到墙上,福伊尔掉了下来。他太阳穴上出现了一块青紫色的瘀伤。
“快滚出去,”夸特吼道。“我完了。”他喘着气。“我完了。不能琼特了。走,姑娘!”
夸特试图摆脱阻止他瞬移的脑震荡,挺直身体向前冲去,迎向涌入病房的穿制服的人。吉斯贝拉抓住福伊尔的胳膊,把他拖出病房后部,穿过一个餐具室、一个诊所、一个洗衣房,走下一段段吱嘎作响、扬起白蚁尘土的古老楼梯。
他们来到一个食品储藏室。贝克的动物园里的动物在混乱中冲出了牢笼,像蝙蝠闯入被攻击的蜂巢,贪婪地享用着蜂蜜一样洗劫着储藏室。一个独眼女孩正用手从桶里舀起黄油塞进嘴里。她鼻子上方那只独眼瞪着他们。
吉斯贝拉拖着福伊尔穿过食品储藏室,找到一扇闩着的木门,一脚踢开。他们踉跄着走下一段摇摇欲坠的台阶,发现自己身处一个曾经是煤窖的地方。头顶上传来的震动和轰鸣声听起来更深沉、更空洞。地窖一侧的一个煤槽口被一扇铁门挡住,门上有铁夹固定。吉斯贝拉把福伊尔的手放在铁夹上。他们一起打开了铁夹,通过煤槽爬出了地窖。
他们在怪胎工厂外面,紧贴着后墙。眼前是特伦顿火箭发射场,就在他们喘息的时候,吉兹看到一艘货船沿着反重力光束滑入一个等待的坑中。它的舷窗闪耀着,识别信号像一个刺眼的霓虹灯标志一样闪烁,照亮了医院的后墙。
一个人影从医院屋顶跳下。是萨姆·夸特,试图进行一次绝望的逃亡。他张牙舞爪地冲入空中,试图抓住最近坑口向上喷射的反重力光束,那光束或许能在半空中接住他,缓冲他的坠落。他的目标很完美。离地七十英尺时,他正好落入光束的轴心。但光束没有运行。他坠落下去,砸在了坑的边缘。
吉斯贝拉抽泣起来。仍然下意识地抓住福伊尔的胳膊,她跑过布满裂缝的混凝土,跑到萨姆·夸特的尸体旁。在那里,她松开福伊尔,温柔地触摸着夸特的头。她的手指沾满了血。福伊尔撕扯着眼前的绷带,透过纱布抠出两个眼洞。他自言自语着,听着吉斯贝拉的哭泣,听着身后贝克工厂传来的喊叫声。他的手在夸特的尸体上摸索着,然后他站起来,试图把吉斯贝拉拉起来。
“得走了,”他嘶哑地说。“得离开。他们看见我们了。”
吉斯贝拉一动不动。福伊尔鼓足全身力气,把她拉直。
“时代广场,”他咕哝道。“琼特,吉兹!时代广场。琼特!”
穿着制服的人影出现在他们周围。福伊尔摇晃着吉斯贝拉的胳膊,瞬移到了时代广场,那里巨大平台上成群的琼特者惊讶地盯着那个顶着白色绷带球脑袋的巨人。平台有足球场那么大。福伊尔透过绷带模糊地环顾四周。没有吉斯贝拉的踪影,但她可能在任何地方。他提高嗓门喊道。
“蒙托克,吉兹!蒙托克!福利平台!”
福伊尔用尽最后一点力气和一丝祈祷进行了瞬移。一股冰冷的西北风正从布莱克岛吹来,将脆弱的冰晶扫过位于一处被称为费舍尔傻事的中古废墟遗址上的平台。平台上还有另一个人影。福伊尔顶着风雪蹒跚地走向那个人影。是吉斯贝拉,看起来冻僵了,迷失了方向。
“谢天谢地,”福伊尔咕哝道。“谢天谢地。萨姆把他的周末客停在哪儿了?”
他摇了摇吉斯贝拉的手肘。“萨姆把他的周末客停在哪儿了?”
“萨姆死了。”
“他把那艘土星周末客停在哪儿了?”
“他退休了,萨姆。他再也不害怕了。”
“船在哪儿,吉兹?”
“在灯塔下的船坞里。”
“来吧。”
“去哪儿?”
“去萨姆的船。”
福伊尔把大手伸到吉斯贝拉眼前;一串发光的钥匙躺在他手心。“我拿了他的钥匙。来吧。”
“他给你的?”
“我从他尸体上拿的。”
“食尸鬼!”
她开始笑起来。“骗子……色鬼……老虎……食尸鬼。行走的癌症……格利弗·福伊尔。”
尽管如此,她还是跟着他穿过暴风雪,走向蒙托克灯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