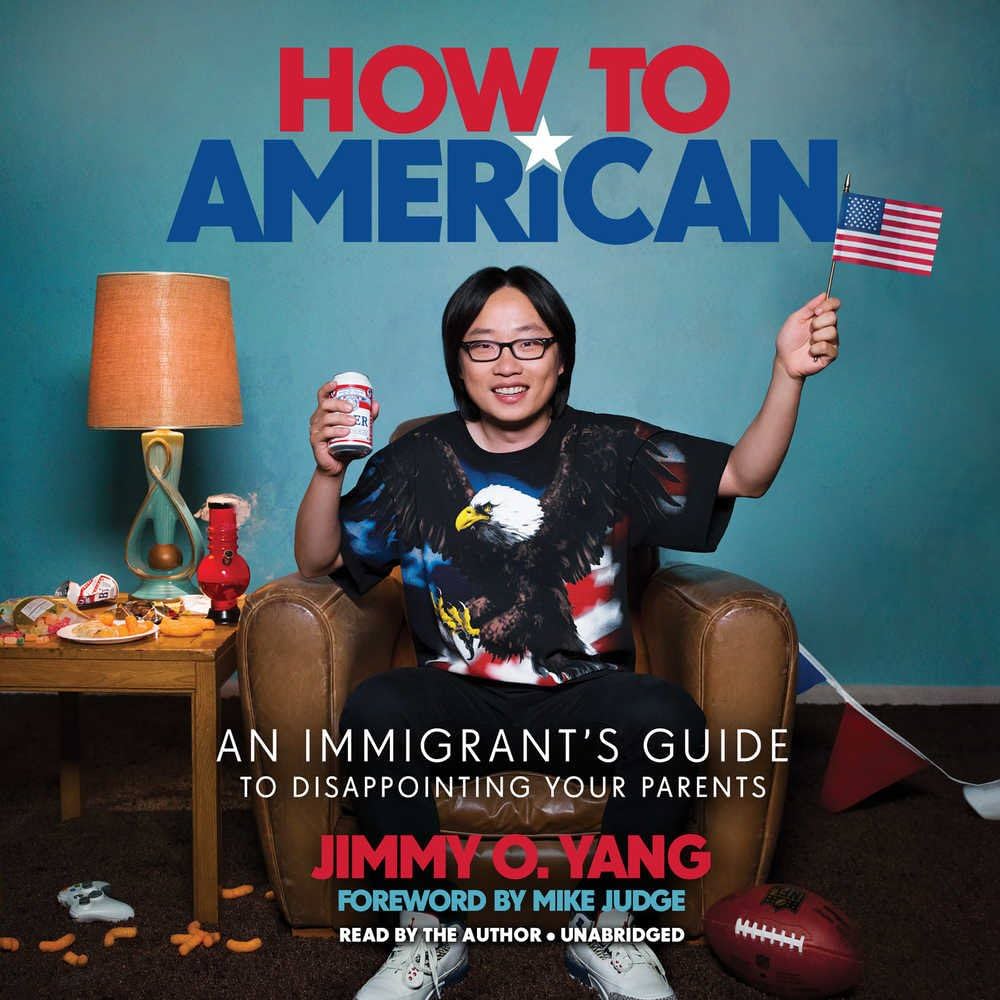高中里,每个人都属于某个小团体(clique),午餐时他们有特定的聚集点。酷酷的运动员坐在游泳馆前面,滑板小子坐在前草坪上,开着时髦宝马的波斯裔在自助餐厅里游荡。就像电影《独领风骚》(Clueless)里艾丽西亚·希尔维斯通(Alicia Silverstone)介绍各个团体的场景一样。事实上,《独领风骚》的调研就是在比弗利山高中完成的,我们现实中的英语老师霍尔先生(Mr. Hall)还在电影里扮演了介绍布列塔尼·墨菲(Brittany Murphy)角色的校长。那是他在好莱坞的成名作,学校里的每个人都认为霍尔先生是个大明星。作为并非来自比弗利山小学体系的新鱼,我再次置身于陌生人的海洋中。高中第一天我谁也不认识,也不属于任何那些小团体。午餐时无处可去,我只能背靠着储物柜站着,希望没人注意到我,默默地吃着我爸给我准备的奇怪的中式午餐。我通常的午餐是爸爸前一天晚上做的中餐,装在特百惠(Tupperware)盒子里;从梅菜扣肉到红烧鳗鱼,什么都有。每周有一次,爸爸会给我带一个“热口袋”(hot pocket)。那不是普通的美国火腿奶酪热口袋;而是一个装满了从中国超市买来的糯米的热袋子。看起来像宇航员食品,但闻起来像唐人街的后巷。说实话,还挺好吃的,但这糯米袋子绝对没帮我看起来像个正常的酷酷的美国孩子。我非常想找到一个身份认同,以便能够归属。有没有矮个子孩子的团体?有没有以前打乒乓球的孩子的团体?尽管我极力不想再当那个外国孩子……有没有外国孩子的团体?
比弗利高中一位年长但精力充沛的华人美术老师刘波(Po Lau)主持着学校的中华文化俱乐部(Chinese Culture Club)。那其实算不上一个有宗旨的俱乐部;只是一群中国学生午餐时聚集在刘波老师的教室里打牌和玩电子游戏。尽管我很想成为美国人,中华文化俱乐部还是成了我午餐时的避难所。我每天和刘波老师以及学校里仅有的另外三个中国孩子一起,吃着我们奇怪的中式午餐。感觉就像回到了香港叔叔家。刘波老师甚至会用他那蹩脚的粤语口音讲着蹩脚的笑话来逗我们:
“嘿,你们的扑克牌呢?”
“我们正在玩呢,波叔。”
“你们有红牌和黑牌,对吧?”
“是啊……”
“但你们的绿卡(green card)呢?!”
他被自己的烂梗逗得前仰后合,而我们则为他感到尴尬地摇着头。
中华文化俱乐部是个不错的安全网,但感觉像是一种倒退。我不想高中接下来的四年都和另外三个中国孩子躲在一个潮湿的教室里冬眠;这种事我在香港就能做。我想要拥有纯正的美国高中青春体验。我想参加返校节(homecoming)的橄榄球比赛,我想开着我爸的车进行一次公路旅行,我想和一个白人女孩去参加毕业舞会(prom)。我不在乎和酷孩子们混在一起,但我厌倦了当外国孩子。我只想做一个“普通”的美国孩子。
我在比弗利山高中交到的第一个非华裔朋友是在九年级第二学期。杰里米(Jeremy)是橄榄球队的一个波斯裔孩子,但他既不像典型的波斯人,也不像典型的橄榄球运动员。我们在六年级的计算机课上一起取笑其他同学,很快就打成一片。杰里米和他的朋友们在自助餐厅旁边的顶楼有一张桌子。我开始偷偷溜出中华文化俱乐部,和他们一起玩。他们是我见过自从“We Are the World”(著名慈善歌曲)音乐视频以来最多元化的一群哥们儿。杰里米和他表弟菲尔·亚德加里(Phil Yadegari)是波斯人,喜欢星球大战、Madden橄榄球游戏和正义联盟这些普通的美国青少年玩意儿;扎基·哈希姆(Zaki Hashem)是来自孟加拉国的优等生;金波(Bo Kim)是一个安静的韩国移民;克里斯·奥康纳(Chris O’Connor)是个高高瘦瘦的半白人、半美国原住民的家伙,穿着大三号的T恤;德里克·华(Derek Wah)是个ABC(American-born Chinese,在美国出生的华人),他的父母也来自上海,他会说上海话。当一个上海人在美国遇到另一个上海人时,就像找到了一个生日相同、恰好还是失散多年的表亲的最好朋友。这是一种瞬间的连接。最棒的是,德里克和我可以一起用上海话取笑其他人。德里克、杰里米、菲尔、扎基、波、克里斯和我很快就成了最好的朋友。
这个团体里没有人符合任何特定的高中类型,也没人在乎。这群混杂的朋友成了我高中余下时光的小团体。我们不是学校里最酷的孩子,但也不是书呆子。我们不太在乎别人怎么看我们。我一直想象中的美国高中经历是,一个英俊的白人高中四分卫在返校节打入制胜的达阵球,然后在返校节舞会上与啦啦队长慢舞。但这群来自不同背景的多元化人群,反映了一个更真实的美国:一个移民国家。
我们从没做过像聚会或未成年饮酒那样酷的事情;我们只是放学后扔扔橄榄球,在菲尔家玩Madden游戏。我每天晚上都有严格的回家吃晚饭的门禁。如果我七点还没到家,我爸就会打电话给我,用愤怒的上海话对我大吼大叫:
“侬死忒了啊?!”(你死了吗?!)
“没,我在杰里米家玩游戏呢。”
“没死么哪能(为什么)还不回来吃饭?”
“我晚点回来。”
然后他就会切换到经典的亚洲父母式的情感勒索。“侬觉得我死忒了啊?”(你觉得我死了吗?)
“啥?没啊。”
“那你为什么这样不尊重你父亲?”
“爸,我——”
“现在就回来吃饭!”然后他挂了电话。
我很确定这些电话给我造成了终生的情感创伤。
大多数美国孩子可能会反抗说:“去你的,爸!你管不着我!”但我不能。在中华文化里,不尊重长辈是最大的罪过。而且最重要的是,我理解我爸。妈妈走了,哥哥在上大学;我是他维系家庭的唯一纽带。我无法承受让爸爸一个人吃晚饭的负担。尽管我很想待在杰里米家,但我每晚都回家和爸爸一起吃晚饭。
BET说唱城
杰里米、菲尔和克里斯是2Pac、Snoop Dogg和Bone Thugs-n-Harmony等说唱歌手的忠实粉丝。我以前从未听说过这些名字,每当他们谈论这种嘻哈音乐时,我都觉得自己被排斥在外。我爸总是抱怨说唱音乐太吵,听起来像“和尚念经”。我们是听迈克尔·杰克逊、麦当娜和老鹰乐队长大的。我对嘻哈一无所知;我甚至不知道2Pac已经去世了。但我想融入我的朋友们,所以我开始接触我能找到的任何嘻哈音乐。就在那时,我发现了BET。
BET是Black Entertainment Television(黑人娱乐电视台)的缩写;这是一个服务于城市社区(urban community)的美国电视频道。后来我了解到,“城市”只是“黑人”的另一种说法。BET播放城市题材的电视剧、城市音乐和周日的城市福音音乐。收看BET就像打开了一个潘多拉魔盒,通往一个全新的美国世界。我从看尼克儿童频道(Nickelodeon)的动画片,转变为研究BET的说唱城(Rap City)。我被丰富多彩的嘻哈文化迷住了。每天,像50 Cent这样的说唱歌手会出现在说唱城,穿着XXXL号的篮球衫,脖子上戴着巨大的钻石链,倒数着最佳城市音乐录影带。每个音乐录影带都是通往一个我从未见过的新世界的大门。当我第一次看到Jay-Z的《Big Pimpin’》音乐录影带时,它改变了我的生活。对于那些不记得《Big Pimpin’》或者太“白”而不知道它的人来说,《Big Pimpin’》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音乐录影带。视频里有数百名穿着比基尼的美女在一艘价值百万美元的游艇上狂欢,而三位名叫Jay-Z、Bun B和Pimp C的说唱歌手则连续四分钟往她们身上倒香槟。而且那些女孩们都乐在其中!我那十五岁的移民大脑简直不敢相信我所看到的。这就是美国?我他妈的加入!《Big Pimpin’》是美国梦的缩影,我需要成为其中的一部分。我想像那些被称为说唱歌手的、高大威猛的美国超级英雄一样。我想像Jay-Z一样当个皮条客(pimp),像50 Cent一样当个黑帮分子(gangster)。我把我人生的目标定为过上《Big Pimpin’》那样的生活。每当我观看BET时,我都会忘记自己是一个矮小的外国中国男孩,感觉自己像个 badass 的黑帮分子。我开始模仿说唱歌手走路和说话的方式。我会走到同学面前说:“Yo what up, dog. 咱们几何老师是个 bitch, homie。”(“哟,咋样,哥们儿。咱们几何老师是个婊子,伙计。”)我是通过看BET学会说地道的美国英语的。我每天至少看三个小时的音乐录影带。这些音乐录影带是美国梦不同版本的片段。它们塑造了我的青春期,并在我高中毕业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激励着我。除了《Big Pimpin’》,以下是我最喜欢的一些教会我了解美国的音乐录影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