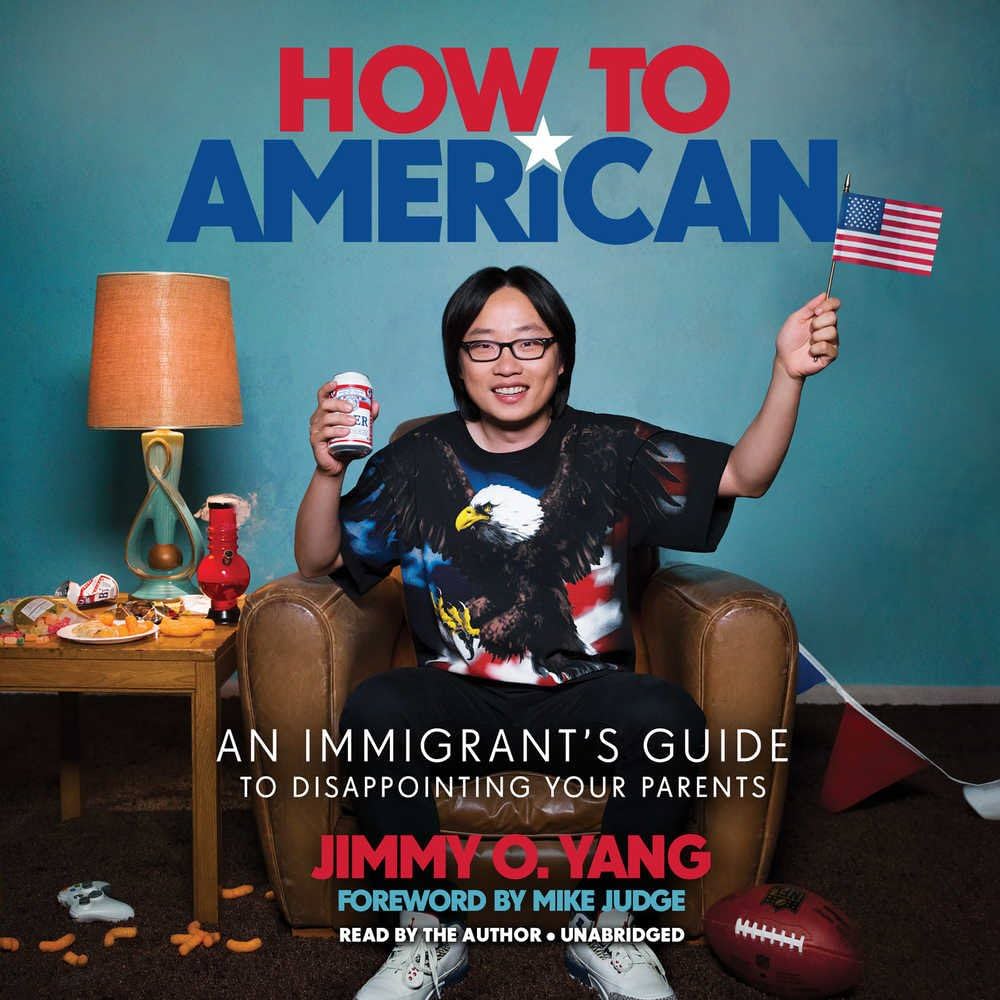我总觉得自己是个局外人,即使是在香港长大的中国孩子也是如此。香港曾是一个繁荣的英国殖民地,有自己的政府,香港人常常看不起他们来自中国大陆的邻居。虽然我出生在香港,但我父母是来自上海的大陆人。我在学校说粤语,回家说上海话,看普通话的电视节目。这些中国方言听起来就像西班牙语和意大利语一样差别巨大。我在香港的同学总是叫我“上海仔”。当孩子们因为我对父母说上海话、穿上海带来的衣服、吃我带到学校的上海菜而取笑我时,我不得不为自己辩护。我不介意这些取笑,但即使在我出生的城市,我也总感觉格格不入。这倒是为我们移民美国后如何融入环境做了些早期练习。
在香港,每个人都有一个法定的中文名字和一个英文昵称。我的法定名字是四个字的中文名。我的姓氏是罕见的复姓“欧阳”,我的名字是“万成”,中文意思是“一万个成功”。这是一个充满希望的名字,但也注定让我难以企及。无论我变得多成功,都无法达到父母那一万个成功的期望。“吉米”(Jimmy)是我父母给我取的英文昵称。
我成长在一个紧密的核心家庭,有父母和一个哥哥。我妈妈的英文名叫艾米(Amy),因为这听起来接近她的中文昵称“阿梅”(Ah-Mee)。我爸爸给自己取名理查德(Richard),“因为我想变得富有(rich)”,他这样向我解释。我哥哥名叫罗杰(Roger),因为我父母很喜欢罗杰·摩尔扮演的007。欧阳罗杰(Roger Ou Yang)从不喜欢他的英文名;他觉得听起来像个老白人。所以他把英文名改成了罗伊(Roy),一个老黑人的名字。我问父母为什么给我取名吉米。他们也说不出个所以然。我爸说:“就是听起来挺不错的。”
我妈妈是个时髦的女士,她太有抱负,不甘心只做个家庭主妇。她从全职妈妈转型为职业女性,在香港一家名为“Dapper”(意为“衣冠楚楚”)的高档服装店担任总经理。妈妈很会与人打交道,但说话也非常直率。这绝对是文化差异。亚洲阿姨们会当着你的面,直接告诉你脸上有什么问题,好像是在帮你似的。每次去看望父母,我都得做好心理准备。我妈经常用一连串非建设性的批评来迎接我:“吉米啊,你的脸怎么这么胖?你的衣服看起来像个无家可归的,头发那么长,看着像个女孩子。”三十年来一直如此,现在我对自己的印象就是一个肥胖、无家可归的女同性恋。
妈妈一直是个精明的购物者。她不是小气,而是讲究划算。有一次我全价买了一件五十美元的T恤;她差点气中风。
“吉米!你花五十块钱买那件衬衫?!你疯了吗?!我在中国花十块钱能给你买五件!”
然后我爸用拇指和食指搓了搓衬衫的料子,检验质量。“还不是百分之百纯棉。垃圾。”
我花了很长时间才适应在Ross(美国平价折扣店)以外的地方买东西。
我爸爸是个精明的商人和企业家。九十年代初,他在香港创办了一家蓬勃发展的医疗设备公司,后来我们来到美国后,他在美林证券(Merrill Lynch)担任财务顾问。他是终极评论家。他是美食评论家、电影评论家和人物评论家。我们去的每家餐厅,他都会抱怨食物、服务,甚至餐具。他就像个行走的Yelp(美国点评网站)评论:
“这牛肉比硬纸板还硬。比我在共产主义革命时期吃的垃圾还难吃。”
“用一次性筷子,还好意思叫自己高档餐厅?感觉像在吃熊猫快餐(Panda Express)。”
“这服务员真是个混蛋。他干嘛染红头发?都五十岁了。看起来像个无可救药的赌徒。”
唯一一家他从不抱怨的餐厅是卡乐星(Carl’s Jr.)。他能一口气吃掉两个六美元汉堡,这对任何人来说都是了不起的壮举,尤其对一个七十岁的中国老头来说。
食物是每个中国家庭的粘合剂,我们家也不例外。中国人是世界上最大的美食家;中国有句俗话:“民以食为天。”我们对待晚餐非常严肃。总是有四道家常中式菜肴,一份精心制作的当日例汤,外加新鲜出炉的米饭。爸爸对晚餐时间很认真。每晚七点,他都会扯着嗓子喊:“开饭啦!”如果我们晚了一分钟,他就会冲进我和哥哥正在玩的FIFA游戏房间:“你们是想吃饭还是想饿死?吃饭。现在!”我们连手柄上的一个按钮都不敢再按。
爸爸是家里的主厨。他擅长上海菜,比如他那道完美的红烧肉。每天,爸爸四点下班,五点开始做饭。我妈妈厨艺也还行,但每次她做晚饭,爸爸都会批评她的手艺。“阿梅,这汤太多水了。蘑菇要用大火爆炒,不是小火慢炖。”他把妈妈的烹饪职责限制在偶尔做个简单的豆腐菜上。爸爸其实有点为自己的厨艺感到不好意思。在重男轻女的中国文化里,女人应该待在家里做家庭主妇,包揽所有烹饪。爸爸偶尔会提醒我:“别像我一样最后在厨房里做饭,那应该是女人的活儿。但我能怎么办呢?我比你妈做得好。”有些人可能会称之为性别歧视;在我们家,这是一种反讽。
我和哥哥负责煮米饭。没有什么比搞砸米饭更能让我爸生气的了。我往电饭锅里放多少水,简直关系到生死存亡。煮饭是一门艺术。如果水放少了,米饭里面会夹生;如果水放多了,米饭就成了烂糊粥。要把饭煮好压力很大,因为爸爸精心准备的五道菜全取决于米饭的口感。每天晚上我都感觉自己像是F1赛车的维修站成员,必须换好轮胎。这是一份吃力不讨好的工作,但如果我搞砸了,就会毁掉所有人的比赛。我总是紧张地坐在餐桌旁,等着爸爸吃第一口米饭。如果煮得好,不会有任何表扬;但如果煮得不好:
“妈了个X的!”我爸会用上海话对着天花板大吼。“这饭是生的。今天谁煮的饭?”我会羞愧地举起我那双无能的手。总是我的错;我哥哥每次都能把饭煮得恰到好处。
在香港狭小的公寓里长大,我们从来没有空间养像样的宠物。我五岁时,哥哥和我养了几只蝌蚪,我们成功地把它们养成了青蛙。那就是我们的小狗。然后我八岁时,爸爸给了我们一个惊喜,带回了几只毛茸茸、有体温的宠物:他带回家三只小鸡。它们是那么可爱的小鸡宝宝。我们把它们放在二十楼阳台一个宽敞的笼子里,还能欣赏到美丽的城市景色。我们不被允许把它们拿出来玩,因为它们啄人挺疼的。但我们可以隔着笼子抚摸它们,我常常盯着它们可爱的黄色绒毛看上好几个小时。我们甚至给它们取了英文名字。我最喜欢的是加里(Gary);它是最小但最有活力的那只。它让我想起了我自己。看着它们长大就像看着蝌蚪慢慢变成青蛙。我为我们的进展感到非常自豪。有一天,我放学回家去看小加里和它的朋友们,却发现笼子是空的。我慌了。我检查了阳台、客厅、卧室,到处都找不到它们。天啊,它们是不是从阳台上掉下去了?然后我走到厨房里找爸爸:
“爸,加里去哪儿了?”
“它在这儿呢。”
爸爸指着他面前的炒锅,里面正滋滋作响地炸着鸡块。然后我才意识到,加里和它的朋友们从来就不是我们的宠物;它们只是从农场到餐桌的晚餐。我感到一阵恶心。我确信在那之后我再也无法去爱了。那天晚上我哭着吃完了晚饭。但我不得不承认:加里真好吃。
看美国动作片是香港当时的时髦事。我们痴迷于所有那些高大威猛的美国动作英雄:阿诺德、史泰龙、西格尔和尚格云顿。我们每隔一个周末就用录像机看《终结者2》。开场机器人革命的场景把我吓得要死,但接着阿诺德就会赤身裸体地从天而降,拯救我们所有人。我们最喜欢的本地名人之一是周星驰,他是香港的喜剧传奇,后来凭借《少林足球》和《功夫》成为国际明星。周星驰在香港创造了一种名为“无厘头”的喜剧电影类型。从粤语翻译过来,字面意思就是“没道理”。他将滑稽幽默与他标志性的面无表情的表演风格相结合,很像莱斯利·尼尔森在《空前绝后满天飞》和《白头神探》等经典杰瑞·朱克电影中的表演。周星驰是我的英雄,他的无厘头电影是我最早的喜剧启蒙。他我最喜欢的电影是《国产凌凌漆》,一部恶搞007系列的电影,片中周星驰扮演一个笨手笨脚的低级中国特工。其中的肢体幽默和道具幽默堪称一流。中国的007拿出一个绝密道具箱。里面有一部其实是剃须刀的手机,一个其实是吹风机的剃须刀,和一个其实是剃须刀的吹风机。这些笑料的创意给了我一些最美好的童年回忆。周星驰是我香港版的“三个臭皮匠”、劳莱与哈代和彼得·塞勒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