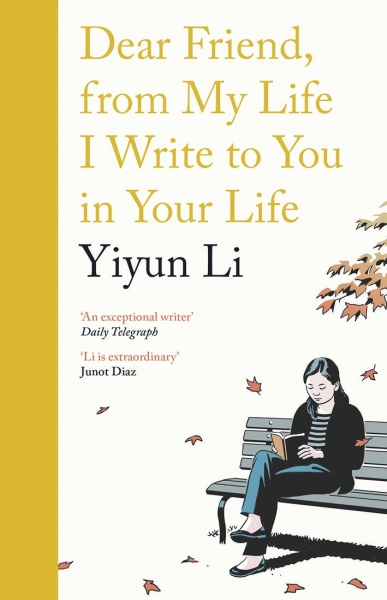茨威格夫妇——他们为爱娃安排了旅行文件,并为她找到了寄宿家庭(“你们尽可放心,我们会照顾好她,把她带大,也许还会带点美国口音回来,”斯蒂芬写信给她的父母)——在得知“贝拿勒斯城号”灾难的消息前,刚刚收到电报,告知爱娃已安全抵达。“在报纸上读到灾难消息的震惊,对我们来说和对你们一样巨大,我能理解你们的感受,”洛特写信给她的哥哥和嫂子。“那个念头困扰了我们好几天。幸运的是,你们的电报前一天晚上就到了……好吧,至少她安全了……”
信中没有具体说明那个念头是什么——坠入地狱不必被完全想象出来。洛特接着描述了彼得罗波利斯充满异国情调的、宁静的景色。“好吧,至少她安全了。”这句话,既坦率又令人不快,在我读信时显得格外突出。那是在我两次住院之间;我常常在人们试图让别人感觉好些的努力中,看到一种轻视。
那句“好吧,至少”所表达的情绪,在战时和日常生活中都很熟悉。大约在“贝拿勒斯城号”沉没的同时,上海一位母亲因白喉失去了她年幼的儿子。“好吧,至少,”毫无疑问,人们会指出——如果他们费心去安慰她的话——她还有两个年长的孩子,而且肚子里还有一个新的。
窥见他人不幸的深度,让我们抓住希望,以为痛苦是可以衡量的。有更悲伤的悲伤,更绝望的绝望。当我们认识到他人的痛苦时,我们无法避免面对自己的痛苦,于是我们逃向可衡量性的想法。“好吧,至少,”我们强调。我们安慰他人的能力,仅限于我们能用来安慰自己的方式。
茨威格夫妇的信是用英文写的。收信人——洛特的哥哥、嫂子和母亲——当时住在英国,德文信件会受到更严格的检查。阅读斯蒂芬的原文信件对我很有吸引力,因为我只读过他著作的译本。阅读洛特的话也很重要;毕竟,她在相当年轻的时候就决定结束自己的生命。
他们从巴西寄出的信件,尤其是后期的,笼罩在忧郁之中。在他们生命的最后阶段,洛特几次描述他们如何在上午十一点到中午之间坐在前门台阶上,徒劳地等待邮递员带来欧洲和美国的信件。“我们感觉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远离你们了,”斯蒂芬写道。等待是奸诈的。它不像灾难那样干净利落地摧毁一个人,而是侵蚀希望的基础。“我们每天都在所有报纸上寻找好消息,”斯蒂芬在为爱娃安排旅行前后写道。第二年,在撰写一部他未能完成的蒙田传记时,他写道:“在这些日子里读蒙田,读所有那些善于教导人顺从的人,是件好事。”
在顺从中,斯蒂芬放弃了对可衡量性的信念——痛苦没有等级之分。在南美的信件中,他常常提醒自己,他的处境——远离战争,有地方写作——是值得羡慕的。但是,我们如何比较斯蒂芬·茨威格的绝望——他在去世前几天参加了里约的狂欢节,并表达了他“在这样一个几乎全世界都在用爆炸杀人的时代,目睹如此奇幻的欢乐爆发的复杂感受”——和一个在中国十五岁女孩的绝望?她因看不到困在村庄里的生活的希望而喝下了除草剂。她生命最后的日子被媒体拍摄下来,从担架上的女孩到裹在塑料布里的尸体。
“实际上没什么可说的,因为我们的私生活现在无足轻重,而公共事件已经有足够的曝光度了,”斯蒂芬·茨威格在1941年12月31日写道。将个人的痛苦掌握在自己手中:这难道不也是一种反抗,一种拒绝让自己的生命被用来衡量他人生命的表现吗?
—
**纪念日前几天,我接受了一个广播节目的采访。本意是谈论书籍,但有一段时间,我被要求回忆四月的抗议如何发展到六月的流血事件。“肯定有人事先可以做些研究的,”事后一位朋友说。“不,这跟研究无关,”我回答,“这是关于把一个历史事件置于一个个人故事中。”接下来的几天,我拒绝了几个采访请求。“我能说的一切都已说过,”我在最后一封邮件中写道。“希望你理解我没有什么可以补充的了。”
事实是,我的不耐烦来自于这样一个事实:能在广播节目或电视上说的话,总是简化或歪曲。希望个体经验与更宏大的事物相联系的渴望,来自观众和演员双方,而表演的评价则基于其与时代的相关性。一个人要么必须服从那个剧本,要么选择只按照自己的方式说话。
在任何采访中,都不可能谈论那顶简爱帽。还有其他无法讲述的记忆。流血事件一周后我们返校时,一个住在广场附近的朋友用各种各样的故事逗我们发笑。其中最无伤大雅的一个是关于她叔叔的,他会趁她祖父母不注意时打开一罐可口可乐。可口可乐,或任何软饮料,在当时都是稀罕物,那“砰”的一声会让老两口因紧张而跳起来,就像听到枪声一样。我们当时笑了,这是否残忍?那个夏天之后,她离开中国去了德国与父母团聚,后来给我们寄来一个包裹,里面有巧克力和一盒磁带,她在上面录下了关于她新生活的故事。我们三个人听着她的独白:在机场不小心把自己锁在错误的洗手间里,盯着手推车上的苹果看得出神而踩到狗屎,一句德语也不会就去上学(她父母曾安排她在北京上夜校学德语,但她要么逃课,要么带了垃圾言情小说去看)。
轮到我们录一盒磁带寄给她时,我们却迟迟没有行动。北京还是那个城市,在那个十一月的傍晚,风大尘多;高中还是那个地方,有些同学问起她的消息,有些已经忘了她。前一个夏天,戒严令实施期间,我们四个常骑自行车去一个哨所,那里驻扎着一个暗恋她的士兵和他的部队。当他得到半小时假时,我们站在街角,看着我们的朋友向他控诉人民解放军的罪行。那个还不满二十岁、脸红扑扑的小战士,恳求她不要以身涉险。戒严令持续到第二年,但在她离开后,我们没有再去过那个哨所。找不到能让朋友发笑的故事,我们吃了巧克力,最终什么也没寄给她。
—
我从小就熟悉一个人的记忆。她出生时,她的母亲——因白喉失去了一个儿子——已经疯了。女孩在十岁到十八岁之间照顾母亲,而她的父亲和年长的哥哥姐姐们则在别处追求自己的事业。那些年里,有过一段青涩的恋情,对方是一个因肺结核而不得不从护士学校退学的学生。他在母亲和女儿住的院子对面租了一间房。那个场景——她坐在自家窗前,心不在焉地做着功课,而他则把胳膊搭在自己的窗台上和她说话——这个场景被向我描述过很多次。它是如此熟悉,仿佛出自茨威格的故事。人毫不费力就能理解它。女孩失去了母亲,母亲死在疯人院里;女孩也因那个年轻人的早逝而失去了他。但外部的不幸——疾病、瘟疫、战争、自然灾害——并非情节剧。情节剧是对原始瞬间的绝对忠诚。
一些批评家指出我的小说不够政治化。一个年轻人在一次朗读会上质问我,质疑我对成为一个政治作家不感兴趣。中国一位记者告诉我,大多数作家相信自己对我们这个时代负有历史责任。“你为什么不能达到那种期望?”他们问。而我的回答,如果我非要给一个的话,是这样的:我生命中的大部分时间都在拒绝别人交给我的剧本,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美国;我拒绝被他人意志所定义,这是我唯一且仅有的政治宣言。
情节剧从来都不是政治性的。操纵我笔下人物的记忆,不是我的责任。除了人物自己,任何人都无权给他们的经历贴标签,或将意义强加于他们的记忆,这样做是僭越的。这样做的角色自有其目的,但那不是我的目的。我的好奇心在于观察记忆,无论是作为情节剧还是作为受控的叙事,如何在时间中存续。我们当中谁敢断言,我们的记忆没有被时间玷污?时间,最甜美的毒药,最苦涩的解药,不可信赖的盟友,可靠的毁灭者。
—
有时我想象,写作是我进行的一项调查,询问我遇到的每一个人,无论是在现实中还是在小说里:你生命的多大一部分是为了被他人知晓而活?为了被理解?你生命的多大一部分是为了了解和理解他人而活?但像所有的调查一样,这些问题都是简化。一个人在多大程度上信任他人,愿意被知晓、被理解;一个人在多大程度上相信一个人了解和理解另一个人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