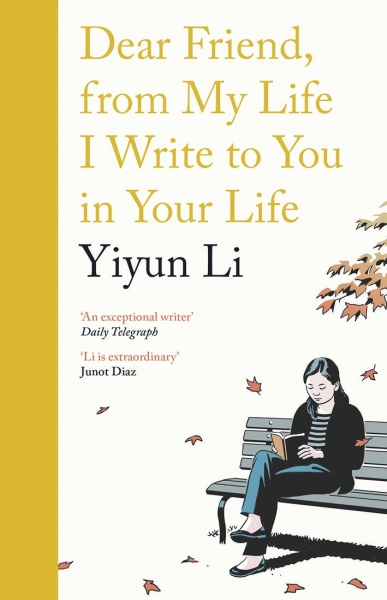在理想状态下,论辩是一种承诺——双方通过给予和接受,发现新的东西。但这种信念就像年轻人对爱情完美无瑕的看法一样天真。人性的占有欲将爱或论辩变成了完全不同的东西:获胜、征服、拥有、毁灭。
论辩的才能于是变成了寻找合适的对手——那些可以被震慑或胁迫而表示同意的人——并将那些无法做到的人视为无关紧要而加以摒弃。这种才能需要观众。世界将永远引用曼对茨威格之死的评论。然而,后者的沉默最终胜出。
还有另一种应对同样自身免疫状况的方法。我有个朋友擅长从他人的角度反驳自己,即使她能看穿对方论点的谬误。心智为了避免攻击自身,变成两个:一个通过与他人结盟而受到保护;另一个通过保持安静而避免被征服。一个通过克制而得以保全的自我,将是最终胜出的自我。
—
我姐姐大学时有个同学患了红斑狼疮。她似乎对英年早逝泰然处之,事实上她也只剩下不到两年的生命了。她躺在宿舍的双层床上,会谈论她的男朋友,他在香港一个富裕家庭当保镖,以及他给她买的昂贵裙子,她计划在死后分给朋友和同学。当我读伊丽莎白·鲍恩的传记时,我在鲍恩母亲身上认出了那个年轻女子的不羁。当鲍恩母亲在四十多岁时被诊断出癌症,她兴高采烈地谈论着自己即将来临的死亡,就在几个月之后。我第一次见到威廉·特雷弗时,他告诉我他将葬在哪里。第二年夏天,我去了那个爱尔兰海滨小镇。那次旅行并非出于伤感。我仍然和当年在北京目不转睛地看着那个年轻女子谈论那些将比她更长久的裙子时没什么两样。我一直相信,在生与死之间,从存在到不复存在,有着那些更接近死亡的人所理解的秘密。我也想知道它们。
但知晓并非理解。医院里有一个时刻我反复回想:一次晨会上,要求每个人陈述当天一个可实现的目标,我无法坐下去,一个护士追着我跑过走廊。她是个表情严厉的女人,身材苗条,头发染成了白金色。“你必须明白,”她说,“自杀是自私的行为。”一个与我亲近的人说那是不负责任;另一个人说那是操控。“是的,我明白你的意思,”我对他们每个人都这样说。理解无法靠意志强行产生。没有理解,就不该谈论感受。人没有能力完全感受另一个人的感受——这是生活的现实,对所有人一视同仁,除非有人利用这一事实来做出评判。人从来不是因为知晓或理解而自杀,自杀总是源于情感。
—
在生活中,我们回避情节剧,无论作为观众,还是更迫切地,作为参与者。在其最初的含义中,情节剧是舞台上演说或哑剧的伴奏音乐。它的目的至今仍然是唤起情感,而非叙述情节或塑造人物。但情感如同货币,有其价值。人们喜欢认为自己在与他人的联系中能够控制自己的情感。“我为你感到难过”,“我为你高兴”,“我为你感到愤怒”,人们这样说;或者他们说,“你不配得到我的爱、同情、尊重或憎恨。”这些话反映了一种地位。那些有感受的人如果愿意,可以停止感受;如果他们的期望没有得到满足,他们就会这样做。
当我在军队时——有一段时间我陷入绝望——我觉得生命的唯一解决办法就是机枪的扳机。我没能扣动它——尽管这可能是记忆的谎言,是为了回避其他真相而做的修正——因为我知道,我的行为会毁掉两个我不太熟悉的人的前途,甚至可能包括他们的生命。那位监督射击训练的连长和指导员,都对我很好。他们不可能知道我脑中上演的那出情节剧。我能清楚地看到我在世人眼中的样子。我的眼镜在一次作战训练中被打碎了,所以我不得不向一个学化学的女兵借一副眼镜用于射击练习。她的右眼镜片度数和我的相似,但左眼镜片度数要深得多。在靶场,我会在左眼前蒙一块手帕,以免头晕目眩。“一个独眼女海盗,”我记得和朋友这样笑着说。
我第二次离开医院后,参加了一个临终关怀机构为期两天的志愿者培训——陪伴临终者,因为这是法律允许志愿者做的唯一任务。来了很多发言人:医生、护士、社工、办公室经理、一位精神疗愈师、一位牧师、资深志愿者、家属。我最喜欢的发言人是一位前芭蕾舞演员,他以一首歌开始演讲,歌词取自艾米莉·狄金森的一首诗;当他唱完时,他的粉色衬衫已被汗水浸透,听众们泪流满面。我最不喜欢的是负责志愿者项目的那个女人。她新婚燕尔,在培训开始前和休息期间,一直展示她婚礼和蜜月的幻灯片。“他帅不帅?”她问,坚持要得到全场的确认。她还指出了新郎的一个老朋友,那人在仪式结束前就喝醉了,切走并偷了一块她的婚礼蛋糕。她明确告诉那个男人要远离她的婚姻。
悲剧和喜剧都让我们体验到坚实的情感,这些情感是可以分享的。悲伤变得不那么难以忍受,笑声更加洪亮。情节剧则让我们保持警惕。我们是自己情节剧以及他人情节剧的局促不安的敌人。
—
2014年6月。就在我写下这些文字的今天,世界充斥着关于二十五年前**的图像和观点。一切都说得斩钉截铁。人们,尤其是那些从远处观看悲剧的人,谈论起来如此滔滔不绝。愤怒、悲伤、对一个充满矛盾、双方都有不可信赖的人物用人民的生命作赌注进行算计、甚至充满闹剧的历史事件的偶像化和理想化——这些情感都以一种类似于曼的傲慢被轻易表达出来。那些没有理解就发言的人,总能毫不费力地找到舞台中央。
早些时候读新闻时,一个我早已遗忘的随机记忆回到了脑海。那时我姐姐在医学院读书,和同学们一起去帮助绝食的学生。有一次探访回来,她给我带回一顶遮阳帽。帽子是用薄薄的白色细棉布做的,形状像维多利亚时代的软帽,被称为“简爱帽”,我一直想要一顶。之后,那顶帽子消失了。毫无疑问,是我的父亲处理掉了它,他在流血事件发生第二天曾去附近一家医院清点尸体。作为一件捐赠给抗议活动的物品,它可能会给我姐姐惹上麻烦。
情节剧就是那顶简爱帽。要想理解这段记忆,我必须穿越几十年的历史;我必须闯入他人的过去。然而,这将是徒劳的努力。我可以在所有层面上——国家的、家庭的、个人的——剖析悲剧和喜剧,但那顶简爱帽仍然难以捉摸。我永远无法解释为什么关于它的记忆让我潸然泪下。
那个脆弱的物件可以被转化为比它本身更多的东西——一个象征或一个隐喻;但那样它将变得远不如其本来面目。情节剧,固执地,拒绝这样的转化。
—
为情节剧辩护或反对它,就像为自杀辩护或反对它一样,都是在反对我自己。作为观众中的一员,我一直持怀疑态度。我也曾被情节剧占据。然而,正是这种经历让我无法摒弃情节剧。为了理解它,我提出这个假说:记忆即情节剧;情节剧保存记忆。
记忆是重新排列——重新收集——以创造叙事的瞬间集合。瞬间,由有形的空间界定,如同雕塑和绘画。但瞬间也是音乐的单个音符;没有一个会永远静止不动。在它们被时间席卷的那一刻——在那从空间到时间的转变中,记忆便是情节剧。
然而,情节剧存活的机会不大。在那一刻不够勇敢,我们错过了音乐,只能用阐释来取代它。如果我们确实捕捉到了音乐,我们又会后悔这一行为——与情节剧共存是困难的。时间带来了观众——外部的批评者和自我审查,它们擅长玷污、削弱甚至抹去情节剧。但是,时间,这个记忆的致命敌人,当记忆同意被剪辑和拼接成优化的存在时,又会以盟友的姿态出现。音乐变得不那么难以忍受,更加碎片化;剩下的是一份被篡改的乐谱。
最终,记忆有两种形式,都难免失真:作为情节剧和作为改编。人执着于后者,是为了前者不至于让自己的心智失事沉没。然而,剥离了情节剧,除了空虚忙碌的生活,人还剩下什么呢?
—
1940年9月18日,驶往加拿大的英国轮船“贝拿勒斯城号”遭到德国U型潜艇袭击。乘客中包括九十名儿童,其中七十七人丧生。这结束了英国政府战时将儿童疏散到海外的计划。不在船上因而幸免于难的是十一岁的爱娃·阿尔特曼,她大约在同一时间登上了另一艘驶往纽约的船。爱娃是洛特·茨威格的侄女。那时,茨威格夫妇——已被纳粹驱逐,从奥地利辗转英国、纽约,最终定居巴西——已在彼得罗波利斯安顿下来,他们将在那里生活,直到两年后自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