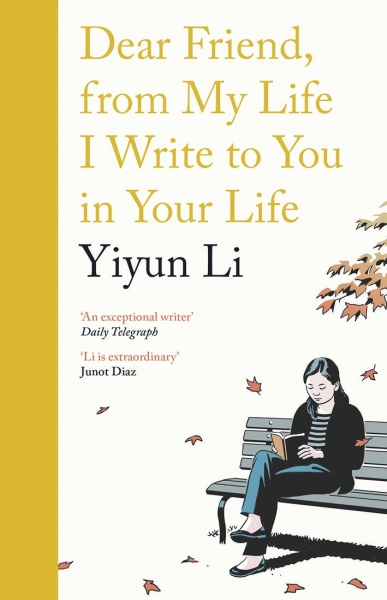为什么要写自传体作品?必定是相信某种自由。对高尔基而言,这种自由似乎来自于他能根据一个自己笃信的体系来评判世界:是非、善恶、未来与过去,都以明确无误的对比呈现出来。而对于既不评判他人(包括他父亲)也不评判自己的麦克加恩来说,自由又是什么呢?不过,自由,如同原创性一样,作为一种普遍的幻想才令人好奇。人们如何忍受自由的匮乏,比他们追求自由更让我感兴趣。此外,那些叫嚣自由的人,就像那些摆出原创姿态的人一样,也可能相当的可预测。
但对于那些希望通过写作来抹去自我的人来说:又何必写作呢?我当时正在写一部小说,写作过程与我急剧崩塌的生活交织在一起,以至于我开始把这本书——书中发生了一起半心半意策划的谋杀——视为我生活中许多美好事物的一个随意的谋杀者。但我太清楚了,这不过是在为我无法理清的困境找借口。当我放弃科学时,我曾盲目地相信,在写作中,我可以凭意志让自己成为一个无名之辈。有几年,我沉醉于这种状态,生活在那些不知道我存在的角色中间。但是,当一个人希望笔下的角色能够活下去,即使不是活得更好、更诚实、或更明智,至少是活得更丰满时,又怎能永远只做一个情感的依附者呢?刻薄地说,人写作是为了阻止自己感受过多;同样刻薄地说,人写作是为了更接近那个感受着的自我。
亨利酒吧里人头攒动。朋友和熟人互相打着招呼。酒杯从人们肩上传递。过了一会儿,大家都安顿下来后,人们走上台,朗读麦克加恩的回忆录,有些人照着书念,有些人则背诵了文本。朗读者一个接一个,然后,极其自然地,没有任何介绍,麦克加恩的声音响了起来:
再过一个星期,母亲回家了。她身体很好,心情愉快,直接回学校上班了。每天早上,我们跟着她走上煤渣小路,穿过小铁门,经过布雷迪家的房子和水池,经过老马洪兄弟住的房子,经过那幽深黑暗的采石场,穿过铁路桥,沿着马洪商店旁边的山坡向上走到学校,傍晚再循原路返回。我确信,正是从那些日子里,我形成了这样的信念:生命中最美好的部分,是平静地生活,没有惊天动地的大事发生,只有我们在一天中安稳地行走,变化难以察觉,而宝贵的生命本身就是一切。
我肯定是在场少数几个第一次听到那个声音的人之一。这段话,我在麦克加恩的回忆录里划了无数次重点,是一种只有最自信的梦想家才敢宣称的顿悟。我嫉妒麦克加恩吗?在那一刻,是的,因为我想相信他的话,但我知道自己做不到。我也可以假装领悟了这样的真理:我常常带着骗人的宁静滑过生活;我有信心将表象当作我的存在。然而,那种信心,正是取代了“我”的空虚。一旦“我”进入我的叙述,我的信心就崩溃了。一个人难道能够忍受自己所缺乏的东西吗——既没有“我”的在场,又无法靠近那些让“我”之缺席变得不可能的人们?
—
第二天,一位爱尔兰作家带我游览了乡村。我们开车经过一个爱尔兰共和军纪念碑,再往前走半英里,看到一对老夫妇在割泥炭——她说,天气好,他们今天会收获颇丰。在一座城堡酒店,我们参观了麦克加恩图书馆。一块金色的铭牌是由爱尔兰前总理伯蒂·埃亨题献的,但他的名字被污损了。有人解释说,这是因为人们对他导致爱尔兰经济崩溃的角色感到不满。这让我想起中学时的一位老师,她因为在共产主义理论课上不倦地宣讲而被人讨厌,有人把她的名字刻在了与校园相邻的圆明园一座古亭的柱子上,这起破坏行为还引来了警方调查。消息传开后,午休时我们都跑去参观那座亭子。每个抗议者的心中,都藏着一颗能幸灾乐祸的童稚之心。
我们开车去看麦克加恩的墓地,他和母亲葬在一座白色小教堂旁。在他和他母亲的墓碑后面有一道门,通向一条绿荫小径,小径尽头是一栋漂亮的房子,半掩在修剪整齐的树丛中。我好奇那是否是教堂的一部分,我的向导说她觉得不是。然后我想起来了。麦克加恩的母亲去世时,他父亲亲自为墓地画了规划图,但因为一个失误,堵住了多兰(Dolan)家的一条小路。多兰家是把这块地捐给教堂的,他们有权走自家的私密小径,而不是通过教众进出的大门。于是引发了法律问题;多兰家必须得到安抚。
我清晰地记得他们家一位老叔叔,查理·多兰,他在美国待过多年,喜欢钓鱼。夏天的大多数日子,他都会经过我们在科拉马洪的家,往返于加拉戴斯湖。每当他钓到一条大鱼,即使鱼尾拖在尘土里,鱼身笨拙地拍打着他的膝盖,他也会把鱼挂在自行车把手上……那是一个幼稚的世界。人们知道他的弱点……查理在路上每转个弯都会被人拦下。那条巨大的鱼引来惊叹和赞赏:能把这么个大家伙弄上岸,简直是个奇迹,而查理每次都乐于接受这种恭维。这种对认可和荣耀的需求,必定根植于人类的孤独。
认出这条路、这栋房子以及它背后的故事——这是我那次旅行中感觉最接近清晰的时刻。不是平静,而是实在感。别人生命中一个确凿无疑的事件,留下了明确无误的证据。麦克加恩的一生是在他的人民中度过的,他的书也是在他的人民中写就的。他笔下的人物,无论真实的还是虚构的,都不比他们的创造者更好或更坏,而这位创造者——再次不同于他许多才华横溢的同胞——从不浪费时间去追求原创性。“我成长地方的人民、语言和风景,就像我的呼吸一样,”麦克加恩在回忆录结尾写道。回到记忆中去,是再自然不过的事。在痛苦与感受之间重新划定界限,能带来解脱;也有喜悦。
我独自在北京走过的小路已经消失了。即使城市保持不变,我也已背离了那里的人民、语言和风景。对我而言,归乡只有在紧随其后的离别中才有意义。永久的归乡将是一种认命。与人为伴——这是否要求一个人与他人相处融洽,与自我和平共处?但一颗焦躁不安的心,除了离家远行之外,不知道任何通往平静的道路,而离家远行一次又一次地将人暴露在对依恋的终生恐惧之下,正如写作背叛了一个人蜷缩和躲藏的本能。人说的每个字,写的每个字,向他人和自己揭示的每个梦想、恐惧、希望和绝望——它们最终都像那些拒绝被塞回蛋壳的小鸡。
记忆是无人能免的情节剧
对斯蒂芬·茨威格与妻子洛特一同自杀一事,最冷酷的批评之一来自托马斯·曼。“他不可能因为悲伤而自杀,更不用说绝望了。他的遗书相当不充分。他说的重建生活如此困难,到底是什么意思?肯定跟女人有关,是不是有什么丑闻要曝光了?”
死亡,除非对于一个完全孤立的人,否则总是一个被公开的私人时刻。自杀,作为一个人能做出的最私人的决定之一,却常常被公众接管。那些表达强烈感受的人,误以为自己是故事的中心。围绕自杀的激烈情绪——愤怒、怜悯、不原谅,甚至谴责——要求着无人有权索取的东西:一个解释,以及评判这个解释的权威。
一个人求死的愿望,可能和求生的意志一样盲目和直觉,但后者从未受到质疑。自杀可能被斥为一出失控而进入情节剧(melodrama)领域的戏剧。如果悲剧让我们出于同情而哭泣,喜剧让我们出于欣赏而欢笑,那么情节剧则令人疏远和不安。当我们哭泣时,我们是在抗议中哭泣,怀疑自己被操纵了;当我们欢笑时,我们带着一种可疑的信念在笑——相信自己超越了它的荒谬。但这是对情节剧的误解。悲剧和喜剧需要观众参与,因此它们必须给予——分享自身以引出眼泪和笑声。情节剧却不是这样的策略家。它不满足任何人的期望,只满足其内在的情感需求。
我无意为自杀辩护。在我生命中的其他时期,我或许会这样做,但我已到了这样一个地步:为我的行为辩护和质疑它们,是同一个论证过程。我说的每一句话都受到我自己的审视,不仅是词语及其逻辑,还有我的动机。就像身体遭受自身免疫疾病的折磨一样,我的心智攻击着它自己创造的每一种感觉和想法;一个解剖自身的自我,几乎找不到安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