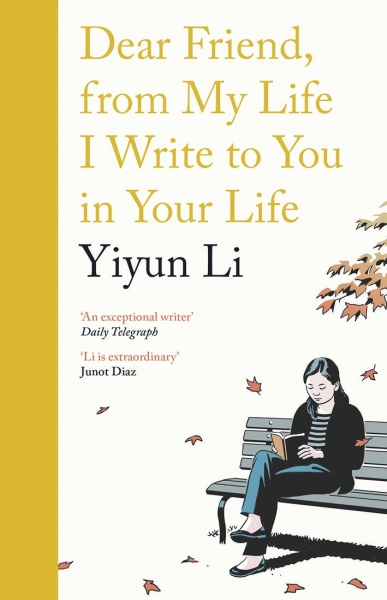迷宫般的小路连接着稀疏散落在田野间的房屋,小路像溪流一样蜿蜒交汇,最终汇入某条主路。这些狭窄的小路仍在使用中。在某些地方,生长在高高堤岸上的树篱是如此茂密,以至于树木在上方交织缠绕,形成一个顶棚,在夏季枝繁叶茂时,走在其中就像穿行在一条绿色的隧道里,被明亮的光点刺穿……
我住处周围有很多这样的小路,多年来,在某些罕见的时刻,当我在这些小路中行走时,我体验到一种非凡的安全感,一种深深的平和,在那之中我感觉自己可以永远活下去。
我划下了“一种非凡的安全感,一种深深的平和”这几个字,然后做了一件暴力的事:我把笔扔进了水里。它无声地沉没了,我立刻后悔了这个举动。我一生中从未因无法控制的情绪而伤害或毁坏过一件物品:没有摔过门,没有砸碎过盘子或杯子,没有把一张纸撕成碎片。我一定是从我父亲那里继承了这种对物品的尊重,他是个囤积者,尽管我一直抗拒对任何物品或任何地方产生依恋。那时我希望,现在也希望,我从未对世上的任何人产生过依恋。那样我会全然友善。我不会做任何毁灭性的事。我永远不必问那个问题——我何时才能配得上你?——因为通过废除“你”,那个“我”的反面,我也能将那个麻烦的“我”从我的叙述中抹去。
我在河边待到天色太暗无法阅读。麦克加恩在他的回忆录中重新揭开的伤口,并非那种可以愈合、遗忘或作为历经苦难的荣誉勋章佩戴的伤口;通过将它们(平实地而非血淋淋地)展露出来,他似乎承认,他怀念那些从他生命中被夺走的美好事物,并希望它们回来。这种渴望中没有贪婪——贪婪源于匮乏以及不择手段摆脱匮乏的欲望。他安于这种渴望。也许这就是为什么这本回忆录对我来说总是难以卒读。如果我的生活中缺少了什么——确实有,就像每个人一样——我已经下定决心永远不去渴望它们。这一定也是一种贪婪;什么都不想要和想要一切一样极端。
他回忆录中描述的小路——那里鲜花从未停止绽放,他和兄弟姐妹以及母亲日复一日地一同行走,直到疾病和死亡将他们打断——与我在北京曾熟悉的小径并无太大不同。花园路是一条两旁有水沟的柏油路,下雨时会泛滥。沿途没有花园,只有野葡萄、苍耳丛和一些我不知其名、只知其随季节变化的野草。只要孩子不乱跑就很安全,有一次,我父亲外出参加核试验时,我姐姐,那时五岁半,走了四十五分钟到花园路与一条更大街道的交汇处去买菜。我上小学的路环绕着我们的公寓楼,每扇窗户后面都有某个大人热衷于抓小孩的坏行为;穿过一片夏天我们捉蚱蜢的空地;经过一个屋顶简陋的户外厕所——雨天泥泞,晴天苍蝇滋生——它既服务于学校,也服务于附近的一个人民公社;还有一段最危险的路段——在任何人的视线之外,不超过一百米长——在厕所和学校之间。一年级时的一个冬日下午,我和我最好的朋友在那里被一个持刀男子拦住,但我们得以逃脱,一路尖叫着跑回学校提醒老师。四年级时,当我们的友谊已不再牢固到可以一起走回家时,我的朋友被另一个持刀男子抓住,带到了厕所后面,这件不幸的事被议论纷纷,但伤害无法挽回,所以最终什么也没做。
一定有很多次,在那些小路上,我身边有人陪伴。在我朋友和我疏远之前,我们在上下学的路上发明了各种游戏。有一次,我和姐姐为了省公交车费,走完了花园路全程去看一场电影,那是一次学校活动。我们提前一小时出发,每隔十分钟左右,当我们的同学在经过的公交车上向我们喊叫时,我们就向他们挥手。有一次,我的外祖父——和我家住在一起的母亲的父亲——带我去了花园路以外的一个区邮局。他带我进行了一次盛大参观,包括一个柜台,在那里,用旧枕套包裹的包裹被检查,然后由一位穿着绿色制服的老妇人重新缝合。他还写了一条信息,在一张带绿色格子的卡片上,演示如何发送电报。“一切安好勿念,”上面写着,然后被递给窗格后的电报员,几分钟后一张收据被拿回来,承诺电报将于当晚送达。它被发给了外祖父一位二十年未联系的侄女。
这些与他人共享的时刻——书写它们是为了重温感情,但我写作却是为了将那些感情抛在身后。那些独自度过的时刻才是更受偏爱的叙述:我独自一人走路时很快乐。厕所后面潜伏着男人,或者有人一手暴露自己一手骑着自行车,都无关紧要;大一点的男孩等着拿石头伏击我;我姐姐班上一个刻薄的女孩跟着我,每天轮换着一长串侮辱性的绰号(肉球是一个,大头鲢是另一个)。这些时刻没有被遗忘,因为它们构成了孤独的背景,而孤独是一种强烈满足的体验。我记得,我们公寓楼旁边有一个幼儿园,周围有一堵砖墙,我会在墙边绕很长时间,戳砖块的中心,坚信假以时日,每块砖上都会留下我手指留下的凹痕,形状相同,高度一致。
固执(Willfulness)是一种奇怪的乐观主义者。它把不可避免变成值得渴望的。如果孤独是不可避免的,我愿意相信孤独就是我一直渴望的,因为它本身就是幸福。这一定是一种误解——尽管我一直不愿放弃——认为一个人的生活可以被活成一系列孤立的时刻。其间,与他人共度的时间,是为了他们消失做准备的时间。至于存在一种相反的视角,我只能从理论上理解。时间线也是一个人陷入孤立状态的重复。消失的不是他人,而是人自己从他人身边消失。
固执也是一个悲观主义者。它把不想要的变成不可避免的。我所熟知的不快乐——我母亲的尖利,我父亲的沉默,我姐姐的苦涩——都被当作天气或国家政治一样去忍受。我们是否曾问过自己:我们为什么如此孤独,如此骄傲,如此执着于完善我们的伪装?我们很好地保守着我们的秘密,对世界保密,也对自己保密,并且出于宿命论,我们培养了坚忍。多年来,我拒绝看到我们对我母亲行为的毫不犹豫的顺从,甚至在她在我结婚那天宣布,我留给她的唯一希望就是我的离婚时,也是如此。这是一个人会反复对自己和他人当作笑话来讲的时刻之一,伴随着另一个故事:在爱荷华州约翰逊县,为我们在美国国旗和爱荷华州州旗前、由两位朋友作证的简短仪式上主持婚礼的那位法官,后来与助理地区检察官有染,在一个鲜有丑闻的地方成了一桩丑闻。笑声,无论多么不充分,都能将人隔绝起来。
—
我最早的一些文学教育来自一套带插图的高尔基(Maxim Gorky)自传。这三本手掌大小的书——《童年》、《在人间》、《我的大学》——经过删节并配有生动的墨水画,被称为“小人书”,尽管它们并非写给儿童的。(这种文学形式曾让沈从文,我最喜欢的中国作家之一,感叹共产主义中国文学的失落——即使不识字的人也能翻阅它们,就像我在学会任何汉字之前就开始阅读高尔基的自传一样。)然而,作为一个孩子,我从这三本书中获得了无尽的乐趣——它们是我自己的财产,而我拥有的东西很少。没有一页是沉闷的:高尔基的外祖父殴打他的外祖母,他的继父踢打他的母亲,他的舅舅们说服一个心地善良的年轻人把一个沉重的十字架背到墓地,然后毫无悔意地看着他被压死,高尔基当学徒时被打。死亡每隔几页就会发生:他的父亲、他的弟弟、他的母亲、一个常哼唱忧郁曲调的患肺痨的年轻人、朋友、邻居和陌生人。书中的信息——苦难、不平等、高尔基的政治觉醒——所有这些我都忽略了。让我觉得有趣的是形形色色的人物:拾荒者、富有的亲戚、水手、市民、牧师、圣像画家、店主、码头工人、寡妇、妓女、乞丐、一个独臂男人、一个盲人、一个为诗歌之美而哭泣的厨师、一个借给高尔基书的美丽女人、一个哀悼被雇工毒死的猪的专横面包店老板。(这是对俄罗斯文学多么奇怪的入门方式。从高尔基开始,感觉就像爬上了一座平房的屋顶,却没意识到附近就躺着中国的长城。)
现在重读这些自传,我仍然能认出这些书的魅力所在。高尔基经历了一段足以致残和击败他人的生活,但每次冒险后,他总是站在舞台中央,变得更高大、更英勇、更有魅力。一出戏剧和下一出戏剧之间没有时间可以浪费;事实上,戏剧之间根本没有生活可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