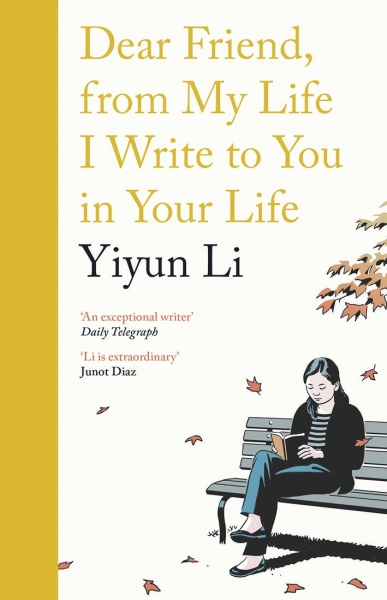—
这次旅行是为了参加一个庆祝爱尔兰作家约翰·麦克加恩(John McGahern)的文学节。收到邀请时,除了钦佩之外,我实在谈不上有多少关联,但我确实想去看看香农河(River Shannon)以及利特里姆郡和罗斯康芒郡(Roscommon)的乡间小路。去看一位自传体作家的生活背景,就是短暂地把握另一个人的现实。
我不是一个自传体作家——没有一个坚实且可解释的自我,人是无法成为自传体作家的——我带着同样的好奇心阅读所有自传体作家的作品。什么样的生活允许一个人有权将自己作为书写的主题?
虽然我以前读过麦克加恩的回忆录,并且知道它不会提供答案,但我还是带上了它去旅行。痛苦的童年,年幼丧母,在暴力且反复无常的父亲手下长大,他被流放爱尔兰又重返故土——所有这一切他都平实地写出,毫不炫耀许多同胞作家那样的文学腹语术般的技巧。没有谁的脆弱比另一个人更具毁灭性,没有谁的快乐更值得拥有。发生在麦克加恩身上的一切,不过是生活本身,发生在我们所有人身上的生活。
比起新的痛苦,已经承受过的痛苦更难忍受:它提醒着你,你离过去的自己并不遥远。为什么要写作来揭开旧伤疤?为什么要重温一部回忆录,当那本身也是一种放纵。
—
在英语中,我讨厌使用的一个词是“我”(I)。这是一个充满戏剧性的词。在中文里,一种语法不那么严格的语言,人可以构建一个省略主语代词的句子,跳过那个令人尴尬的“我”,或者用“我们”来代替它。活着并非什么独创的事业。
当然,每个时代都有远见卓识者、革命家和怪人,但他们,要么意识到——要么更可预测地,为了——自己的形象而活,往往显得乏味。剥离了观众,独创性会远不如现在这样自得。
忍受缺乏独创性:即使是我们中最没有野心的人,也必须发明某种方式来相信自己是独特的、不可替代的。人不禁会想,这种愿望,虽然既卑微又自负,却是人类与生俱来的,是否正是它赋予了使用“我”的许可。然而,在住院后的几个月里,我试图向周围的人解释,任何人都可以,也应该被替代。当这个“我”对自己都意义甚微时,它对你又意味着什么呢?
**事件后,我们大学的入学年级被送到军队待了一年,以防未来再发生不服从事件。在军队里,带着年轻人的自负,我把自己表现得与众不同:被命令写宣传材料时,我提交了拐弯抹角的颠覆性诗歌;对军官发表巧妙无礼的评论;抓住一切机会削弱我们班长的权威。挑战任何政治权威,以一种正义的方式将自己置于危险之中,用我的言语将这个自我与周围的人区分开来——这些,在十八岁时,是我通往真正渴望之物的捷径:确认生活,这惨淡而不公的生活,本不值得活。
离开军队前,班长给我写了信(互相写告别赠言是当时的传统):“有些人很平凡,有些人则不然。与后者相处一天留下的记忆,比与前者共度数年还要多。作为一个平凡的人,能与你共度一年,我视之为我的幸运。”
她在一个军人家庭长大,对任何上级都毕恭毕敬,真心相信军队赋予她的权力,信任共产主义的教导(我是如何通过坚持谈论**事件让她痛苦和愤怒的)。
这赠言并无恶意,却让我羞愧难当。我一直很感激她让我看到,一个人在努力用个性给世界留下印象时,可以多么乏味。幸运的是,我的无聊是以如此温和的方式被揭示出来的。如果她看穿了我,并且是出于讽刺而写,我可能会为自己的愚蠢而辩护。但她太年轻,没有意识到她比我当时扮演的那个装腔作势者更真实,而我则不够老练,感觉不到内疚。一个人,通过病态的漫不经心来否定自我,可以轻易地摧毁另一个人的信念。
—
在我第二次住院后的几个月里,我有个室友,她有着我见过最蓝的眼睛。她问我,她是应该去另一家机构,还是留在这里。我不明白她的问题,她换了种说法:她应该先治好她的精神障碍再去戒毒所,还是反过来?我没有专业意见,但冒险说也许戒掉毒品不是坏事。“你不懂,”她说,并解释说她会吸毒直到死去。
我不知道还能说什么,于是就听着。她不停地说——关于她的童年;纽约市的地铁;和她一起长大的朋友,现在没一个承认她的存在;她的父亲和兄弟们,他们拒绝借钱给她;让她失望的中途之家。很快,我不得不找借口离开房间。她太执着地要求一个答案。我很难过失去了那份隐秘空间,哪怕只是半掩门后的有限空间。“你那个室友,”好几个女人对我说,一边打量着她破烂的纸病号服和她在走廊里走动时浑然不觉的半裸状态,我们都坐在走廊的沙发或椅子上,按照被鼓励的那样进行社交。
在和后来搬进来的新室友的一次谈话中,我用一种我听别人用过的严厉语气说了些什么。“你不能那样说她;她和你我一样;她病了,”我的新室友说,这让我惊呆了。我从未认为自己是“病了”,而是“搁浅了”。
塞内卡(Seneca)在谈到与人相处时自己的“脆弱”时写道:“他们中没有一个人不会让某种恶习显得诱人。”(我喜欢塞内卡和他的门徒蒙田(Montaigne)。他们的智慧和自信如此紧密相连,让人在钦佩他们的同时,也有一种想取笑他们的冲动。)不过,如果我把“恶习”换成“语言”,它就描述了一种我深有体会的经历。我很容易受到他人说话方式的影响——他们的用词、语调和怪癖。
在军队里,一本模糊影印的《飘》(Gone with the Wind)在我的同伴中流传。我排里超过一半的女孩——她们的个性从害羞到健谈再到刻薄,不一而足——都声称在斯佳丽·奥哈拉(Scarlett O’Hara)身上看到了自己。有些女孩太有趣,有些则太无聊,不可能是斯佳丽。这种集体渴望必定是自我塑造的一部分。这个过程几乎没有独创性;但即便如此,这样做是多么勇敢的一件事。
我没有在斯佳丽·奥哈拉身上看到自己;也没有在安娜·卡列尼娜(Anna Karenina)、苔丝(Tess Durbeyfield)或简·爱(Jane Eyre)身上看到自己;我也没有在让-克里斯朵夫(Jean-Christophe)、尼克·亚当斯(Nick Adams)、保尔·莫雷尔(Paul Morel)或那位与海搏斗的老人身上寻找自己。将自己读入别人的故事,与我阅读的方式和原因恰恰相反。阅读,是与那些不像你周围人一样会注意到你存在的人相处。
军队里有个女孩曾几次从食堂偷红薯或馒头给我。这个举动,我不知如何拒绝,让我充满了冰冷的怨恨。像这样被特别对待,意味着人必须承认给予者赋予自己的地位;比受人恩惠更糟的是,为人不想要的东西而受惠。在医院里,三个女人玩起了把橙子从餐厅偷运到我抽屉里的游戏。我像一个正常的、心智健全的人那样吃橙子这件事,和我在朋友探视时要来的托尔斯泰小说和蒙田散文集一样,让她们觉得好笑。我接受了这些违禁水果,也欢迎她们的玩笑,尽管我引用了格雷厄姆·格林(Graham Greene)笔下的一个人物——一位天主教神父——的话,说她们可以嘲笑我,但不能嘲笑我的书。她们中的一个将被转到戒毒所;第二个,在其他治疗失败后,将开始接受电休克疗法(ECT);第三个在我离开的前一天被置于自杀监护之下。人必须和那些处境与自己相差无几的人一起自嘲。
医院让我想起了军队。特定环境的词汇构成了一个棱镜,透过它,外面的世界看起来光怪陆离;笑话是共享财产;人的思想变成一个无边无际的迷宫,是对物理空间匮乏的一种补偿;被所有人看见是隐藏最容易的方式;说话,并且说别人的语言,是沉默的最佳模式。大千世界,又能有多大不同呢?
—
在爱尔兰的第一个晚上,我在香农河边散步。除了一位孤独的渔夫和一艘系泊的小船,几乎没有人间烟火的痕迹。水鸟、芦苇、降临的黄昏和异国的天空,是否足以证明生命值得活下去?河对岸是丘陵起伏的草地,再远处,就是麦克加恩笔下的小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