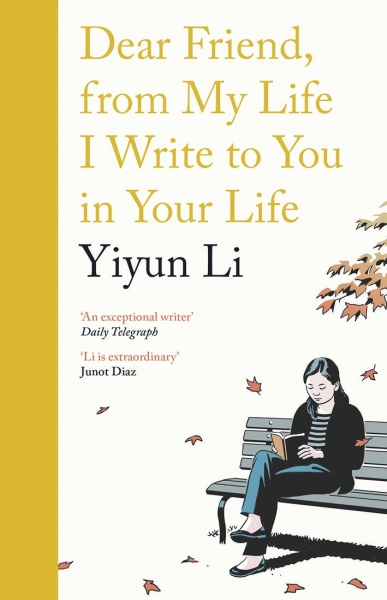这个人物离开了北京,并不改变那里有一个属于她的空间的事实。她可以拒绝占据它,但它不能被别人填补。颐和园湖上的那艘她本可以租一个下午的划艇,将闲置着,船桨从桨架上脱落。她当地的邮递员,绿色帆布邮包挂在他的自行车横梁上,会用一条腿撑在路边整理邮件,尽管她不会在那里和他聊天。在一次同学聚会上,一张旧的一寸校照会被扫描放大,因为她不愿参加,也不愿寄一张近照来赦免她的缺席。
“你为什么不承认你可能就是那个人——”我能听到朋友质问我,“——事实上,你就是那个人?”答案,我想,是我不想要一个自我,在一旁观察自身并思考替代选项。人在小说中有失去隐私的风险,而反自传性则减少了这种危险。我不可能是我笔下的任何一个人物;她们拥有我所没有的替代选项。然而我并不介意与她们一同体验失去替代选项的过程。人在借来的人生中活得更有感觉。
“难道你不担心在这些散文中失去你的隐私吗?”我又听到朋友质问,但事实是,我所执着的隐私与他人几乎无关。有一次我看到一个学龄前儿童,我儿子的玩伴,展示了那种技巧。他被一个小小的灾难所困扰,没有抱怨也没有哭泣,他让自己的身体静止下来;他灰蓝色的眼睛变得毫无生气。我从未如此近距离地目睹过一个心智通过意志关闭自身。只花了几秒钟——时间不长,却是一个间隙——他的眼睛从恐慌变成呆滞,在那背后我能感觉到一种对缺席的不屈决心。实践那种消失术的人会形成一种信念——其实是幻觉——即人可以不被观察地存在。
—
人无法成为自己生活的娴熟作家;也无法成为那个故事的敏锐读者。没有小说家的工具来创造情节、掌控节奏,以上帝视角叙述或抛弃不方便的观点,调整时间的线性、拼接联系较少的瞬间,我们当中最有趣的人,我常常怀疑,比小说中最扁平的人物还要扁平。我们不仅没有任何替代选项,我们还不相信它们的存在。“事情必须如此”——这种不容置疑的信念常常是我们决策的基础,包括最冲动或最具灾难性的决策。确信一件事比不确定一百件事更容易;存在一个“是”比存在许多“可能是”更容易。
“你余生的每一天都应该非常小心,”一位医生告诉我。“为什么?”我问。(我忍不住想这句台词有多糟糕——余生的每一天。如此绝对。在小说里,一个角色绝不该被允许说出这句话。)“事情可能会悄悄找上你,”医生说,“等你意识到的时候,你脚下的坚实地面已经消失了。”“那我该怎么办?”我问。医生回答说我永远不应该停药。我理解为:我无能为力。
事情必须如此吗?我常常想。
这些散文是在复杂的情感和矛盾的动机下开始写的。我想反驳自杀,也想为之辩护,也就是说,我想保留自杀这个选项,同时又希望它被永远从我身边夺走。写这本书到现在大约花了两年时间,和导致它的那段时间一样长:一年陷入最深的绝望,一年被那绝望所禁锢。那份绝望,可以用几个笼统的词来概括——自杀未遂和住院治疗——是如此绝对,以至于它几乎不能照亮任何东西。一个明智的目标是避免它。
在过去的几年里,我学到了一点小小的失误就可能导致崩溃,在几小时内,有时是几分钟内。发生这种情况时,缺少的并非智慧或精神力量。承认这不是失败,并不能减轻悲伤。困难的时刻并非放弃之时——放弃,实际上带来了确定性;还有解脱与平静——而是事后,当同样的模式再次重复时。为什么?人一次又一次地追问,但追问就是面对不可改变之物。人只能接受,细胞信号的运作比逻辑更快,也更不受约束。在那个男孩眼睛变暗淡之前的几秒钟:那清晰与混乱之间的间隙,正是心智凭借自我保护的本能与自身搏斗的地方。那个间隙是我的隐私。写小说一直是我保护它的方式,尽管并不总是有效。从那个间隙出发写作——这本书——是一次与无法改变之物建立休战协定的实验。
许多草稿都是在事情开始变得难以忍受时写的。写一个句子总比什么都不写好;从危险的沉思中夺回一个小时就是一个小时的收获;将一个想法的线索追随到底,比让许多想法纠缠不清要好。从某种意义上说,写作变成了在警示信号出现之前就侦测到它的努力。有些时候,我的文字听起来像是在反对希望和幸福,反对他人和自己,但任何依恋,即使是对最谬误的想法的依恋,在感觉不到坚实时,也是一个锚。
—
蒙田散文中的段落都标有字母(A、B或C),以表明他创作它们的不同时间点——他常常回到同一篇散文上继续修改。没有这些标记,读者“可能会认为他前后矛盾得不负责任”,他的译者唐纳德·弗雷姆解释说,因为这些散文“旨在记录变化”。
为我的散文做类似的标记未免冒昧,尽管写这些文章的两年充满了模糊不定。句子和段落是在不同情况下写了又改,论点被重新构建,思想被修正;这些散文大多花了一年或更长时间才写成。连贯性和一致性并非我一直追求的目标。
没有任何梯子可以爬出任何世界;每个世界都是无边的——我的朋友艾米·利奇写道。我不再寻求梯子。相反,我希望有一天能够对自己说:亲爱的朋友,我们已经熬过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