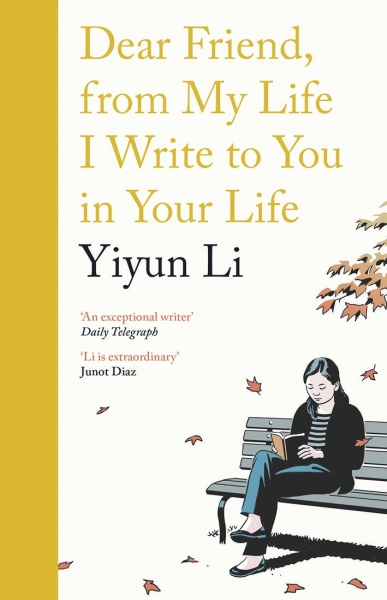—
我没有忘记任何一个进入我生活的人,也许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我别无选择,只能像个隐士一样生活。我随身携带的那些人,不仅耗尽了他们自己的生命配额,也耗尽了我的。铭记,是隐士欠世界的债。
我和父亲曾经在我们院子里种豇豆,它们的卷须每天都在竹篱笆上爬得更高。夏天结束时,邻里的一位老太太总会在我们准备收获前几天把豆角掐走。第一次抓到她偷东西时我很生气,但父母说我不应该生气,因为我还是婴儿时她给我缝过一件棉袄。年复一年,那位老太太收割我们的豆角,每次父母都提醒我要为那件棉袄心存感激。后来她不再来了:她去世了,我再也没有理由去感受任何东西了。
有一次,外公在花园路散步时感到不适,得到了一位年轻士兵的帮助。他成了这个家庭的一份子,一个周末来访的认养的孙子。外公去世后,他带着新婚妻子来北京,和我们住在一起。我和姐姐都很喜欢他的新娘,她漂亮又温和。他们离开的前一天,他不得不在排队买火车票的地方过夜,早上他还没回来时,我撞见她在哭。他只是耽搁了,他们高高兴兴地结伴回家了。他们离开后,我发现了一个写字本,最上面一页被撕掉了,但我能看到曾经写下的痕迹:那是新娘焦虑的独白,问自己他的缺席意味着什么,为什么她被留在这空虚之中,以及这段婚姻当初是如何开始的。多年后,我在一本鲍恩的小说里划下了一段关于一个人物“着力甚深”的铅笔的文字,那铅笔留下了痕迹,让她的女儿得以解读。
—
“这是关于什么的?”当我正在网上观看北京阅兵时,我的大儿子问我。“庆祝二战结束七十周年,”我说。“我的曾外公死于那场战争,”我说,并立刻后悔自己听起来像那些轻易兜售继承来的家族剧目的出租车司机。“那是哪一年?”儿子问。“一九三八年,”我说。讨论就此结束。我不想描述那个男人的死状,就像它被描述给我听的那样。他,一个小镇上的布商,被迫为日军做苦力;他跛脚,跟不上其他劳工,于是被草草杀害,躯干被军刀劈开。(没有见过那个人,也没有目睹他的死亡,我年轻时却花了很多时间思考他。他的跛脚让我想起了我跛脚的表哥。)
“我不明白为什么特雷弗还在写‘北爱尔兰问题’,”爱尔兰曾有人对我说。“那些都是老故事了,爱尔兰已经向前看了。”“我可以告诉你,你的书伤害了我的感情,”一位读者,后来发现和我是在同一个大院里长大的,在一次书店朗读会上宣称,“你为什么要写中国的历史?为什么不能让我为自己是中国人感到骄傲?”但是,残忍与善良并非老故事,永远也不会是。
小学时,一个女孩的父亲突然去世了。第二天早上,轮到我值日打扫,我扫着校园我这边,看着她扫另一边。(我当时并未想到去质疑为什么值日打扫比父亲的去世更重要,或者为什么我没有主动帮她。)她在哭泣,眼泪掉进一堆树叶里。我想对她说点什么,却不知道说什么,心里一直被一个阴郁的担忧困扰着。她是我年级里另一个胖女孩;现在连最坏的男孩也会放过她了,而我将是唯一被取笑的胖女孩。我没有意识到自己担忧的轻浮。尽管我记得我随后看着她时的想法:至少她有理由哭,人们会理解的。
“我跟你说过孙老师去世了吗?”母亲最近问我。“没人会想他的,”她说,“卧病十年,当时也没人心疼他。”她的话里没有恶意。那个去世的人,我五年级的数学老师,曾以在课堂上打男生、把手不规矩地放在女生身上而闻名。没有家长、老师或学校领导干预过。他是个暴力的人,能对任何冒犯他的人为所欲为。“世上少了个恶人,”母亲说。她的话让我想起了一件我几乎成功忘记的事。这位老师过去常常在课前在黑板上写题,让我去解,而他则在过道间踱步,不慌不忙地挑选要拧的耳朵。等我解完题,他也已经折磨了一两个男孩了,便会回到黑板前。“漂亮,”他会评论道。尽管他那沾满烟渍的手指和虐待狂笑容背后烟民的酸臭气息,我并未因他的认可而感到排斥。然后他会转过身,朝某人扔出一截粉笔——我们都知道这会发生。“你,”老师会说,“对,我跟你说话呢,”他会盯着那个被粉笔标记的男孩,“你永远不会懂得头脑之美。”说完这些话,我就被遣回座位了。
残忍与善良,重新审视时,并非它们表面看起来的样子。
去年夏天我去看望父母,在我就长大的那套公寓里,我看到一张我五岁生日时拍的照片,旁边是我母亲十六岁时拍的照片。还有其他家人的照片,但这两张,比其余的早了几十年,照片的主角被定格在年轻得多的瞬间,却被显眼地展示着。我对着这个纯真的圣坛畏缩了一下,那时照片里的两个女孩都还没造成太多伤害。母亲有着梦幻般的笑容,以一种浪漫迷人的方式美丽着;我则按照摄影师的要求微笑着,不显早熟,但很尽责。如果我不认识她们俩呢?我会更仔细地看她们,我的好奇心与我对任何陌生人的好奇心并无不同。不比别人好,也不比别人坏,这两个人,也是命运的傻瓜。
“你可能没有你想象的那么困惑,”特雷弗在一封信中写道。“故事是一种希望,它们常常顺从地回答问题。”
—
“你是谁?”今年春天我见到特雷弗时他问我。“没关系,”我说,“我只是来看你的。”“啊,我们在波士顿见过,”一分钟后他说。“是的,我们在波士顿见过,”我说,但我本也可以说:我们是孤独的旅人,曾在故事的土地上萍水相逢。
后记
关于做一个扁平人物,及创造替代选项
回答那个问题的方式有很多种。不是每个人都会问,但如果允许真正的好奇心——一种真诚理解的愿望——取代客套,有些人是会问的。我也会。事实上,我仍然在问自己:是什么让你觉得自杀是一个合适的,甚至是唯一的选择?
这个人或那个人在这个或那个时刻提出了各种假说:基因,缺乏精神力量或成熟,自私,细胞信号随机出错。也有更实际的解释。我曾经雄心勃勃——或者说贪婪——想要同时扮演好母亲和作家的角色,还要做一份全职工作。将近十年,我都在午夜到凌晨四点之间写作。
如果早知会留下这样的损害,我还会那样剥夺自己如此基本的需求吗?我想会的。我看不出还有其他方式来处理我想做的事情。伊丽莎白·鲍恩在她关于写小说的笔记中强调了替代选项:
正是替代选项的明显存在赋予了行动趣味。因此,在每个角色行动时,必须能感受到替代选项的相互作用和牵引力……到小说结尾时,角色起初拥有的众多替代选项,已被削减至无……“扁平”人物没有替代选项。
—
我愿意相信,生活中的替代选项和小说中一样多;那些未选择的路,一旦曾被权衡过,就和已选道路那不可逆转的方向一样,定义着一个人。“如果你没有离开中国会怎样?”一位朋友问;“如果你没有落在爱荷华市,或者如果你继续做科学家,又会怎样?”我能提供的不是替代选项,只是否定式回答。我不会选择英语作为我的自然语言;我不会知道人可以去学校学写作;我不会成为一名作家。
但是我会变成什么样子呢?当这位朋友问及一个角色类似的问题——如果她没有移民,她的生活会怎样?——我毫不费力地就能在北京看到她:她每天上班过街要走的天桥;她终于掌握了视而不见的艺术后不再给钱的残疾乞丐;她和出租车司机半心半意地搭话,而司机像北京所有出租车司机一样,乐于嘲笑政府;她钥匙链上的一大串钥匙——一把开她公寓门旁木箱的锁,里面是每天给孩子送的新鲜牛奶(她的孩子长大后不会知道每天傍晚去牛奶站的乐趣);另一把开信箱(多年前整栋楼的邮件都塞进同一个绿色信箱里,这是一种诱惑,因为她总喜欢看谁是收到信件的幸运儿);公寓、办公室、汽车和安全门的钥匙——钥匙,太多了,代表着特权和责任。在我的中国生活中,我只有一把难忘的钥匙——那种在美国任何古董店都能找到的——青铜的,有我整个手掌那么长,我用蓝色尼龙绳把它挂在脖子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