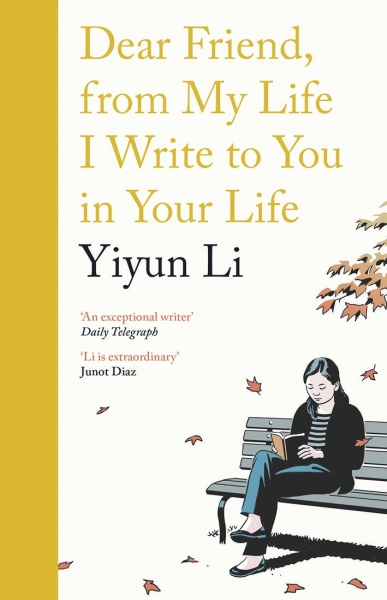—
在访谈中,特雷弗说他写作是“出于好奇和困惑”。没有道理可言的东西才是重要的。是什么促使我舅舅写那封信?是着迷还是执念,让母亲总是以某人自杀的消息开启谈话?我冷淡地回应,仿佛事不关己,这是否自私?特雷弗为什么同意见我?为什么与特雷弗的午餐不仅仅是一次礼节性的会面,表达和接受了恰当的感激?“趁早来访,”他说,并提到他想让我看看的花园。在地铁站,扶梯上我身后的那个男人转过身来看简(她后来加入了我们)和特雷弗。他们一直挥手,直到我消失在视线之外。“告别,是吧?”那个男人说,我说确实是告别。未来几年还会有更多的告别,在埃克塞特火车站;在伦敦维多利亚车站;在德文郡一家餐厅阳光明媚的花园里。每一次告别,那个未问出口的问题总在那里:我还会再见到你吗?
只有充分准备好面对人们的缺席,才能对他们的在场感到自在。一个隐士,我开始理解,并非一个无法与他人建立联系或认为联系毫无意义的人,而是那种觉得自己必须远离人群的人,因为连接是一种折磨,或者更糟,是一种瘾。直到遇见特雷弗,我才想到去问:我还会再见到你吗?此前阻止我问这个问题的是:也许我不会再见到你了,如果这样,那么暂别即是永别。
—
“写完书后,你还会想起你的人物吗?”下一次拜访特雷弗时,在他开车送我从火车站去他家的路上,我问他。
“会的,”他说。“我不会重读它们,但我记得那些人物。有时我仍然为他们感到悲伤。你呢?”
“我也记得你的人物,为他们感到悲伤,”我说。
他看着我。“不,我的意思是,你会想起你自己的人物吗?你会为他们感到悲伤吗?”
我知道他问的是这个,但承认那些已经离开的人物仍然将我挟持,似乎很傻。
那已近春天——二月,虽然温暖晴朗——花园里的花已经绽放。午餐时,特雷弗让我坐在桌子靠窗的一侧,这样我可以看到外面。他坐下,又站起来,轻轻地拉了一下窗帘。“这样,”他向我解释,“你可以欣赏花园,又不会被阳光刺到眼睛。”
有时人们问我,如果想开始阅读威廉·特雷弗,应该读什么。谈论特雷弗的作品,也就是在谈论记忆——它们是用英语写成的,我知道它们从何开始。有《钢琴调音师的妻子们》:看到人物们挣扎于他们自己都不知道自己有能力犯下的残忍,那种痛苦并不会因熟悉而减轻。有《读屠格涅夫》:有一次在宾夕法尼亚,一位诗人在月光下的乡村开车带我,她告诉我她一直在写一首名为《读屠格涅夫》的诗,作为致敬。有《亚历山德拉之夜》,这本书经常伴随我旅行。有一次去纽约,我在地铁上看到一个中年妇女和一个孩子,女孩不超过十三岁,头靠在年长女人的肩上,后者抚摸着孩子的内腿。我分辨不出她们是母女还是一对恋人。这种未知,和两种可能性本身一样,都让我不安。后来在酒店里,我开始写一部中篇小说的开头几段。叙述者是一位独自生活在北京的中年妇女,她用特雷弗小说中那位爱尔兰外省小镇老单身汉叙述者同样的开篇句讲述她的故事。一个孤立生活的人说话,并非出于独处,而是出于孤独;特雷弗的叙述者决定向世界倾诉,使得这个女人也可能这样做。
特雷弗的书——《他人的世界》、《命运的傻瓜》、《伊丽莎白独身》、《露西·高尔特的故事》,等等等等——为我提供了一个避风港。但即使是解释这一点,也是一种侵扰:有特雷弗的隐私,他建造了那个空间;也有我的隐私——在写作和生活中,人常常被未分享的记忆所支撑。
—
特雷弗最后一次公开朗读之后——我为此飞到了英国——他告诉简和我,签售队伍末尾有位老人。那人来不是为了特雷弗的签名,而是为了感谢他。他的妻子曾深爱特雷弗的故事,当她病得太重时,他就读给她听。她去世时,他正在读给她听的,就是一个特雷弗的故事。
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将体会到通过一位垂死读者的眼睛来理解自己作品的意义。一位来自加拿大的女士写信给我,指出了她读到的一句话所在的章节和页码,她说她永远不想失去那句话。她的脑部因放疗受损,她写道;她无法集中注意力,因为她总是睡着。她感到孤立,但不想去寻找他人。“这是我考虑了很久的事情,现在我想我有了答案,”她谈到那句话时说。“也许我再也不会睡觉了。”
我记得写那句话的情景。为了捍卫我当时正在考虑将死亡作为出路的心智,我越过了界限,写了关于自己的话:以努力衡量的爱,是他能力范围内唯一的爱。失败,同样以努力衡量,也将是他有朝一日必须与之和解的失败。
—
前几天,我通读了特雷弗的来信。我希望能有办法把它们写进这本书里。但我也希望能有办法像书中另外两位朋友一样,不提及他的名字。
—
“你的宝宝多大了?”多年前,当我住进我们即将共享的病房我这边时,一个年轻女子问我。“三天,”我说,“我们回家后他发烧了,所以又住进来了。”“你的宝宝多大了?”我问。“昨天满月了,”她说,“我们在等他长到五磅。”她是个高中生,没被叫去喂宝宝的时候,她就在床上学习。放学后,一个和她同龄的男孩来看她,他们挤在她狭窄的床上,窃窃私语,咯咯地笑。两天后,双子塔倒塌了,我那天就在看新闻和探望被隔离的宝宝之间度过。晚上,当我回到房间时,他们已经把频道换到了卡通频道,低声看着《猫和老鼠》。
第一次去德文郡时,火车上邻座的一个年轻女子向我描述了她有朝一日将从祖父母那里继承的寄宿公寓。她的男朋友希望能被那对老夫妇雇用。我想象着他们背着她祖父母窃窃私语、咯咯傻笑,就像多年前那对新父母一样。人对陌生人的希望来得更自然。也许爱荷华的那个孩子,现在已经是青少年了,仍然有彼此相爱的父母。也许那个年轻女子和她的男朋友已经在寄宿公寓安顿下来了。
几年前,在飞往伦敦的航班上,邻座的一位女士要求看我正在读的书以及我在上面写了什么。我给她看了我在伊丽莎白·鲍恩的一个故事里划线的地方,一个人物问另一个:“有没有什么事是你从未告诉过我的?”“可怕”,我在页边空白处写道,而那位女士坚持要我写下“对亚历克斯来说没那么可怕”,亚历克斯是她的名字。
在我最近一次访问德文郡时,一位出租车司机问我当地的监狱是辛辛监狱还是恶魔岛。“恶魔岛,”我说,他表示遗憾,因为这样我就不会听说过他那位三十年代被关在辛辛监狱的亲戚了,那位亲戚有举办家庭派对的记录,而派对上的人总是不断消失。
“是我的爱尔兰负罪感把我驱赶到了西海岸,”加州的一位出租车司机对我说,“你听说过詹姆斯·迈克尔·柯里吗,我的叔祖父,波士顿唯一一位从监狱里当选的市长?”“拿着我的名片,”司机催促我,在我下车前,他提醒我去查查他家的故事,我尽职地照做了。
一天早上在华盛顿特区,我和另一个女人站了半个小时,等待机场柜台五点钟开放。她是一位单身母亲,她和三个女儿正要去迪士尼乐园。她们打包了所有派对服装,还检查了一遍清单,确保拔掉了家里所有的电器插头。“她们为了这次旅行攒了好几年的钱,”那位女士说。“和你聊天真愉快,”柜台开放时她说,“我们应该交换电子邮件。”
人们喜欢被问及他们的生活。有时他们只需要有人倾听。没有比这更安全的方式置身于世界之中了,直到倾听将你拉入一个不请自来的故事。“我不知道自己还有多少时间。我想知道你是否愿意见个面,看看你是否对我的故事感兴趣,”一位患癌症的女士写信给我。我曾以为拒绝一个垂死之人的愿望是不可能的,直到那位女士再次写信,预言我会取消预约,因为她“受到连环杀手汉尼拔·莱克特博士角色的启发而成为一名精神病医生。有过自杀和杀人意念。一直在善良与邪恶之间挣扎。这些年一直追求幸福却从未找到。常常希望我有一个按钮可以按下,杀死全人类。”
“你必须保护好自己,”一位朋友警告我。但要写作,人就必须从根本上放弃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