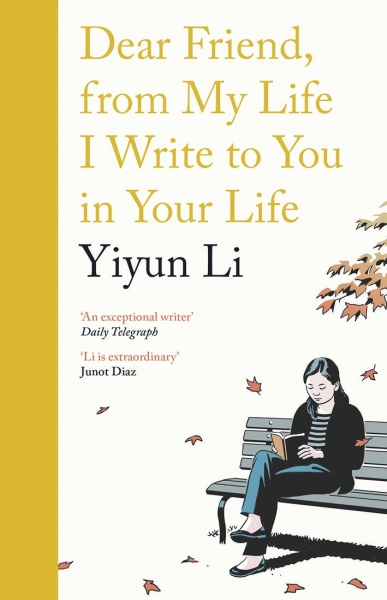—
我读到的威廉·特雷弗的第一个故事是《传统》,背景设定在一所爱尔兰寄宿学校。它发表在《纽约客》上,配图是一张穿着深色西装的年轻学者的照片。它的现实离我的现实很远。那时我还在读理科,不确定是否应该继续下去。我的疑虑在于,我可以轻易地看到自己的生活在眼前展开:一年后拿到学位,几年博士后训练,一份学术界或生物医药行业的稳定工作,房子和孩子,还有一条狗,因为一条在精心维护的院子里嬉戏的狗,在我看来一直是美国生活的顶峰。
读完那个故事后,我借来了特雷弗最新的短篇小说集《山地单身汉》,然后踏着雪从大学图书馆走到学生活动中心,坐在那里面对着一个每晚放映小众外语片的电影院旁边的绿色沙发上。记忆保存下来的细节可能很乏味,只对记忆者本人有意义,但正是这平淡无奇的东西,依然神秘。
若声称在那第一次相遇中就建立了一种连接,未免冒昧;但若说通过阅读特雷弗,一个我此前未知的空间得以可能,则不那么冒昧。《山地单身汉》之后,我开始读他其他的书。几周后,我和导师讨论了离开科学界的可能性。“留下吧,”他说,“你在这个国家有光明的前途。”“是的,”我说,“但我已经能看到自己在那前途的尽头;我知道如果我不尝试这个,我会后悔的。”
这个,正如我向他解释的,是成为一名作家。写作是为了找到一种看待世界的新方式,而在阅读特雷弗时,我毫不怀疑,我想要像他那样去看。
—
在特雷弗访问美国前几个月,我们通过信件往来确定了会面日期。2007年10月,我从加州乘坐红眼航班飞往波士顿,与他共进午餐。我有三个小时的时间,因为要赶晚上的航班回去。
午餐时谈了很多事:前一年特雷弗和妻子简为见将为他们雕刻墓碑的刻字工而进行的旅行;几十年前他与父亲关于自己想成为刻字工的对话;一场葬礼上,违背逝者和生者意愿播放了宗教音乐;与格雷厄姆·格林的对话,另一次与V.S.普里切特的对话;对莫莉·基恩作品的描述以及她安葬的墓地,我会在第二年去参观。午餐进行到一半,一位穿着橙色衬衫的女士走过餐厅露台,引起了特雷弗的注意。“那一刻,她身上有种难以理解的东西,”他解释道。“这样的时刻可能会过去,”他说,尽管我感觉到,它们常常并不会。
午餐后,特雷弗带我去看他酒店附近的亨利·摩尔的作品。我跟着他,或者说我的眼睛跟着我以为他正在看的地方,感到忧虑不安。我可以描述那个十月里阳光明媚的新英格兰下午,以及被正在变色的树木环绕的青铜雕塑,但那都会是陈词滥调。事实是,我不知道我应该看到什么。
—
这种忧虑不安反复出现,在博物馆、画廊和电影院里。有一次,一个朋友指出我描写菊花的一句话感觉不对。“写得不坏,”我说,为它辩护,丝毫不怀疑自己已把每个词都用得恰到好处。“不是句子写得不好,”她说,“而是它并非源于感知,而是源于感知的缺失。”
这种观看的艺术——看一幅画、一件雕塑、一部电影——对我来说是难以捉摸的。在特雷弗的中篇小说《亚历山德拉之夜》里,一个爱尔兰外省小镇的电影院提供了一个关于爱与忠诚的故事背景。在特雷弗的回忆录中,日子在电影院里消磨,青春的无聊被银幕上的奇观所补偿。
我从未感受到电影的吸引力。北京的电影院——在70年代和80年代初被称为工人俱乐部,能容纳一千多人——几乎提供不了什么奇观。关于西哈努克国王和他的战友波尔布特将军的新闻纪录片重复乏味,而那些我们常常被要求作为学校活动去看的电影,远不如坐在附近的人们吸引我:一个嗑瓜子的女人,或一个用搪瓷缸子喝茶时发出咕噜声的男人。电影放映中常常有人被叫走。一张手写的字条,说某某同志因紧急情况被找,会被投射到银幕旁边黑暗的柱子上。这些中断感觉像是谜语,答案被永远扣留。我顺从地编造情景来满足自己。我曾希望自己的名字会出现。
在部队里,我最害怕的活动之一是每周看电影,一项旨在提高士气的文娱活动。我和邻座的女孩建立了一项竞赛,看谁能在这些电影中睡得更久——我赢的次数更多。但我的“功绩”不如另一个班的那个女孩令人钦佩,她能以最完美的军姿站立,却自信地打瞌睡。
白天睡觉的女孩们是你的盟友。熄灯后到起床号前,她们占据储藏室和厕所隔间,背诵英语词汇。也有其他的夜游者。有一次发现一个女孩在黑暗中哭泣;她后来被送回了家。有一次我的同 bunkmate(铺位伙伴),据说是中国顶尖的年轻数学家之一,去上厕所时被一个女孩拦住。那个女孩熄灯后花了几个小时试图解决一个著名的数学难题,请求她的帮助。“疯了”,有人评论道,但痴迷也同样需要尊重。我班里一个娇小的女孩给我们讲她村里的故事,那里的女人用除草剂和农药自杀,就像——用她确切的话说——苹果从苹果树上掉下来一样轻易。同一个女孩在一本杂志上阅读并标记了几条启事,是年轻女性登广告希望在军队中寻觅知音。“淫荡,”她称呼那些女人,“她们想要的只是嫁个军人图个实际好处。”我表示怀疑,但还是被说服了——“别质疑我,”她说,“这些人我太了解了”——起草了回信。我编造了男性的名字和军衔,结合对军旅生活的扎实了解,用部队发的信封寄出信件,以确保回信会寄到我们虚构的自己手中。我们等了几天,几周。没有一封情书最终落入我们手中。
—
电话里,母亲告知我舅舅去世的消息时,还告诉我他临终前变得暴力,殴打他的子女和孙辈。“你表兄妹们说是老年痴呆,”她说,“但你觉得他真正的问题是不是精神上的?”
母亲谈论精神疾病和自杀的方式让我不安。我抵达北京那天,她告诉我一位小学同学的父亲去世了。他妻子出去买菜时,他详细列出了银行账户和密码,需要支付和已经处理的账单,然后上吊自杀了。“你记得他吗?”母亲问。“记得,”我说。“他积极参加退休人员合唱团,”母亲说,“是个不错的男高音。”“他看上去挺开心的,”她说,“为什么要这样做?”我没有答案,于是母亲问我她是否告诉过我我们以前的邻居肖阿姨去世的事。“说过,”我说,但这并未阻止她再说一遍:那位女士前一年从她八楼的公寓跳了下去。她彬彬有礼,有些疏离,在大多数女人都穿灰蓝色毛式中山装的年代,她总是衣着优雅,是我童年认识的最有风度的人之一。她拒绝加入邻里的闲聊(因而自己也成了话题);她从不干涉我或任何孩子的闲事。
我长大的过程中,我们全家从未一起旅行过。我七岁那年夏天,住家离北京四个小时火车路程的舅舅,带我和姐姐去了他家,那是我第一次坐火车,第一次踏足另一座城市。也许是他的去世让我修改了记忆,但似乎在舅舅家的那两周属于我童年最快乐的时光。尽管回想起来,我知道那个夏天对他的家庭来说必定是艰难的。我们的大表哥参加了高考,考了全省第三名,但他因小儿麻痹症而有明显的跛行,所以没有大学录取他。他很安静。尽管如此,他还是像个尽职的主人一样带我们在镇上转悠,用一辆28寸轮子、为农用加固过的自行车,载着四个孩子。当他骑车穿过小镇时,我和姐姐还有两个表弟表妹向人们挥手,仿佛我们是一群杂技演员。
舅舅每晚都会在风琴上弹奏好几个小时。我不懂他的音乐,但我着迷于那上下踩动的踏板。
我上高中时,舅舅给他的三个外甥女写了一封长信,叙述他的委屈。他六岁时日本人入侵了他的家乡,父母撤离时,他被留下了。(“不对,”母亲和姨妈说。正确的版本,她们解释说,是他当时正和一个仆人的儿子玩,拒绝离开,说他要去他们外公家住几天;但外公很快被日本人杀害,几天变成了几个月。)他在信中写道,父母从不关心他,十几岁时他被迫去参军谋求前途。(“不对,”母亲和姨妈说。她们的大哥,国民党军队的一名军官,帮他报名当了军校学员。)两兄弟都在内战中与毛泽东的军队作战。战败后,其中一个去了台湾,而错过船的舅舅则被送到一家工厂接受改造。最终,他在一所小学当了音乐老师。到他写信的时候,已有更多理由抱怨生活的不公:他在台湾的哥哥的富裕(如果他离开中国,自己本可以过上同样的好日子),他儿子的残疾,使他难以找到妻子,他独生女儿的死胎。失望接踵而至:有人曾试图理解他吗?这个问题让姨妈和母亲很不安。她们认定他一定是像许多前辈一样疯了。不然他为什么会写这些不实之词?难道他还没有三个孩子来继承他的不幸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