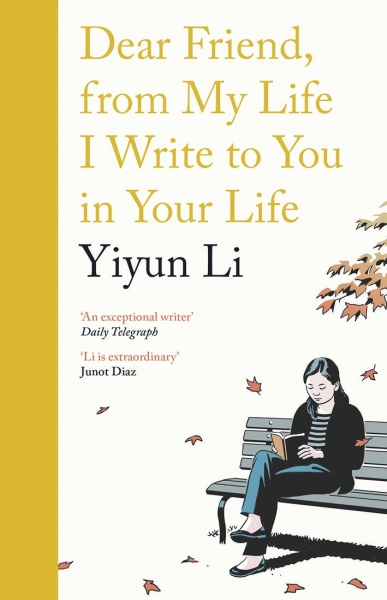在一次由两位作家举办、他们母亲也出席的朗读会上,我看着她们以一种我所羡慕的自在共享着同一个空间。我本可以问她们很多事情,关于阅读她们孩子的作品以及被写进书里的感受。但我真正想知道的是:你给你的孩子们做什么样的饭菜?
从我记事起,母亲从未给我做过一顿饭。这是一个用任何声音都无法讲好的故事。
找一个像阿拉伯马一样热烈的年轻人,让他结婚,他就完了。首先女人是骄傲的,然后她是软弱的,然后她晕倒了,然后他晕倒了,然后全家都晕倒了。
——克尔凯郭尔,《非此即彼》
我在等孩子放学时读着克尔凯郭尔。我真希望自己能把某个 idling vehicle(空转车辆)里的母亲招手叫过来,给她看这段话。然而,阅读是一种私密的自由:超脱时间,超脱地点。
当你读到墓志铭上的名字时,你很容易会想知道他在世上的生活是怎样的;人会想爬进坟墓去与他交谈。
——克尔凯郭尔,《非此即彼》
写作如同阅读一样,能给人自由,这是一种幻觉。迟早会有人带着他们的期望而来:有些人要求忠诚;另一些人,则要求作为角色而不朽。只有墓志铭上的名字保持沉默。
这些故事像秋天一样沉闷乏味,调子单调,其艺术元素与医学元素密不可分地纠缠在一起,但这一切都不能阻止我冒昧地向您提出一个谦卑的请求,恳请您允许我将这本小书献给您。
——安东·契诃夫致彼得·柴可夫斯基
1889年10月,契诃夫,还不到三十岁,写作生涯刚起步不久,写信给柴可夫斯基,谈到一本即将出版的集子。书名是《忧郁的人》。
在什么情况下,作家和读者可以成为同时代人?契诃夫的邀请是一种消除时间鸿沟的姿态。跨越界限,让另一个人的名字与自己的文字永存——这几乎是一个不恰当的请求,然而非凡之事证明了不恰当的合理性。没有友谊可以是死后的。
阅读威廉·特雷弗
回想起来,没什么道理可言——也许所有的故事,都该这样开头,而不是“从前”。
我的第一本书出版后不久,我请一位爱尔兰朋友寄了一本给威廉·特雷弗,并附上一张感谢便条。我认为这张便条是必要的——没有他的故事,我的故事就不会被写出来。我也想表现得有礼貌,所以便条写得简短而客气。几个月后,收到了一封回信,写得很是亲切。我把信裱起来,挂在书房里。这不像我的风格——赋予一件物品意义,就预设了一种依恋。那是为了激励,我告诉自己,来自一个我渴望成为的人的激励。
故事本可以就此结束。我会继续阅读特雷弗,就像我读屠格涅夫或哈代一样:保持距离,这是毫无顾忌地建立连接的前提。但屠格涅夫和哈代不可能写信给我,并提出某天或许可以见面的可能性。
次年十一月,我去伦敦参加一个活动,便写信给特雷弗,询问是否可能去拜访他。现在想来,我当时的行为简直不可思议,因为特雷弗是最注重隐私的作家之一,这一点我本不难推断出来。换作是我自己,面对这样一个不合时宜的请求,也会感到错愕。
—
想要避免孤立的努力有时让我焦躁不安。从世界上消失的想法是一个紧急出口,离开医院时我同意放弃它。想到过去人们可以轻易消失:跨越边境,更改姓名,销毁证据,切断联系。似乎没人介意郝薇香小姐或罗切斯特夫人的缺席。琼·斯塔福德小说里的一个父亲,走出鞋匠铺后就再也没出现过。《红楼梦》或《源氏物语》中的少女们,心碎或被弃,受辱或幻灭后,便出家为尼,她们的故事在生命远未结束时就已终结。一位舅舅,我母亲的大哥,在共产党战胜国民党的军队前夕消失了,家里一个半是丫鬟半是女儿、被当作他未来新娘养大的孤女,只好嫁给另一个男人。南浔的姨婆,我们这样称呼她;没有其他亲戚是以居住地来称呼的。一本相册里有她每年寄给我外公的家庭照片,她所有的孩子都继承了她非凡的美貌,每次我翻动书页,他们就在我眼前毫不费力地长大。南浔的姨婆之所以常被提起,是因为那个不可提及的人,一个舅舅,在乐观的日子里被认为活在台湾,当乐观无法维持时则被认为已在战斗中牺牲。(我是一次偷听母亲和姨妈谈话时,才知道他的存在以及对他命运的推测。我傻乎乎地告诉了学校的一个朋友,她随后写了张字条告诉老师我这个在台湾的舅舅。字条被转交给了我母亲。老师是她的同事,足够体贴地截下了一个可能带来麻烦的秘密,尽管我对老师找不到感激,对朋友也无法原谅。正是因为她们的多管闲事,我挨了一顿打。)
四十年后,这位舅舅像他消失时一样出人意料地出现了,在一封长信里,信经过许多人的手,花了一年多时间才送到他父亲手中。我的外公,只剩几个月生命,希望能与失散的儿子团聚,但台湾海峡两岸的旅行禁令还要再过两年才会解除。
我们现在生活在一个永远连接的世界里,只被分配了对隐私和独处的奢望。有一次,我的绿卡申请被拒,并且被新闻报道了,一个自称 S 医生的男人不停地打电话到我的工作单位提出要与我结婚,说这样能帮我拿到绿卡。有一次,在一个鸡尾酒会上,我刚走进修剪整齐的花园,一个女人就对我说:我想让你知道,如果我母亲有你的成就,她是不会自杀的。在东萨塞克斯郡的一个文学节上,我看到一个男人在活动结束后走近特雷弗,问他是否可以顺道去喝杯茶,并准确而详细地描述了特雷弗的房子。
—
在寄给我出版商和酒店的便条中,特雷弗让我一到伦敦就给他打电话。他提议见个面,不在他居住的德文郡,而在巴斯,一个双方乘火车都更方便的地方。我知道这是他的体贴,但我也想到,巴斯对他来说,与陌生人见面会更安全。我也可能是一个特雷弗故事里的角色,安静、不起眼,却拥有莫名其妙的恶意。一个不信任他人、能够用冷酷的想象力剖析自己的人,究竟值得信任吗?
结果证明,我去不了巴斯。那天安排了宣传活动。我既失望又松了口气。外部的干预使人免于矛盾心理。我想见特雷弗的愿望,与害怕它真的发生的恐惧一样强烈——我无法摆脱那个开始困扰我的疑问:你是谁?是什么让你觉得自己是无害的?
我回了电话,希望特雷弗也松了口气。我们聊了一分钟天气——伦敦在下雨,德文郡也在下雨。他告诉我以后还会有机会。明年他和妻子计划来美国。“坐船来,”他说,“我向你保证,那是更愉快的旅行方式。”
—
2015年7月。我和丈夫成为美国公民后第一次访问中国。在白山,我丈夫的家乡,母亲打来电话,说她哥哥那天早上过世了。
多年前,我曾在没见过白山的情况下,写了一部以它为背景的小说。白山,曾叫浑江,因流经城镇的河流而得名。上世纪90年代,市政府认为这个名字有碍其繁荣,便给城市改了名。我以小说家的投机取巧,认领了那个被遗弃的浑江。丈夫曾画过一张大约70年代的城市地图,我便跟随人们的脚步在其中穿行。
当我们进入市区时,我注意到了我笔下两个人物初次相遇的桥,一条信任主人的狗被毒死的山脚,一个杀人犯清洁工工作的发电厂冷却塔,还有那条河本身,恰如其名地浑浊,连日降雨后水流湍急。我曾想过,是否会注意到一些关于这个地方及其居民、我在写小说时未曾想象到的东西。结果没有,这令人失望。我不在乎我的想象力有限;我在乎的是,当世界并不比人所能想象的更大时。
直到接到舅舅去世的电话前,我一直情绪低落。“拜托,”我命令我的眼睛,“找一件意料之外的事”,但中国的一切似乎都只是印证。出租车司机讲着二十年前我就听过的政治笑话。拥挤的人群让我不耐烦,我用一种轻易就回来的攻击性,以及随口而出的粗鲁俚语,去肘击插队者。我的孩子们,像西方游客一样,不断被公共告示和标牌上蹩脚的英文翻译逗乐,但对我来说,那些都是陈词滥调。只有一次,我停下来欣赏了一条信息。在北京国际机场,一个布告板上的女人鼓励观众享受生活。“看看这展现在你面前的美好生活吧,”她用中文规劝道,但在英文翻译里却显得怀疑(或颠覆):This wonderful life lies as you see it. (这美好的生活如你所见是个谎言/就躺在你眼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