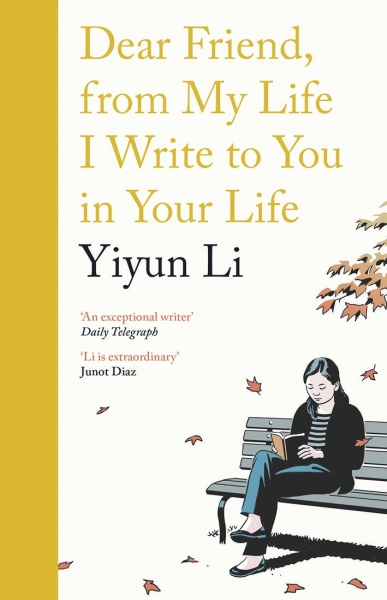与内在相比,外在变得微不足道,无关紧要。反思性悲伤的关键在于,悲伤在不断寻找它的对象;这种寻找即是悲伤的不安及其生命力所在。
——克尔凯郭尔,《非此即彼》
在这段困难时期,唯一一次我真正毫无顾忌地大笑,是某天我坐在病区沙发上,觉得生活没什么希望。另一位病人从我手里抢过《战争与和平》,用脏话连篇地骂我,说我用这些胡说八道的东西搞乱自己的大脑。她对托尔斯泰的怨恨是如此个人化,以至于我笑得停不下来。
“我让你笑了吗?”她说。然后她举起那本厚书。“这该死的书让你笑过吗?没有!它重得要死,能砸死我。”
“好吧,你想让我怎么办,”我说,“我改变不了自己。”
“多笑笑,”她说。
笑声需要一个目标,我想说;它不是论证,而是评判;我宁愿论证而非评判。这些想法在我脑中盘旋,让我不禁自嘲。
当人们坚持说我看起来太快乐,不像写那种作品的人,或者我的作品对我这样子的人来说太阴郁时,我便油嘴滑舌地回应。“哦,”我说,“有那个奇妙又悲伤的克尔凯郭尔啊。”有一年,当我无法自救于绝望时,我着魔般地读他。他比任何其他作家都更让我发笑。
一个长篇故事终究有一个可测量的长度;另一方面,一个短篇故事有时却具有令人困惑的特性,比最冗长的故事还要长。
——克尔凯郭尔,《非此即彼》
有一年夏天,我十二岁的儿子把《悲惨世界》从头到尾读了三遍。我徒劳地想说服他,那并非唯一伟大的小说,维克多·雨果也不是唯一伟大的作家(我甚至对他说,连唯一伟大的法国作家都算不上)。
一个刚开始认真阅读的年轻人,往往一次只沉浸在一本书里——甚至为之痴迷。书提供的世界足够广阔,足以容纳所有其他世界;或者足够排他,足以让所有其他世界退避。有时这本书会被另一本取代,旧世界让位于新世界;那种着魔——或曰陷入——也可能是一生只有一次的经历。
孤独是高贵的,但对于没有力量从中挣脱的艺术家来说却是致命的。艺术家必须过他自己时代的生活,即使那生活喧嚣污浊:他必须永远地给予和接受,给予,再给予,然后再次接受。
——罗曼·罗兰,《约翰·克利斯朵夫》
几年前,我在一家旧书店发现了一本《约翰·克利斯朵夫》的英译本。小说最初出版于1910年。在我找到的1938年现代文库版中,作者名字后面只标了出生年份:罗曼·罗兰(1866–)。书的主人写下了他的名字,爱德华·G——,以及日期“1943年10月30日”在封里。罗兰买这本书时还健在:它的主人是罗兰的同时代人。除了这个标记,他没有在文本上划线,也没有在页边空白处做评论。
十六岁到十八岁之间,我读了《约翰·克利斯朵夫》的中译本很多遍。刚到美国时,我带着一本法语语法书和一本词典,对法语一无所知,却着手阅读法语原文,同时对照英译本,两本书都是从大学图书馆借来的,在那里放了几十年都没人借阅过。我以为这是个好方法,可以用一本我几乎背下来一半的小说来提高英语和学习法语。还没读到第二卷,两本书就到期了。
罗兰,这位小说家、剧作家、音乐评论家、传记作家和诺贝尔奖得主,在这个国家早已被遗忘,我想部分原因在于他是个共产主义者(而且还是个法国人!)。
人年轻时,阅读往往没有语境——或者说,所谓的语境不过是个借口。一个爱情故事是为爱情做准备,一个悲伤故事为悲伤铺路,一部史诗则是一次荣誉与光荣的体验。生活也是如此。人学会理解自己的语境并与之和解,而不是从一个借口跳到下一个借口。后一种体验我一直很熟悉。多年来我一直相信,我所有的问题都会在我正在阅读的书里找到答案。然而,书只会引向其他的书。
现在想来令人惊讶,《约翰·克利斯朵夫》,一部关于参与政治、参与生活的小说,曾一度是为我提供了整个世界的小说。如今我还会相信罗兰的话吗?我终于到了明白我所寻找的答案不在任何书里的地步。
我说我自己的性格如何像一个影子一样在我面前切割出一个形状。她理解了这一点(我举此例说明她的理解力)并证明了这一点,她告诉我她认为这不好:人应当融入事物之中。
——弗吉尼亚·伍尔夫日记,关于她与凯瑟琳·曼斯菲尔德的最后一次会面
弗吉尼亚·伍尔夫和凯瑟琳·曼斯菲尔德之间有着紧张而不自在的友谊,这在两个既是对手又彼此理解的人之间很常见。
一个切割出来放在自己眼前的 shadowy shape(模糊形状)不是一个角色,而是一个幻影。融入事物之中——曼斯菲尔德的这句话里有契诃夫的回响。曼斯菲尔德去世后,伍尔夫批评说,曼斯菲尔德无法“将思想、或感情、或任何种类的精微之处赋予她的人物,而不在严肃时变得生硬,在同情时变得伤感”。
她(凯瑟琳·曼斯菲尔德)说了不少关于深刻感受事物的话:也说了关于纯洁,对此我不予置评,尽管我当然很可以评论。但现在我对自己的写作感觉如何?——这本书,也就是《时时刻刻》,如果那是它的名字?人必须带着深切的感情写作,陀思妥耶夫斯基说。而我呢?或者我只是用词语编造,因为我爱它们?不,我想不是。在这本书里,我的想法几乎太多了。我想赋予生命与死亡,理智与疯狂;我想批判社会体制,并展示它在最激烈状态下的运作——但在这里我可能在装腔作势……我是带着深切的情感在写《时时刻刻》吗?当然,疯狂的部分让我非常疲惫,让我的思绪严重扭曲,以至于我几乎无法面对接下来几周的写作……然而,或许是真的,我没有那种‘现实感’的天赋。我使事物非实体化,某种程度上是故意的,不信任现实——它的廉价。但更进一步说。我有能力传达真正的现实吗?还是我只是在写关于我自己的散文?无论我如何以不恭维的方式回答这些问题,这种兴奋感依然存在。
——弗吉尼亚·伍尔夫在曼斯菲尔德去世后的日记条目(这段常被引用,因为它谈到了《时时刻刻》,后改名为《达洛维夫人》)
人们可以继续引用伍尔夫在信件和日记中对曼斯菲尔德的评论。有很多,有些敏锐或同情,另一些则不公,甚至琐碎。但在曼斯菲尔德所有的笔记本中,伍尔夫只出现过两次。1920年7月,有一条简单的记录:“弗吉尼亚,周三下午。”根据伍尔夫的日记,这个日期指的是一次午餐,当时两人对约瑟夫·康拉德的新书《援救》意见不一。“我仍然坚持我是真正的先知,是那群顺从的绵羊合唱中唯一的独立声音,因为他们一致赞扬,”伍尔夫写道。(人们不禁好奇,她是否会乐于享受自己未来处于康拉德那种地位。)
伍尔夫第二次出现在曼斯菲尔德的日记里时,没有被点名,只被称为“那对坐在藤椅上的出版夫妇”中的一员。当然不能确定这对夫妇就是伍尔夫夫妇。但那段描述——一种冷静观察下的人物肖像,正是曼斯菲尔德的长项——让我们想起了他们。其中一句话,大概是对伍尔夫的恭维,格外引人注目:“她是那种女人——那种历经一切仍然存在的女人之一。”
曼斯菲尔德这话是什么意思?不管怎样,这并不改变旁观者那种奇特的满足感。这两位非凡的女性永远不会知道她们在各自的私密文件中对彼此说了(或没说)什么。这种不知情将她们变成了角色。看到他人生活的语境,而那语境却对身处其中的人保密:读者最终总是赢家;读者有无限的时间来干预人物的生活。
哦,她确实把我写进了她的书里,但只是那些古怪的瞬间。
——一位作家的母亲
现在你们都长大了,我都没人给做薄煎饼了。
——一位朋友的母亲
每个人都可以用一种无所不知的声音来讲述他人的故事。然而,有一种无所不知的声音我无法忍受,但它却是唯一持续压倒其他声音的声音。
写作是我生活中唯一超出我母亲叙述范围的部分。我一直避免用自传体的声音写作,因为我无法忍受它可能被我母亲的无所不知所覆盖。我可以轻易地在她的叙述中看到我生活的所有其他部分:我的婚姻,我的孩子,我的过去。正如她要求进入我的叙述一样,我也要求被排除在她的叙述之外。没有办法改变这一点;不可能有幸福的结局,甚至连结局都不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