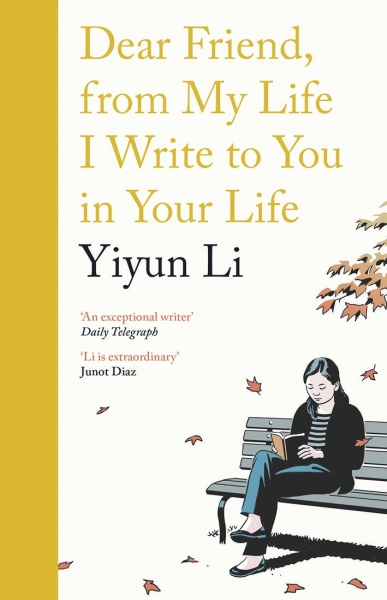歌词是中文的。记忆也本该是中文的。但是,如果我不给自己用英语命名这些事物——我们那有葡萄藤的小园子,那是父亲栽种的,后来被愤怒的母亲拔掉了;点缀着牵牛花的竹篱笆;占据了半个阳台的、父亲多年积攒堆高的杂物——我就无法看见它们。我看不见我的姐姐,但我能听见她用英语唱出那些歌词。
多年来,我的大脑已经驱逐了中文。我用英语做梦。我用英语自言自语。而记忆——不仅是关于美国的,也包括关于中国的;不仅是持续存在的,也包括那些希望遗忘而被存档的——都用英语分类整理。与我的母语成为孤儿,过去感觉,现在仍然感觉,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决定。
“你有没有考虑过用中文写作?”一位来自中国的编辑问道,就像许多人之前问过的那样。我说我怀疑自己不会。 “但你不想成为当代中国文学的一部分吗?”他问。我拒绝将我的书翻译成中文,这被一些人理解为令人厌恶的自命不凡。偶尔,我母亲会评论,暗示我的自私,说我剥夺了她阅读我书籍的乐趣。但中文从未是我的私人语言。而且永远也不会是。
我用英语写作——这是否使我成为其他什么的一部分?我在研究生院的教授的论断是,我用一种不属于我的语言写作,因此我不会,也不该,属于任何地方。但他的抗议是无关紧要的。我并非为了成为什么的一部分而使用这种语言。
——
当我们进入一个世界——一个新的国家,一所新的学校,一个派对,一次家庭或班级聚会,一个军营,一家医院——我们说它所要求的语言。适应的智慧就是拥有两种语言的智慧:一种是别人说的语言,另一种是自言自语的语言。一个人掌握公共语言的方式,与习得第二语言的方式并无太大不同:评估情境,用正确的词语和正确的句法构建句子,如果能避免就捕捉错误,否则就在犯错后道歉并吸取教训。公共语言的流利,就像第二语言的流利一样,可以通过足够的练习来达到。
也许这两种语言——公共的和私人的——之间的界限是,并且应该是,流动的;但对我来说从来不是这样。写作时,我常常忘记英语也被其他人使用。英语是我的私人语言。每个词都必须经过反复斟酌,才能成为我的词。我毫不怀疑——这会是一种错觉吗?——我与自己的对话,无论在语言上多么有缺陷,都是我一直想要的对话,以我想要的确切方式进行。
在我与英语的关系中,在这种因其固有的距离而引人侧目的关系中,我感到隐形,但不疏离。这是我相信我一直想要在生活中占据的位置。但每一次追求都有越界的危险,从隐形到被抹去。
曾经有一段时间,我能用中文写得很好。在学校,我的作文被用作范文;在部队,我们的班长让我选择是为她起草演讲稿,还是去打扫厕所或猪圈——我总是选择写作。高中有一次,我和几个同学参加了一个演讲比赛。获胜者将代表班级参加一个爱国主义活动。当我走上台时,出于某种恶作剧的原因,我确保了许多听众被我编造的、富有诗意但不真诚的谎言感动得流泪;我自己也被感动得流泪。我可能会成为一个成功的宣传作家的念头闪过我的脑海。我感到不安。一个年轻人想要忠于自己和世界。但我当时没有想到要问:一个人的智力能完全依赖公共语言吗?一个人仅凭公共语言就能形成精确的思想,回忆起准确的记忆,甚至感受到真切的情感吗?
我的母亲,她喜欢唱歌,常常唱她童年和青年时期的歌曲,许多是五六十年代的宣传歌曲,但有一首歌她念叨了一辈子,因为她不知道怎么唱。她在幼儿园学的这首歌,那年共产党接管了她的家乡;她只记得开头第一句。
医院里有一位老妇人,总是带着一双闪亮的红鞋子坐在走廊里。“我觉得自己像多萝西,”她一边给我看那双她从捐赠给病人的物品中挑选出来的鞋子,一边说。有些日子她头脑清醒,会谈论那双磨脚的红鞋子,或者那些让她大脑感觉麻木、身体疼痛的药物。其他日子里,她对着空气说话,与看不见的人进行无休止的对话。那些通过离开或死亡抛弃了她的人们回来了,让她哭泣。
我常常坐在这个孤独的多萝西旁边。我是在偷听吗?也许是,但她的对话已超越了侵犯的范畴。一个人可以达到公共语言和私人语言之间的界限不再重要的地步,这是令人恐惧的。一个人所做的许多事情——为了避免痛苦,为了寻求幸福,为了保持健康——都是为了给自己的私人语言保留一个安全的空间。然而,生活的自动参与,可以将那个空间变成一个安全的坟墓。那些失去了那个空间的人只剩下一种语言。据我母亲和她的兄弟姐妹说,我的外祖母在被送进疯人院死去之前,已经变成了一个与看不见的人说话的女人。有太多东西可以放弃:希望,自由,尊严。私人语言蔑视任何禁锢。唯有死亡能将其带走。
—
曼斯菲尔德谈到她记日记的习惯时说,那是“喋喋不休……我必须承认,没有什么能给我同样的慰藉”。阅读她的日记却让人陷入两难。她几次以一种嘲弄的口吻直接对读者——她的后世子孙——说话。我宁愿不信她。但不承认阅读日记带来的慰藉,那也是不诚实的。我找不到确切的语言来形容当时感受到的那种绝望,便狼吞虎咽地吞食她的文字,如同饮下止渴的毒药。一个人,有没有可能被他人的文字所挟持?我划线、重读的那些句子:究竟是她的思想,还是我的?
除了工作,别无他事可做,可身体如此虚弱不堪,连笔都像根拐杖,叫我如何工作。
这种建立联系的永恒渴望中,蕴含着某种深刻而可怕的东西。
一只傻乎乎的小鸟飞离后,一根大树枝竟会如此剧烈地摇晃,真是惊人。我想小鸟是知道这一点的,并且为此感到无比傲慢。
人想要的,不过是确信有另一个人在。仅此而已。
我比任何人都更清楚自己的缺点。我确切地知道自己错在哪里。
除了那些遥远的人,其他人对我来说,曾存在过吗?还是他们总是让我失望,因为我否认了他们的真实性而最终褪色?假设我就这样死去,坐在这张桌子旁,把玩着我的印度裁纸刀——又会有什么不同呢?毫无不同。那么我为什么不自杀?
—
当一个人用习得的语言思考时,他排列、重组着那些中性,甚至漠然的词语,试图抵达一个自己并不知道它在那里的思想。
当一个人用习得的语言回忆时,那记忆中便有了一条分割线。此前发生的一切,像是别人的生活;甚至可以说,那就是虚构。有时我觉得,正是这种疏离感,让我显得冷漠和自私。忘记过去是一种背叛,我们年少时在学校是这样被教导的;否认记忆是一种罪过。
人需要用什么语言来感受?或者说,人需要语言才能感受吗?在医院里,我旁听过一堂医学院学生的课,研究心智与大脑。一次面谈后,带班的医生问起感受。我说,那或许是无法描述的东西,而要描述它,超出了我的能力。
“如果你能清晰地表达你的想法,为什么不能清晰地表达你的感受?”医生问。
我花了一年时间才想明白答案。用习得的语言去感受,很难;然而用母语去感受,已经不可能。
—
我常常觉得,写作是徒劳的;阅读也是;生活亦然。孤独,是无法用自己的私密语言与人交谈。这种空虚被公共语言或浪漫化的连接所填补。但人在假定意义时必须谨慎。两个人之间瞬间的认同,反而更凸显了语言的匮乏。可以言说的,无法维系;无法言说的,暗中侵蚀。
做了那个关于公用电话的梦之后,我想起了在部队的一刻。那是除夕夜,我们奉命观看中央电视台的官方庆祝晚会。节目进行到一半,一个值班的女孩过来说,有我的长途电话。
那电话和我家大院里那种黑色转盘电话一模一样,是我姐姐打来的。那是我人生中接到的第一个长途电话。下一次要等到四年后,一位美国教授打电话来面试我。我至今还记得那个女人,从纽约市西奈山医院打来,问我对免疫学的兴趣,谈论她的研究项目和在美国的生活。我的英语水平足以听懂她一半的话,而背景里的沙沙声则让我为错过的那一半急出汗来。
可是,在那个除夕夜,我和姐姐到底谈了些什么?在抛弃母语的过程中,我已将自己从那段记忆中抹去。常常有人问我——或者干脆断言——英语是否给了我表达的自由。仿佛只要习得另一种语言,人就能变成一个全新的自己。但是,抹除并不会随着新语言的到来而停止,而那,我的朋友,正是我的悲哀与自私所在。用习得的语言说话、写作,我从未停止抹除。我也越过了界线,从抹除自己,到抹除他人。在这场对抗自我的战争中,我不是唯一的伤亡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