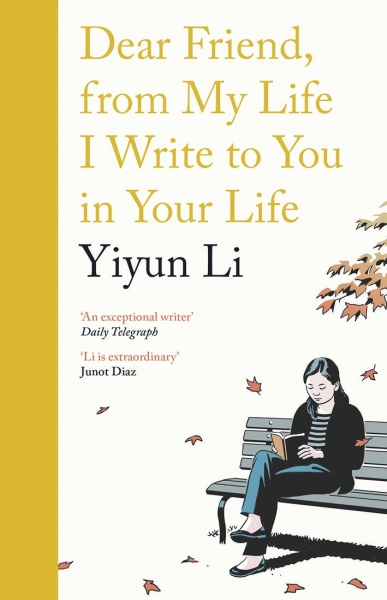想象纳博科夫的悲哀时,我感到一丝愧疚。像所有的亲密关系一样,一个人与母语之间的亲密关系,所要求的可能超过一个人愿意给予的,或能够给予的。如果我允许自己诚实,我会借用纳博科夫的话,做出一个更强烈、也更奇怪的声明:我的个人救赎,不能也不该成为任何人的事,那就是我抛弃了我的母语。
有一段时间,我身体不适,梦境常常回到北京,站在一栋楼顶——那种灰色的、苏式风格的公寓楼——或者迷失在一辆穿行于陌生街区的公交车上。从这些梦中醒来,我会在日记里列出梦中未出现的记忆:阳台下的燕子窝,屋顶上的铁丝网,老人们坐着闲聊的花园,街角的邮筒,圆圆的,绿色的,蒙着灰尘,半透明的方形塑料窗后面贴着手写的收信时间。
然而,我从未梦到过爱荷华市,我在美国的第一个落脚点。当被问及对那里的最初印象时,我无法从记忆中挖掘出任何东西来形成一个有意义的回答。最近一次去那里旅行,我探访了以前每天走过的街区。那些一层楼的房子,漆成宜人的柔和色调,前面有白色尖桩篱笆围起来的花园,都没有改变。我意识到,我从未用中文向别人或向自己描述过它们,而当英语成为我的语言时,它们已经变成了日常的平淡无奇。在我从一种语言过渡到另一种语言期间发生的事情,并没有成为记忆。
——
拥有——一所房子,一条安静街道上的生活,一种语言,一个梦想——就是允许自己也被拥有。当现在滑入过去的瞬间,拥有就开始被抛弃所取代。何必等待那不可避免的结局呢?
人们常常问我决定用英语写作的事。“从一种语言转换到另一种语言对我来说感觉很自然,”我回答道,尽管这说明不了什么,就像一个人很难给出令人信服的解释,为什么某人的头发在这天而不是另一天变白,或者为什么有些鸟在气温下降时会飞向南方。但这些都是空洞的类比,被用作借口,因为我不想触及问题的核心。是的,有些不自然的东西,是我一直拒绝接受的。并非我用第二语言写作——总有纳博科夫和康拉德作为参照,还有许多我的同代人也是如此;也不是我冲动地放弃了可靠的职业去写作。而是那种抛弃的绝对性——如此决绝,以至于近乎一种自杀。
纳博科夫损失的悲剧在于,他的不幸很容易被公共历史所解释——他的故事成了别人的财产。我决定用英语写作,也被解释为是对我国家历史的一种逃离。但与纳博科夫不同,他曾是一位俄语作家,而我从未用中文写过。尽管如此,一个人对自己的作品如何被接受几乎无法控制,而且一旦通过公共棱镜来看待,一个私人的决定也无法避免地会变成一种隐喻。有一次,一位东欧裔诗人和我——我们都在美国生活多年,都用英语写作——被要求在一个晚会上用我们的母语朗读作品。“但我不写中文,”我解释道,组织者为她的误解道了歉。我提出可以朗读李白或杜甫或任何我从小背诵的古代诗人的诗,但最终安排我朗读的是一位政治犯的诗歌。
隐喻渴望超越的欲望会削弱任何人的故事;它意图阐明的野心会蒙蔽那些创造隐喻的人。在我对隐喻的不信任中,我感觉与乔治·艾略特有种亲近感:“我们所有人,无论严肃还是轻松,思想都会陷入隐喻的纠缠,并因此而做出致命的行动。”我知道,这就是我丈夫多年前质疑的东西。但我放弃我的第一语言是私人的,是如此深刻的私人,以至于我抗拒任何诠释——无论是政治的、历史的还是民族志的。
——
在美国的我们这一代中国移民批评我的英语不够地道。一位同胞发邮件指出,我的语言既不华丽也不抒情,不像一个真正作家的语言应有的样子;“你只用简单的英语写简单的事情,你应该为自己感到羞耻,”他愤怒地写道。研究生院的一位教授告诉我,我应该停止写作,因为英语对我来说将永远是一门外语。他们对语言所有权的担忧,并没有像让纳博科夫那样让我不耐烦,反而让我暗自发笑。英语对我来说,就像任何其他语言一样,是随机的选择。一个人走向什么,远不如他从什么转身离开来得更明确。
离开中国之前,我销毁了多年来保存的日记和大部分写给我的信件(那些我不忍心销毁的,我封存起来,再也没有打开过);至于我写给别人的信,如果我能拿到,我也会销毁。但是,一个人与母语的关系类似于与过去的关系。没有一个时刻你可以指着说:这是我过去的开始,或者这是我与母语关系的开始,在那一刻之前我是自由的。之前发生的一切——别人的过去,别人与那种语言的关系——会违背你的意愿提出权利主张。故事很少在我们希望它开始的地方开始,或者在我们希望它结束的地方结束。
——
一个人跨越边界,是为了成为一个新人。一个人完成手稿,切断与人物的联系。一个人选择一种语言。这些都是虚假和强加的框架,提供虚幻的自由,就像时间在我们痛苦地任其单调流逝时,提供虚幻的宽容一样。“消磨时间”(kill time)——这个至今仍让我感到寒意的英语短语:时间可以被消磨,但只能通过琐碎之事和无目的的活动。没有人会把自杀看作是消磨时间的勇敢尝试。
在医院里,一个周五晚上,一群护理专业的学生来玩宾戈游戏。一个年轻女子问我是否愿意和她一起玩。“宾戈,”我说,“我这辈子从没玩过。”她想了一会儿说,她只在医院里玩过宾戈。那是她第八次住院;她曾在医院里上过一段时间学,有一次她指着一小片用栅栏围起来的绿地说,她和其他孩子曾被放出来在那里活动。她父亲常常下午来看她,我会看着他们坐在一起玩游戏,不试图交谈。到了那时,所有的话语想必都已不够用了;语言对于帮助一个头脑捱过时间,几乎无能为力。
然而语言却能够使一个头脑沉沦。一个人的思想被语言奴役般地束缚着。我曾经认为深渊是绝望的瞬间变得无休无止,但任何瞬间,即使是最可怕的,也注定会结束。深渊般可怕的是,一个人飘忽不定的语言像流沙一样将人吞噬。然而他人所说的话——作为陈词滥调的真理,作为唯一真理的陈词滥调——却像那退却的坚实地面一样不容置疑,越来越遥不可及。深渊在于时间被语言所废除。我们可以消磨时间,但语言会杀死我们。
“病人陈述她感觉自己是亲人的负担”——很久以后,当我读到急诊室的记录时,对那次谈话已没有任何记忆。“亲人的负担”(a burden to loved ones):这种语言一定是提供给我的。我在思考或写作中绝不会使用这个短语。但我的抗拒与避免陈词滥调关系不大。说“负担”是赋予自己在他人生活中的分量;称他们为“亲人”(loved ones) 则是伪装自己爱的能力。一个人并不总想让自己经受陈词滥调强加的自我拷问。
——
凯瑟琳·曼斯菲尔德在新西兰还是个十几岁的少女时,曾在日记中写到隔壁一个男人连续几周用短号吹奏《斯瓦尼河》(Swanee River)。“我伴着《斯瓦尼河》醒来,每顿饭都伴着它吃下,最终枕着‘全世界都悲伤而疲惫’(all de world am sad and weary) 的摇篮曲入睡。”我大约在同一时间阅读了曼斯菲尔德的笔记和玛丽安·摩尔的书信。摩尔在一封信中描述了布林莫尔学院的一次募捐活动,少女们穿着泳衣,拖着绿色的泳尾躺在木筏上:“那真是太逼真了……在那斯瓦尼河下游。”(way down upon the Swanee river.)
我标记了这些条目,因为它们让我想起了一个我已遗忘的瞬间。我九岁,姐姐十三岁。一个周六下午,我在我们的公寓里,她在阳台上。那年姐姐参加了中学合唱团,在秋日的阳光下,她用开始脱离少女期的声音唱着歌。“在那斯瓦尼河下游,路途遥远,家乡可爱。如今我到处流浪,心里更想念家乡。”(Way down upon the Swanee River. Far, far away. That’s where my heart is turning ever; That’s where the old folks sta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