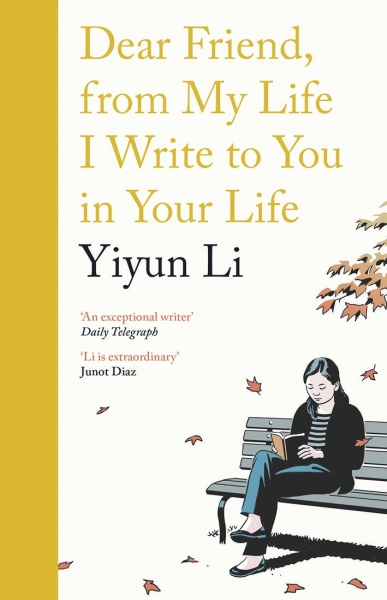在一封信中,拉金思考了特里费娜·斯帕克斯,哈代的表妹,一些人认为她是苏的真实原型。(有猜测说特里费娜是哈代早年的情人;也许还有一个孩子出生。)“但如果这是真的,我会很失望——首先,因为我一直认为哈代是个正人君子 (non bastard),其次,我讨厌他有什么理由变得忧郁——我原以为只有他,唯有他,看到了生命固有的痛苦。”
为什么苏·布莱德赫如此重要?我希望能和拉金谈谈这个。我也希望能问哈代这个问题。我重读了哈代的其他小说,以及哈代两位妻子的信件。我整日阅读那些角色仅在我脑海中交汇的小说;我阅读那些靠着注脚联系起来的作家日记和传记。我不常与家庭以外的人见面;除了一个朋友,我不和任何人通电话。孤立,我一次又一次被提醒,是一种危险。但如果一个人的真实语境在书中呢?有些日子,从一本书到另一本书,沉浸在那些无关紧要的想法中,我会感到一种罕见的宁静:生活中所有无法解决的事情,只要我保持距离,就都只是小事一桩。在那悬置的生活和我自己之间,是这些死去的人和想象中的角色。一个人可以终日与他们为伴,就像一个孩子在夜幕降临时,围着一圈毛绒玩具。
——
我差点丢了拉金的信件。我的包被偷了,我有半天时间心烦意乱。付了赎金后,我与拉金的信件、一本厚厚的克尔凯郭尔以及我的日记重逢了。一台电脑、一个钱包和几支笔成了别人的东西。
“侵犯隐私,”有人谈到我被偷的日记时,表示同情。然而那并非我所担心的。小偷,对他来说我的日记只是一个物质上的机会,无法侵犯我的隐私——记录在里面的争论对一个外人来说只会像布谷鸟钟一样重复。但这次中断暴露了我生活于其中的幻觉。失去日记就是失去一天与一天的连续性。失去这些书——我的这些书——就是失去对话。而对话是我时间存在的证据。我封存日记,把书放到书架上,但它们仍然是我的永恒。不像人的生命和感情,它们不是用会消失的墨水写成的。
——
在拉金的信件中,曼斯菲尔德是被提及最频繁的作者之一。在分析她的生活和爱情时,拉金是在谈论他自己。同时阅读他们两人时,我不断地提出自己的解读,为曼斯菲尔德辩护,或者不同意拉金对她的辩护。更敏锐地,我意识到我对他们的痴迷反映了我对自己所憎恶的东西:隐居、自欺,以及最重要的——那种在他人生活中为自己不确定的自我寻找庇护所的需求——那种匮乏感。对曼斯菲尔德来说,是契诃夫;对拉金来说,是曼斯菲尔德和哈代。两人都具有这样的特点:曼斯菲尔德选择了她渴望成为的人,而拉金选择了那些会宽恕他弱点的人。
当拉金寄给琼斯一本《圣灵降临节婚礼》(The Whitsun Weddings) 的预发本,却没有预先告知她里面包含一首写给另一个女人的情诗时,琼斯难以置信。拉金以他典型的闪烁其词、因而也颇能说明问题的方式回复道:
我的借口——或者如果这不是借口,而是我的回答——正如你可能预料到的那样,是完全的健忘:我毫不犹豫地把它收录进去,因为我没想过这会让你烦恼,而且它看起来足够好……我很抱歉关于《广播》(Broadcast)那首诗,我相信我的痛苦是真实的。我想我并不像大多数人那样,把诗歌和现实生活真正等同起来——我的意思是,它们在某种程度上是真实的,但经过了大量的修饰和审查。
我也不把写作和现实生活等同起来——如果被逼到角落,我会同意拉金的观点,但我无法清晰地说明现实生活是什么。“如果从来没有人读我,我还会写吗?也许不会;但我无法停止在脑海中写作,”V.S.普里切特在一封给伊丽莎白·鲍恩的信中说。当然,写作对作家来说是必不可少的,被阅读也是——我半心半意地向别人和自己重复他的信念。但事实是,直到读了普里切特的信,我才将这些必要性与作家的生活联系起来。写作是一个选项,不写作也是;被阅读是一种可能性,不被阅读也是。然而,阅读,我将其等同于现实生活:生活可以像书一样打开和合上;活着是一种选择,不活着也是。
大声说出这些话让我害怕自己又弄错了什么——不是怕别人会不同意或误读我,而是怕我越接近我想说的东西,就越偏离它。当一个词太接近那不可言说之物时,任何词都是错误的词。
我意识到,每次我与一本书对话时,我都受益于某人反对沉默的决定。尽管如此,我仍贪婪地渴求那些我被剥夺的东西:我有一个朋友,在写下一个句子之前会擦掉许多句子;另一个朋友则把她的想法留在自己心里。然而我相信,有一种真理在未表达的状态下更真实;一旦说出口,我便忧虑自己不再拥有对那份真理的主张。
那又为何要写作来困住自己?纯真——鲍恩在《心之死》中描述的那种——是我能提供的答案:
纯真总是发现自己处于错误的境地,以至于内心纯真的人学会了不真诚。找不到用自己的语言说话的方式,他们只好接受被不完美地翻译。他们独自存在;当他们试图建立关系时,他们会因为焦虑,因为渴望传递和感受温暖,而做出虚假的妥协。我们的情感体系对他们来说太腐败了。他们注定会犯错,然后被告知他们在欺骗。在爱情中,他们所能提供的甜蜜和猛烈,对那些不那么纯真的人来说,意味着成千上万次的背叛。作为世界上无法治愈的陌生人,他们从未停止索求一种英雄式的幸福。他们的单一性,他们的无情,他们持续不断的唯一愿望,使他们注定要变得残忍,并遭受残忍。
在生活中,避开纯真的人似乎是明智的。但事实上,纯真会逐渐影响一个人。我一直在想苏和波西亚。我也一直在想我的母亲。生活在人物中间更容易些——无论是别人的还是我自己的。即使是那些生命已逝的真实人物,在阅读中也变成了角色。他们永远不会察觉我的纯真。而正是出于纯真,我才写作。
我离开伦敦时,仍未对那部小说做出决定。回家后,我翻出特雷弗早先的一封信,信中询问了另一部小说。“小说怎么样了?(How is the novel?)”人们这样问,就像问候一个病人一样,而一部尚未完成的小说确实有点像那样。你写到结尾,那东西要么死了,要么状态好多了。死者应安息。
开口即错,但我仍要冒险一试
前几天晚上做梦,我又回到了北京,在我们公寓大院的入口处,那里曾经有一个黑色的转盘式公用电话,由居委会的老太太们看守着。过去我给朋友打电话时,她们总是毫不掩饰鄙夷或好奇地听着;等我打完,她们会抱怨通话时间太长,然后才把它记在她们的本子上,计算费用。那些日子里,我总要攒一堆杂事才去打电话,生怕父母注意到我离开太久。我的零花钱——都是我从午餐费里省下来的——都花在了电话费、邮票和信封上。像维多利亚时代的人物一样,我会在父母之前检查我们的邮件,截留写给我的信件。想到那个渴望与世界建立联系的热切的人——后来会变成我如今更愿意自居的隐士:每个人的青春里一定都有那么一部分,是后来不愿细看的。
在我的梦里,我要打电话。两个女人从办公室里出来。我认出了她们。在现实生活中,她们都已不在人世。“不行,”她们说,“这项服务已经取消了,因为现在人人都有手机了。”这个梦没什么特别之处——一次对过去的忧伤探访是无法控制的——只是那两个女人跟我说的是英语。
当我开始写作时,我丈夫问我是否明白我这个决定的含义。他指的不是那些实际的顾虑,尽管有很多:出版的渺茫希望,缺乏科学领域已规划好的职业确定性,更严苛的移民法规。我的许多大学同学,作为科学家,都通过国家利益豁免类别获得了绿卡。艺术家对任何国家的利益都没那么重要。
我丈夫的问题是关于语言的。我是否明白放弃我的母语意味着什么?
纳博科夫曾经回答过一个他一定听腻了的问题:“我的个人悲剧,确实不能、也不该成为任何人的事,那就是我不得不放弃我的自然语言。”然而,某事被称为悲剧,就意味着它不再是私人的了。一个人因私人的痛苦而哭泣,但只有当观众蜂拥而至,声称理解和共情时,他们才称之为悲剧。一个人的悲伤属于自己;一个人的悲剧,属于他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