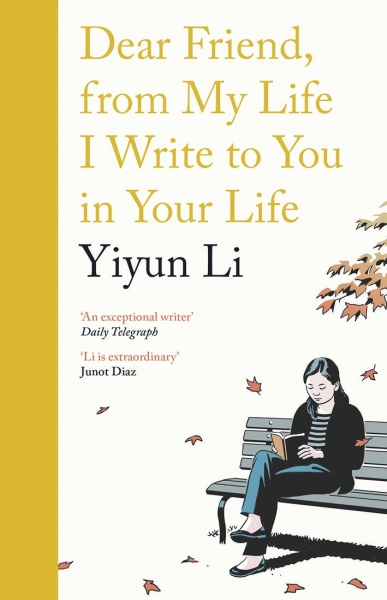我只能从那些信里回忆起几件事:他对同班邻座女孩的迷恋;他写的一部契诃夫式政治讽刺剧,主角是戈尔巴乔夫和一位东德将军,第三幕有枪响——那是1988年,共产主义仍在欧洲部分地区掌权。也正是在那一年,我们最后一次见面。
但我确实记得,在他找到艺术痴迷的出口并寄来那些能赚钱的广告之前,他曾构思、设计并命名了无数的汽车模型;此外还有各种奇特的手枪、步枪、航天器和家用电器,以及抽象图形。所有的图纸都画得一丝不苟,有时已经是第五稿或第六稿,其细节曾让我充满敬畏,也感到不耐烦。
也许我说我预料到他的自杀,不过是记忆在回头修正自己。没有理由一个有艺术天分又敏感的男孩不能成长为一个快乐的男人。他在哪里、如何出了差错,我不得而知,尽管即使在十几岁时,我就已察觉到他的沮丧——在学校,他编导的戏剧引来了嘲笑,他举办的汽车设计特别展览让他与同学疏远。他是那种需要别人来感知自己存在的人。
9.
梦想家:无论在中国还是在美国,这都是我最不想被冠上的称谓。毫无疑问,当我在北京的朋友用这个词时,她想到的是诸如坚持、专注、固执——尤其是——不切实际这些特质,她肯定在我身上看到了许多。尽管如此,一个人拥有梦想家的性格,和一个人拥有梦想,并不能保证这个人懂得如何去梦想。
在新罕布什尔州的那个女人和我,以及许多像我们一样的人,来到这个国家时目标相同——在这里开创新的生活。我不会称之为梦想,甚至不算野心。她遵循了科学家的道路,在一家生物医药公司有份稳固的工作。而我则偏离了轨道,选择了一个让隐藏变得不那么可行的职业,如果我确实是个习惯性隐藏者的话。
我不好奇如果我留在中国,生活会是怎样:不离开从来不像是我的一个选项。十年来,我所做的一切都内嵌着一个具体的“之后”。抵达美国的那一天,我将成为一个全新的人。
但也有可能,我根本不会走上写作之路。如果我一直做科学家,我会不会变得不同——更平静、更少烦恼、更明智?我会不会停止隐藏,或者变得更擅长隐藏?
10.
在我朋友自杀前几个月,他在网上找到了我。在他的邮件里,他告诉我他离婚了,我告诉他我放弃科研转而写作。他回信说:“我祝贺你。你一直是个梦想家,但美国让你的梦想成真了。”
有人在台上将我描述为美国梦的典范。当然,我也曾这样做过,把自己放在一张“之前与之后”的海报上。然而,这种转变就像贴在公交车背后的广告一样,肤浅而具有欺骗性。
时间会证明一切,人们这么说,好像时间总有最终定论。也许我只是在躲避时间,就像我一直躲避那些想对他人拥有最终发言权的人一样。
11.
如果我知道如何去梦想,我会乐意被称为梦想家。觉得自己名不副实的感觉,我知道,是很自然会发生的,而那些偶尔都没有这种感觉的人,我觉得不可信。我不介意被当作许多我并非如此的人:一个害羞的人,一个开朗的人,一个冷漠的人。但我不想被称为梦想家,因为我离真正的梦想家还差得很远。
12.
我所钦佩和尊重的梦想家特质是:对自己能力的信心,不受浮华琐事影响的定力,以及相信美好与真实终将胜利并持久的信念。梦想家身上没有任何自私、炫目或荒唐的东西;在日常生活中,他们融入人群而非脱颖而出,但这并非隐藏。一个真正的梦想家与时间相互信任。
除了觉得没资格被称为梦想家,我也可能担心被误认为是那些自称为梦想家、实则不过是野心勃勃的人。生活中常遇到这种人,他们的野心比梦想小,更世俗,需要四处宣扬,并依赖于这个特定时代的认可。如果他们给别人带来痛苦,他们会毫无困难地将那些伤害作为实现梦想的代价而一笔勾销。时效性或许是区分野心和真正梦想的一点。
13.
新罕布什尔州的那个女人既不是梦想家,也不是野心勃勃的人。她曾希望在美国郊区过上安稳平淡的生活,但孤独一定让她的生活变成了一片沙漠。
我在北京那位过世的朋友则雄心勃勃,因为他了解自己的才华;他也有梦想。我一定曾经是他梦想的一部分——否则他为何要写信,如果不是为了寻求与另一个梦想家的共鸣。
14.
我来到这个国家时,是一名有志向的免疫学家。我选择这个领域——如果不算那些实际动机,比如想要一个离开中国的理由和拥有一项谋生技能的话——是因为我喜欢免疫系统的工作理念。它的任务是探测并攻击“非我”(nonself);它有记忆,有些记忆与生命一样持久;它的记忆可能选择性地出错,或者更糟,不加区分地出错,导致系统将“自我”(self)误认为外来物,当作需要清除的东西。“免疫”(immune)这个词(源自拉丁语immunis,in- “免除” + munia “服务,义务”)是我在英语中最喜欢的词之一,拥有免疫力——对疾病、愚行、爱与孤独、烦恼思绪和无解痛苦的免疫力——这是我一直渴望赋予我的角色和我自己的特质,尽管一直都明白这种愿望的徒劳。只有毫无生机之物才能对生活免疫。
15.
人的直觉是,要对那些印证自己生活信念的人获得免疫力,也要对那些将自己信念化为乌有的人获得免疫力。后者是我们心灵的天敌,前者则被我们树为敌人,因为我们与其他物种不同,不仅能够壮大,也能够贬低我们那岌岌可危的自我。
16.
刚开始写这些文字时,我曾有过一个想法,认为这会是一种检验——一种剖析——关于时间的想法的方式。甚至曾设想过一个“之后”,那时我的困惑都会被理清。
科学中的分析检验(assay)是无尽探索的一部分。一个问题引出另一个问题;后续的结果证实或否定之前的假设。当时间本身仍未安定、难以捉摸时,去剖析自己关于时间的想法,感觉是徒劳的。正如一个人刚要理解时间的某个方面,它就呈现出另一个方面来颠覆你的推理。
在挣扎中书写挣扎:人必须抱着希望,相信这混沌总有一天会结束。
17.
“但是你还想要什么呢?你有家庭、职业、房子、车子、朋友,在世界上也有一席之地。你为什么不能快乐?为什么不能坚强?”问这些问题的,除了别人,还有我母亲。
在我住的第二家医院里,有一位气度不凡的心理健康工作者,她来上班时总是涂着完美的口红,顶着亮泽的卷发,穿着颜色鲜亮的衬衫和平底鞋,色彩搭配协调。
“年轻女士,”她每次见到我都会说,“别丢了你的笑容。”
我曾喜欢她,在她质疑我的精神生活后也依然喜欢她。我看得出,我那无神论的精神状态让她担忧,而我的顺从让我成了一个好项目。“别理她,”我的室友,一位黑人佛教徒说,“她有福音派背景。”“我不会的,”我向室友保证,“被人说教并不会烦扰我。”
然后有一天,我过得很艰难。晚餐时,那位气度不凡的女士问:“年轻女士,你今天为什么哭了?”
“我很难过,”我说。
“我们知道你难过。我想知道的是,是什么让你难过?”
“难道我就不能一个人待在我的悲伤里吗?”我说。餐桌旁的女士们对着自己的盘子微笑。好女孩在发脾气呢。
18.
是什么让你难过?是什么让你生气?是什么让你忘记了生活中的美好和你对别人的责任?人躲避那些问这些无法回答问题的人,结果只是为了自己一遍又一遍地问自己这些问题。
“我知道你不喜欢我问你来这里的原因,”我的室友说,“但你能描述一下你的感受吗?”我找不到词语来形容我的感受。
我换过好几个室友——又是一扇旋转门——但我喜欢最后一个。她在一个中产阶级非洲裔美国家庭长大,是兄弟姐妹中唯一被收养的孩子。她为爱结婚,但在婚礼当天,她意识到自己犯了一生中最大的错误。“整个第一支舞,他一次都没看我,”她说,“他看着每个客人的脸,确保他们知道这是他的秀场。”
她告诉我这个故事时,她丈夫已经因糖尿病卧病在床并且失明。她和一个护士一起照顾他。她陪他看特纳经典电影频道(TCM),因为他还记得老电影里的对白。尽管如此,她说她仍然生气,因为他们生活中的一切都围绕着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