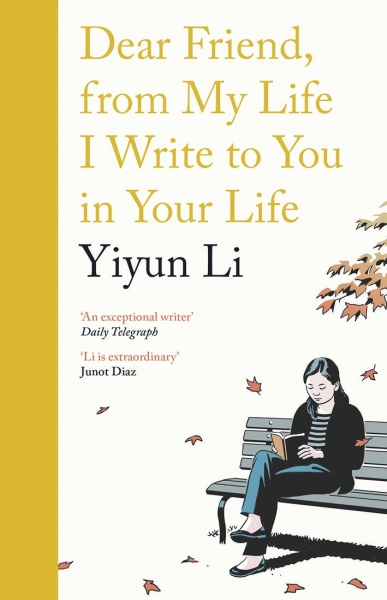再次住院后读到这段话时,我羡慕拉金。我的生活暂停了。有诊断需要应对,有药物和方案需要执行,有医院工作人员需要汇报,但它们的存在只是为了排除一个选项。取而代之的是什么,我看不到,但这也不是任何人能力范围内可以回答的。拿走比给予更容易。给予需要理解和想象力;拿走只需要决心和行动。
逃避痛苦的愿望是自私的吗?对于自杀,人们是这样认为的。但即使是没那么极端的逃避,也会在他人的生活中留下创伤。《心之死》不仅是对自私的研究,也是对逃避痛苦的挣扎的研究。损害了谁,没有人想问。
这个问题更让我不安:受苦是自私的吗?
从我记事起,母亲就说我是个自私的人。如果我是信教的,我会每晚跪下祈求从这罪恶中得到救赎。没有标准可以量化自私:一个人将多少自我奉献给他人,甚至生活的哪一部分应该自己过,哪一部分应该放弃。我一生都未能证明自己不自私。
有一次,当我恳求母亲想象一下,姐姐小时候被告知是不那么漂亮、不那么聪明、因而也不那么受宠的女儿时,她会有什么感受,母亲开始哭泣。“她四岁那年,过年我给她买了件新衬衫,尽管我当时身体不舒服没法去商店,”她说。“你怎么能说我亏待了她?”我的孩子们出生后,母亲不止一次告诉我,我们婴儿时期她从未在夜里照看过我们。“你爸爸得起来喂你们,因为他知道我的睡眠不该被打扰,”她说这话时带着如此真诚的骄傲,让我怀疑她所做的一切是否都应该以更多的理解重新审视。她可能是我一生中遇到的极少数无可争议的纯真之人。
纯真能被称为自私吗?“纯真总是默默地呼唤保护,而我们若是保护自己远离它会明智得多:纯真就像一个失去了铃铛的哑巴麻风病人,在世间游荡,并无恶意,”格雷厄姆·格林在《沉静的美国人》中这样写奥尔登·派尔。我现在意识到,只有纯真的人才有权谴责自私,因为纯真的人不知道自己的界限在哪里结束,他人的界限从哪里开始。事实上,他们的自我没有终点。他们拥有一个完整的、一致的世界。当我们进入那个世界时,我们是入侵者;当我们退出时,我们是遗弃者;当我们不遵守纯真的规则时,我们是背叛者。
(玛丽安·摩尔的母亲难道不也是纯真的另一个形象吗?还有屠格涅夫的母亲?所有母亲在指责孩子自私时都是纯真的。)
——
一个真实的人,是开放式的,只能作为一种假设来接近。小说中的人物则被要求负责。有些人物更愿意提供一个背景。例如,简·奥斯汀小说中的年轻女性寻求幸福,当幸福因环境、机遇或愚蠢而不可得时,她们会感到痛苦。没有哪个角色比《无名的裘德》中的苏·布莱德赫更反抗这种要求了。
像拉金一样,我也痴迷于托马斯·哈代,尤其是他的最后一部小说(拉金称《裘德》“像一场街头事故”)。苏是如此语无伦次,以至于在我脑海中引发了关于可信度的问题。并非我不相信她作为一个角色的真实性——这是人们有时用来批评不太成功的角色的抱怨——而是我不相信一个角色能够达到她那样无法解释的程度。“实在太令人恼火了,不可能是个真实的人”是拉金的结论,一些传记作者提出哈代的第一任妻子是其原型。
说我们了解一个人,就是把那个人打发掉了。这有时是生活的必需。我们耗尽了时间、耐心或好奇心;或者我们自愿或不自愿地离开了那个使调查成为可能和必要的情境。一个被打发掉的人可能会变成一个角色——这取决于记忆的仁慈程度。
当角色放弃了真实性——他们的不可知性——他们就变得对读者来说真实而可知了。苏——我担心这种说法会引起混淆或误解——太过于浑浊地真实,以至于不像一个角色。她开始时不可知,结束时亦然。然而,尽管我对她感到沮丧,她却可能是我愿意竭尽全力去辩护的唯一一个小说人物。
苏的生活中有一段插曲,让人想起曼斯菲尔德生活中的一段插曲。十几岁时,曼斯菲尔德的浪漫兴趣在两兄弟之间摇摆。当她怀了其中一个的孩子后,她匆忙嫁给了一个比她大十一岁的歌手,但在婚礼当晚就离开了他,婚姻并未圆房。经历流产和康复后,她遇到了约翰·米德尔顿·默里。两人开始了一段关系,在她之前的婚姻合法解除、他们结婚之前,曾两次分手。
比曼斯菲尔德早一代的苏,在遇见裘德之前,正与一名大学生维持着柏拉图式的关系。她对裘德的态度,用拉金不耐烦的话来说,“全是那种‘不-你不能爱我-好吧-也许-如果你愿意-你可以’的调调”,被许多人,包括V.S.普里切特和拉金,解读为卖弄风情。尽管如此,我发现她的行为更加难以捉摸:她仓促地选择嫁给一个年长的男人,尽管她厌恶他以及性本身;她孩子气地坚持让裘德在她婚礼前陪她走教堂的过道,像一对已婚夫妇一样;她冲动地决定离开丈夫去找裘德,条件是他们维持没有任何身体接触的关系(后来又离开裘德,重新嫁给了她的第一任丈夫);她最终默许成为裘德的情人,却拒绝接受婚姻。这种“巨大的反复无常”,人们怀疑,正是哈代意图塑造的她性格的核心。“苏的逻辑异常复杂,似乎认为一件事在做之前可能是对的,但一旦做了就变成了错的;或者换句话说,理论上正确的事情在实践中是错误的。”
一个波西米亚式的曼斯菲尔德可以拍成一出好戏。她是那种不知疲倦地为自己创造语境的人。没有什么——她的误判,她的不可预测性,她给别人和自己造成的痛苦——会影响我们对她作为一个角色的理解,甚至可能是爱。她的日记中有许多能说明问题的细节——一闪而过的念头,啃噬的痛苦,后来会出现在她故事中的精彩句子。我最喜欢的是开销清单:大部分是日常食物的条目,但总少不了信封、信纸、邮票,有时还有电报,加起来比食物还贵。其他小开销我也喜欢读到——窗帘、鞋油、发夹、“裁缝账单”、“给杰克的安全别针”和“洗衣费(!)”。(而在弗吉尼亚·伍尔芙——她的朋友和对手——的日记里,人们读到的是茶会和午餐,很少读到开销。)
苏仍然难以理解。“我不知道他到底在做什么,”拉金对哈代为她所做的设计感到困惑。他本可以把她塑造成一个可信的角色,用她的犹豫不决和矛盾心理来吸引和挫败读者。他对待其他角色——即使是最不讨人喜欢的——都用了小说家更深思熟虑的手法。
例如,阿拉贝拉,裘德的第一任妻子。如果哈代意图让读者对她的粗俗、不诚实和冷酷感到厌恶,他也赋予了她不可否认的生命力。她没有矛盾心理,只有强烈的愿望,要在一个没什么可提供的生活中有所作为。我们看到年轻时的阿拉贝拉,练习吸着脸颊制造酒窝。小说后面,在一次与苏的相遇中,阿拉贝拉背对着门躺着,以为进屋的人是裘德,她不慌不忙地重新做出诱人的酒窝,直到苏开口说话才意识到徒劳无功。
第一版的序言以这样一句先发制人的声明结尾:“《无名的裘德》仅仅是试图赋予一系列表象或个人印象以形式和连贯性,至于它们的一致性或不和谐性,它们的持久性或短暂性等问题,则不被视为首要考虑。”这些“表象”(seemings) 实际上只与苏有关。是什么让哈代剥夺了她那种他赋予其他角色的形式和连贯性?
小说结尾,在裘德的墓旁,阿拉贝拉带着复仇般的真实谈论苏:“自从离开他的怀抱后,她从未找到安宁,而且永远也不会找到,除非她变得像他现在这样!”一个作家的残忍在于将一个真实的人流放到虚构中。她被迫放弃她的不可知性。当她反抗这种命运时,她在读者面前就毫无防御能力,读者会认为她是一个不成功的角色。
但是,当我质疑哈代的不公平时,难道我没有犯那个常见的错误,将角色与作家或他生活中的某个人混为一谈吗?人们可以用侦探般的眼光审视作家的作品和生平,寻找令人信服和引人入胜的细节。欧内斯特·海明威在给父亲的信中为自己的不忠辩护:“你很幸运,一生只爱过一个女人”;弗吉尼亚·伍尔芙在日记中对曼斯菲尔德生前和死后的嫉妒:“难道人总能得到他们应得的吗?K.M.做了什么应得这廉价的死后生活?难道我现在还在嫉妒吗?”毫不奇怪,我们不断看到作家变成角色:海明威、伍尔芙,甚至拉金,他的爱情生活被搬上了银幕。剥去了真实性,他们的名声和特质,他们内在和外在的探索,都增强了他们的角色性,构成了引人入胜的故事。读者的残忍在于将作家还原为角色。而阅读他们的日记和书信是可靠的第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