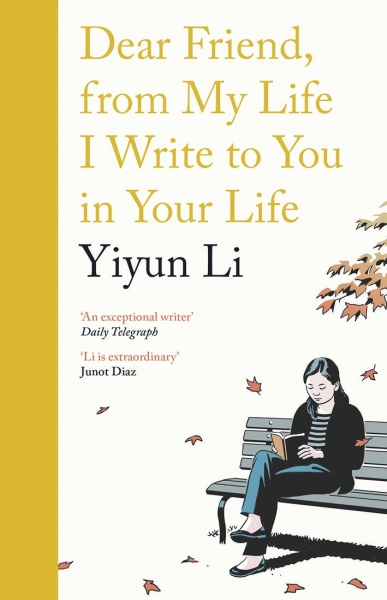在另一次旅行中——比伦敦之行晚得多——我在去吉维尼参观莫奈花园的路上,在火车站偶然遇见了波西亚。布告栏上张贴着一幅宣传展览的海报,是比利时画家西奥·凡·里斯尔伯格的《玛格丽特·凡·蒙斯肖像》:一个身着黑衣的女孩,正要打开一扇华丽的门,凝视着画外(或者她正在关上门以确保自己留在房间里——是进入而非离开?)。那个夏天肯定有成千上万的人经过那个车站,但不会有太多人认出波西亚——这幅画用作我平装版《心之死》的封面——正从一间客厅走出来:“她的每一个动作都带有一丝夸张,仿佛某种秘密的力量不断涌现出来。与此同时,她看起来很谨慎,意识到她必须生活的这个世界。她十六岁,正在失去她孩童般的高贵。”
波西亚,新近成为孤儿,被送到她同父异母的哥哥托马斯和他的妻子安娜那里生活。孤儿总是情节剧,但波西亚是最令人难以忍受的那种。她的整个自我暴露了他人无法在生活中看到与她相匹配的那种严肃性。她以一种笨拙的执着观察着世界。然而,观察并非理解;也不是保护。对波西亚来说,每一刻都是决定性的、灾难性的,而过去、现在和将来的区别,都被她那种坚持让每一刻都变得像生活通常并非的那样有意义和确定无疑所抹去。我对波西亚感到一种恼人的亲近感——我像拍苍蝇一样拍打这种想法。说“没什么要紧的”就是承认“一切都要紧”。像波西亚一样,我也在与缺乏深度感知作斗争。
“任性,”一个朋友这样评价波西亚;“任性地自私。”确实,《心之死》是对自私的研究,但伟大的小说不可避免地是对自私的研究。有些自私比其他的更司空见惯,有些更值得尊敬,或更具破坏性,或更愤世嫉俗。有波西亚的父亲,他胆怯的自私与他第一任妻子严厉的自私形成对比。(他被他精明能干的妻子排挤,在情妇怀上波西亚后娶了她。)有埃迪,他以其骄傲的自私摧毁了波西亚的生活。(埃迪,一个以受伤的纯真为核心的无赖,比一个无情的人更需要猎物。)托马斯和安娜在他们整洁的自私中寻求便利,当他们发现自己陷入波西亚的情节剧时,即使是他们冰冷、理智的自我,也无法使他们的生活恢复到只活在表面。
有些人,了解自我的界限,选择将界限之外的一切视为无关紧要而加以忽略。这种自私或许并不光彩,但当安娜承认偷看波西亚的日记时,人们不得不佩服她的诚实。“不,这一点也不奇怪:这是我常做的那种事,”她说,既无悔意,也非自辩。
波西亚和安娜,鲍恩的一位情人曾在日记中推测,是鲍恩的“两个半边”,一个拥有“童年——或天才——的天真”,另一个则是“一个外部怀有敌意的人可能会看到的样子”。鲍恩的天才在于,通过让这两个半边相互对抗,她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
鲍恩对她笔下人物的残忍与她的放纵无法区分。安娜下定决心要消除一切情感。波西亚除了希望所有人都被感情——她对他们的感情以及他们对她的感情——软化之外,别无所求。如果安娜不是如此无情地剥夺自己任何真实的联系,我们会失去对她的尊重。如果波シア不是如此坦率地付出爱——不请自来、也未曾赢得——我们会想要保护她。鲍恩操纵我们,让我们在安娜最冷酷的时候对她感受最深,并在我们站在无情世界的立场否认波西亚受苦的尊严时,暴露我们自己。
鲍恩没有留下日记或札记。也许没有幸存下来,人们不禁好奇,如果她严格地只为自己写作,会记录些什么。或许她根本没有写如此私密和暴露的东西的习惯——这是我感觉对她怀有一种对抗情绪的另一个原因。我觉得在写作时有必要与她对抗,仿佛只有通过匹敌她的所作所为,我才能保护自己免受她的影响。鲍恩在小说中摧毁了何种纯真,我就想以同样的决心去摧毁。鲍恩放纵了何种自私,我就想去放纵。鲍恩让她的角色承受了何种暴力——心理上的而非身体上的——我就想让我的角色也去施加和承受。波西亚在她最脆弱的时刻被暴露和背叛,鲍恩不允许来自他人或她自己的任何帮助;怀着同样的满足感,我对年轻时那个冬日坐在湖边心怀死念的自己也几乎没有同情。不,我站在了那些骑自行车经过她身边、怂恿她跳进水里的年轻男子一边,站在了那个走进院子把她赶走的女人一边,站在了那个看着钟、告诉她因为犹豫不决而迟到了整整多少分钟的母亲一边。
“我不知道将会发生什么;但我确实知道什么能够发生,”塞内加在一封信中写道。这句话带来的恐惧,正是我将自己写入一场对抗鲍恩的战斗的原因——不是为了对话,对话寻求理解;不是为了争论,争论是智力上的;不是出于艺术上的分歧、误解甚至嫉妒而去对抗,而是为了坚守某种本质的东西。“[我]首先是个作家,其次才是女人,”她这样评价自己。我可以轻易地断言一个更绝对的立场,即首先是个作家,然后才是个人,或者是个作家,仅此而已。鲍恩让我意识到我能够变成什么样子;她的角色让我意识到每个人都能够变成什么样子。正是这种认知让我反对她,却又把我带回她的作品。“一个人悲伤的瞬间,也就是他变得普通的瞬间,”她写道。但这还不够。一个人感觉到任何东西的瞬间,也就是他感觉到宿命的瞬间。
——
当拉金二十八岁时,将自己比作埃迪或波西亚的父亲,这一定是出于自我厌恶和自我防御的双重心理。是何种意识,何种顺从,何种被动攻击性,让他写下了那封信。
“我的生活完全是自私的,以至于无私的幻象折磨着我,”他后来写信给琼斯,再次解释他缺乏承诺的原因。
我渴望完全将自己交给另一个人。我性格的奇特之处在于,我从未感觉有过任何融合——要么我不“退位”,对方就输了;要么我退位,我就迷失了自己。一个巨大的、幼稚的利己主义外壳,我在里面悄然窒息。读到K.M.(凯瑟琳·曼斯菲尔德)与默里共享生活的梦想——这让我非常不安……与另一个人安静地、互补地生活,这将是非同寻常的——几乎不可能——我不知道,只是因为我从不为任何人做任何事,才引发了这些自我反省。
这种极端指责的反面是,一个人为他人做一切——一种我一生都熟悉的模范般的无私。它概括了我母亲的存在。退休前她是一名教师,受到一代又一代学生及其家长的尊敬,因为她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他们。我的母亲是我近距离观察到的第一个人,也许太近了,她的公众形象和私人形象几乎毫无共同之处。
如果一个人不是为别人而活,那也并不意味着他知道如何为自己而活。人们更喜欢任何知道如何为自己而活的人——无论是母亲、爱人还是朋友。这样的认知并非自私。
在将自己比作波西亚的埃迪二十二年后,拉金的处境并未好转。
我不像你那样对说真话那么有信心:不太确定我能否做到,不太确定我是否想这样做。我固守着伪装……你看得很清楚这一点,但是,我想,你把它解读为故意的、怀有敌意的欺骗。对我来说,它看起来不像那样,更像是让生活变得可以忍受。
这种让生活变得可以忍受的、令人难以忍受的努力,是贯穿拉金书信的反复出现的主题,也是支配《心之死》中托马斯和安娜生活的同样哲学。即使人们觉得这令人沮丧,也不得不为他们担忧。他们被波西亚破坏了,波西亚的每一份努力都是为了让生活变得无法忍受,除非按照她的条件来过。
拉金持续的自责和他持续为自己辩解的努力,让我觉得他过着一种情感上诚实的生活,并且很好地承受了痛苦。但这种印象一定来自于在几个月内读完他多年的信件。当然,他经历了时间,甚至忍受了它:雨中孤独的自行车骑行,独自一人烹饪难以下咽食物的夜晚,等待亨德尔音乐广播的长夜,与朋友、家人和情人的麻烦,在信件和电话中与琼斯的争吵,崩溃,伤人的沉默。
我对时间流逝(或无论这个短语意味着什么)的想法感到恐惧,无论我是否“做”了什么。在某种程度上,我可能内心深处相信,什么都不做可以作为“时间”的刹车——当然它并不能。它只是增加了什么都没做的折磨,当那个你是否做了什么都无关紧要的时刻到来时……也许你比我更自然地适应什么都不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