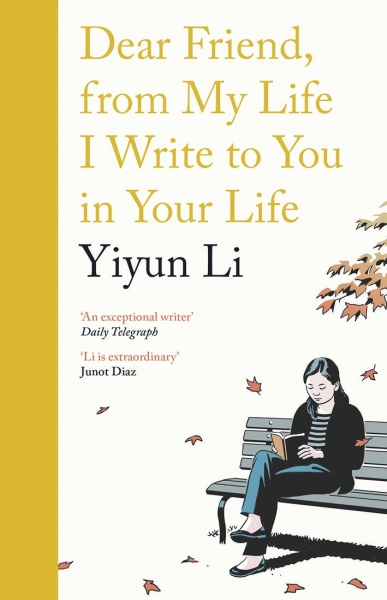伊丽莎白·毕肖普在读到迪伦·托马斯的讣告时,写信给朋友们:“这一定是真的,但我仍然无法相信……托马斯的诗歌是如此狭窄——我想,就是一条介于生与死之间的笔直通道——中间没有多少生活的空间。”在以两次住院(六月和十月)为起止的那几个月里,我常常重读那封信。一条介于生与死之间的狭窄通道——我一直相信有必要以同样的方式对待我的生活。一个人剥夺了自己的空间,是为了分配给笔下的人物;一个人与他们一同进行的那些短途旅行、分心和耽搁,是对不耐烦的一剂解药。“你对自己不耐烦,对你的工作不耐烦,对别人也不耐烦,”大约在那个时候,一个朋友对我说,“你是世界上最不耐烦的人。”
不耐烦是一种想要改变或强加的冲动。“自杀是人们很少理解的一种不耐烦,”我回复那个朋友,并引用了伊丽莎白·毕肖普的一封信来辩护。
——
高中最后一年,我有逃学的习惯,也不担心被抓住。我负责记考勤,深得老师信任,偶尔会被同学说服,记录得不那么准确。一个沉闷的冬日下午,我逃了课,在学校附近破旧的胡同里闲逛——如今这些胡同两旁林立着时髦的酒吧和精致的餐馆,迎合着外籍人士和游客。我在找一个我在报纸上读到的地方——文章说那是当时城里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此类机构。那是在电话尚未普及的年代,我也没有地图。我花了将近两个小时才找到那个地方,一个夹在居民四合院中的四合院,大门旁挂着十几个不同组织的牌子。我走进院子,看到靠墙堆着一堆煤球,另一面墙边靠着几辆自行车。一个女人从一扇门里走出来,问我要干什么。“我找‘下一代心理健康志愿者办公室’,”我说。女人重重地叹了口气。“真不敢相信,”她对屋里的人说,“又来一个这种疯孩子。”然后她转向我,说:“他们今天不在;回去过你的日子吧,别再来了。”
陌生人的冷漠与人物角色的冷漠相去不远,然而后者不会让人感到被暴露。他们对干涉我的生活毫无兴趣;他们既没有时间也没有好奇心来问我问题;他们不会把我保存在他们记忆的琥珀里。一个人除了想要这种自由——一种最接近于不存在的存在——还能从他人那里希求什么呢?
然而,冷漠者自有其力量。我一次又一次地让他们侵占我的梦境,又一次又一次地被他们从他们的世界里驱逐出去,他们对任何依恋都浑然不觉。“现在回到你真实的生活中去吧”——他们用这句话打发我,就像我过去结束与朋友的电话时,用同样的话打发自己,并以轻松的口吻加以掩饰。“你明白你存在于别人的真实生活中吗?”多年前一个朋友问我。我记得当时感到震惊——那时,唯一真实的人是我笔下的人物。当一本书完成时,为了减轻他们离去的空虚感,人们会以一种温和的方式杀死他们——如果想象这个行为带有任何暴力,那也像 lodged (盘踞) 在一个人心头角落里的自杀念头一样隐秘。写作难道不就是我演练死亡的方式吗?
我去伦敦时,曾想过要将一部小说从记录中抹去,告诉别人它无法完成,让草稿埋葬在我的电脑里。不是演练死亡,而是一次彻底的割裂。这部小说引出了我对别人的不友善和对自己的不宽容。它几乎毁掉了一段友谊。它让我质疑哪种生活——我的还是书的——更重要;也许两者都不重要。多年前,我丈夫曾告诫我,写作比科学事业要求更高。“不疯魔,不成活,”他引用了一句中国老话,但我当时拒绝将其视为障碍。如果我有写作,还有什么可怕的呢?
一个人的生活会受制于他笔下的人物吗?这种可能性似乎很荒谬,然而在我分崩离析之际,他们不再是我的盟友,没收了我一直坚决维持的写作与其余生活之间的界限,而我一直相信,其余生活就是最低限度地活着,只活在表面上,不去活。一个人无法永远维持那种介于中间的状态——活着又没有活着。我第一次希望我的生活能像我的人物一样合法,一样坚实,一样宜居。“让我变得真实,就像你对我一样真实”——这种呼喊只能指向我的人物。他们本不该看见我;那又何必让小说继续存在?我曾拒绝给予我生活中的人以真实性;那又何必让自己徘徊不去?
“当你拥有你所爱的人时,你怎么会想到自杀?你怎么会忘记那些爱你的人?”这些问题被一再问起。但质疑爱是错误的。一个人不会强迫自己去爱;一个人也不会因为停止去爱而自杀。困难在于爱会抹去:一个人变得越模糊,就越容易去爱。
回想起来,我的困惑很清晰:我低估了自己对欲求任何东西的厌恶;我高估了自己一无所求的能力。
——
在伦敦的一个下午,我给特雷弗打了个电话。他告诉我一直困扰他的脊椎疼痛。“别把你的同情浪费在我身上,”他说,“我是个老人了。”然后他问起那部小说。“快写完了,”我撒了谎,他则主张让作品顺其自然,不要流连。
第二天,我去了大英博物馆,那总是一个在生者与逝者之间迷失自我的可靠去处。之后,在离博物馆不远的一家书店,我买了一本《致莫妮卡的信》(Letters to Monica),这是菲利普·拉金写给莫妮卡·琼斯的信件选集,时间跨度近四十年。就像凯瑟琳·曼斯菲尔德一样,当初我在一家二手书店买下她的笔记,进入她的世界只是为了分散自己的注意力,我拿起这本信集也是因为拉金和琼斯在当时与我毫不相干。
我在书店咖啡馆一直坐到打烊。在一封早期的信中,拉金将琼斯一封尖刻的信比作曼斯菲尔德写给一个名叫弗雷德里克·古德伊尔的年轻人的一封信,那封信“仁慈地未曾寄出”。信的开头,她告诉古德伊尔他误把她当作可能的姘妇,几行之后,笔锋一转,亲切幽默地描述了她在法国一处别墅的一天,最后请求他再写信来,并署名“带着我‘严格相对’的爱 ‘K.M.’”。
曼斯菲尔德的信本该只是拉金通信中的一个注脚——人们总是把它们划下来,想着以后再查,却很少真的去做——若非那个奇怪的巧合:前一天我刚在曼斯菲尔德的日记里读到了这封信的草稿。那语气是如此激烈,以至于我在页边空白处写道:怎么回事?!(这封信也收录在曼斯菲尔德的《书信选》中,并未注明是否寄出。拉金相信它被仁慈地未曾寄出,这个想法很吸引人。)
未寄出的信带有一种残忍。信件被写下时,是作为两个人共享的空间;通过不寄出它,写信人获得了同时将收信人纳入和排除在外的权力。出于怯懦或控制欲,以关怀或审慎之名行事。未寄出的信永远不该被写下。但是,一封未寄出的信和一封未写出的信又有什么区别呢?真相早已存在。自我施加的沉默也在说话,尽管不是为了交流,而是为了惩罚。
——
在写给琼斯的同一封信中,为了证明自己不可信赖,拉金声称,比起她构建的“良好形象”,他更像是“波西亚的埃迪——甚至波西亚的父亲”。埃迪、波西亚和她的父亲都出自伊丽莎白·鲍恩的小说《心之死》(The Death of the Heart)。这个提及令人吃惊。我正考虑放弃的那部小说,就是与鲍恩的小说对话而写的。(关于这部命运多舛的小说,为数不多的美好回忆之一:我在洛杉矶一个地下室里,接受一位电台采访者的访问,他因阅读过多而双眼布满血丝。“在我们进录音棚之前,我必须问这个问题,”他说,手里拿着一本旧版的《心之死》,“你写你的小说时,脑子里想着这本书吗?”他是唯一一个注意到这种联系的人。)
但称我的小说是与鲍恩的书对话并不准确,因为这部小说是一场反对话,是以一种竞争、一种对抗的方式写成的,却又自始至终完全笼罩在《心之死》的魔咒之下。要清晰地阐述这一点,需要我几乎不愿付出的诚实。尽管逃避很少带来快乐;但必须承认,如果能精确地剖析某事,包括剖析自己,会有一种快乐之感。(在大学和作为年轻科学家时,我最喜欢的任务是那些边缘活动:剥离一切,只留下昆虫完整的神经系统;从小鼠股骨中收集骨髓,直到骨头变得近乎透明;小心地冲洗小鼠的肺部。也许我作为科学家的缺陷,即缺乏终极目标,正是我热爱写作的原因。精确性比最终结果更能给我带来乐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