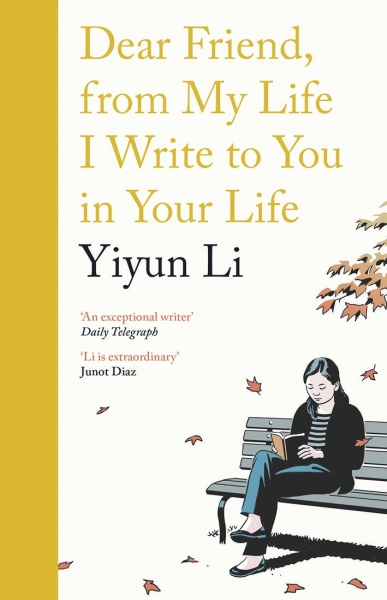我十岁的时候,曾下决心要背诵那些姓李的大诗人的诗。有对李白的浪漫狂热;有从帝王沦为阶下囚的李煜的忧郁低吟;有李清照,中国历史上记载的为数不多的非妓女身份的女词人之一;有李冶,一位以与数位诗人有风流韵事而闻名的道姑。然后还有两位我完全不懂的唐代诗人:李商隐和李贺,都以其用典晦涩著称。我现在意识到,吸引我去读他们作品的,正是他们的不可读性。李商隐在形式上极其考究,格律韵脚无可挑剔,遣词造句煞费苦心,华丽的意象和密集的隐喻串联成难以破解的珠玑;李贺在形式上较少受约束,但他的诗同样晦涩难懂。能够引述——常常只是对自己——那些连身边大多数成年人都不懂的两位诗人的诗句,这是一种孩子气的复仇般的快乐。
作为一个经验更丰富、胆量也小了一些的读者,我在阅读摩尔时会想,一个人是否有权利在不理解的情况下声称与之有联系。摩尔的书信和她的诗歌一样令人费解。读她就像在黑暗中艰难跋涉于冰封的雪原。尽管她的话语似乎是出于交流的愿望而写下的,但它们合在一起却呈现出一种令人沮丧的晦涩。一个人,在真诚地试图传达重要的事情时,怎么会让自己变得如此不可知?摩尔的传记作者——直到读完书信后我才读她的书——也提到了类似的挫败感。
一个作家的书信常常展现出一种透明性,一种自然流畅,即使是最具自传性的作品也无法比拟。在一封写给福楼拜的信中,那个极少离开家园的福楼拜,屠格涅夫写道:
老年,我亲爱的朋友,是一片巨大的、沉闷的乌云,笼罩着未来、现在,甚至还有过去,它让过去更加忧郁,像给旧瓷器蒙上一层细密的裂纹一样覆盖着我们的记忆。(恐怕我表达得不好,但没关系。)我们必须抵御这片乌云!我觉得你做得还不够。事实上,我觉得一次俄罗斯之行,我们俩一起去,会对你有好处。
在发出这个劝告之后,屠格涅夫写到了他最近在俄罗斯进行的一次为期四天的旅行。信中所描绘的乡村风光与《罗亭》或《父与子》中描述的并无太大不同,观察者的感受也曾被他的角色们感受到。(“从中出来,仿佛浸泡在某种恢复活力的浴池里。然后人又继续过日常的生活。”)尽管如此,通过屠格涅夫的眼睛而非他角色的眼睛来看待这一切,读他为福楼拜的心眼重塑这番景象,带来一种奇特的满足感,不仅仅是偷听的快感。这里多了一重观看的框架,即为匿名他人所写的文字与为个人联系所写的文字之间的差异。
在他的书信中,屠格涅夫放弃了对他笔下人物那种超然的审视,倾向于夸张和戏剧化。凯瑟琳·曼斯菲尔德在她短篇小说中那种冷静、有时甚至残酷的掌控力,与她书信中那种奔放不羁形成了鲜明对比。海明威,在其小说中对每个词及其分量都精确把握,但在他的通信中却可能显得喋喋不休。(有一次,被他在一件小小的金钱事务上的反复唠叨逗乐又惹恼,我在页边空白处写道:拿出点海明威的样子来!)作家们发表的作品与私人文字之间的反差让人对他们产生某种感觉,但摩尔的诗歌和书信同样晦涩,对任何人的好奇心都关上了一扇门。也许我读她远非反叛或强行闯入。这仅仅是为了坚持被击败。没有人比摩尔更擅长击败别人。
在一封写给她朋友威廉·卡洛斯·威廉姆斯的信中,我反复读过,摩尔写道:
事实是,我必须承认,我们通常——在某种程度上——体现了我们所痛斥的那些缺点。我在艺术上和生活中都倾向于过度,所以我抗拒任何暗示最小阻力路线是正常的……
威廉,请宽容些,拿出点仁慈来。但就友谊而言,则无需仁慈,因为友谊是我的恐惧症(phobia)。归根结底,难道不是忠诚让人变得抗拒吗?
这封信恰恰说出了我无法用言语表达的东西。听到摩尔说她倾向于过度,这不亚于读到年轻的屠格涅夫哀叹自己未老先衰。这种绝对性可能会被误认为是矫揉造作,但有些人只有走向极端才能生存。
一个作家可以否认自己是自传性的。但暴露了什么和隐藏了什么,同样都能揭示真相。从这个意义上说,精于克制的摩尔是一位高度自传性的诗人。我不知道她会对这样的评价作何反应。如果有人这样对我说,我会退缩;我会把我写下的每一个字都拿出来审视,以证明我没有让生活中的任何东西从裂缝中溜走。有一次——竟然是在北京——一个女人在一个活动上问我是否是自传性作家。“不,”我说,“绝对不是。”“但你父亲是核物理学家,”她说,“而在你的集子里,至少有两位父亲在核工业工作。”一个巧合,我试图解释,并不意味着真正的联系,尽管我现在明白,我试图将写作与生活割裂开来的努力,与摩尔的过度并无不同。一个人书写的是那些萦绕心头的东西。这样看来,没有人能免于自传性。
“如果我不擅长违约(defaulting),我早就死了。”违约什么,摩尔从未说过。即使她没有克制谈论自己,也总是抽象的。如果没有证据证明秘密的存在,一个人就能免于拥有两种生活的命运:
一种是公开的,被所有愿意了解的人看到和知晓,充满相对的真实和相对的虚假,与他朋友和熟人的生活别无二致;另一种生活则在秘密中进行。而通过某种奇怪的、或许是偶然的环境巧合,所有对他来说至关重要的、有趣的、有价值的东西,所有他真诚且不自欺的东西,所有构成他生命核心的东西,都对他人隐藏着。(契诃夫)
玛丽安·摩尔让我想起我本可能成为的样子。
——
除了大学时期,摩尔直到母亲去世都未曾与她分开居住。当她们初搬到纽约市时,一位邻居送给她们一只小猫,她们给它取名“布法罗”。“布法罗正在长大,越来越可爱了,”摩尔对这只小猫感情深厚,写信给她的哥哥。第二天,当她在图书馆上班时,她的母亲杀死了布法罗。“鼹鼠(摩尔母亲的昵称)弄来了氯仿和一个小盒子,准备好了一切,在我周一在图书馆的时候动了手……而且做得再精确不过了……但这像一把刀插在我心上,他是那么惹人怜爱,那么小心翼翼地用小爪子抓挠,那么留意我们对他的要求。”尽管如此,摩尔还是忍不住为母亲辩护。“让他长大对他来说是残忍的,而且如果我们留着他再把他交给陌生人,对他来说可能……就像谋杀。”
母女俩一起让哈德逊河带走了尸体,之后几年她们都避开那个码头。摩尔母亲运作的那套险恶逻辑我很熟悉。我姐姐大学毕业开始工作后,送给我一对仓鼠作为礼物。我很喜欢它们,但不久之后它们就消失了。“我把它们送人了,”我母亲说,“看看你对它们多痴迷。你对父母都拿不出这样的心思。”
摩尔和她哥哥把他们的母亲当作孩子对待。很久以前,在我能用语言表达这个想法之前,我就知道,我们家唯一的孩子是我母亲。比起她的愤怒,我更怕她的眼泪。
我的母亲是我必须抛在身后的一个孩子,这样才能拥有我自己的生活。我钦佩玛丽安·摩尔的哥哥。但有时行动是由仅仅是愿望的希望所驱动的;行动并不能赦免一个人的罪过,行动本身就是罪过。
我记得那些深冬的傍晚,在我做完图书管理员助理后,走向公交车站的情景。校园和车站之间是一条长长的大道,除了两端各有一盏灯外,没有照明。校园空无一人。那时的圆明园,即使在白天也是个荒凉的地方。大道两旁的白杨树在昏暗的天空中映衬出黑色的剪影,乌鸦在树顶盘旋,发出刺耳的嘈杂声。白杨树外是两条狭窄的池塘。夏天曾开出粉色和白色花朵的荷花,此刻已枯萎地躺在水面上;从那时起,我一直有种错误的印象,觉得没有什么比冬天的荷花看起来更死寂了。
我听着自己的脚步声,在脑海里默念屠格涅夫的话语,在那个凄凉的时刻,我确信一件事。我五岁时,父亲告诉我,一个人只有在另一个人在身边时才有危险。当周围没有人的时候,我是安全的;我甚至可以想象一种不同的生活。我害怕的是回到家。母亲太常对我姐姐尖叫;母亲太常因为父亲维护姐姐而受伤哭泣。被指派去平息她的情绪,安抚她的愤怒,让她恢复到孩子般快乐的样子,好让我们都能再次呼吸——这虽然可怕,却还不是最糟的。这个,我要告诉你,才是最糟的——当我读到摩尔的母亲不仅审视摩尔写的每一件东西,还日复一日地审视她的身体变化时,我感到不寒而栗——母亲太常以那种全知全能的怀疑口吻质问,公交车上是否有男人不适当地碰过我。她怎么就不明白,我已经因为早已衰老而被变得隐形了,对于那些潜伏在黑暗中的男人来说,我已经太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