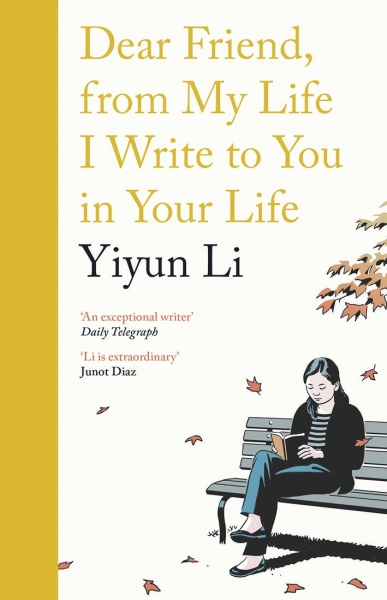但一个人无法拥有不同的人生履历。一个人无法在修正中找到慰藉。一个人无法重活十二岁,不去读屠格涅夫。电话里,我父亲以量子物理学家的神秘非逻辑和宿命论者的纯粹逻辑建议,我们应该换个角度看待我们的困境。“谁知道我们前世对别人做了什么呢,”他说,“我们现在所拥有的一切,都是我们应得的。”
我们如何带着我们所拥有的活下去,而不被萦绕?巴黎公社暴动期间,屠格涅夫写信给福楼拜:“哦,我们这些生为旁观者的人,要经历艰难的时世了。”但人并非生来就是旁观者——是他们选择成为旁观者。这是为了生存而做出的决定。
屠格涅夫终生未婚。他一生中大部分时间都爱着波琳·维亚尔多,当时一位顶尖的歌剧演唱家(“那个丑陋的吉普赛女人,”他母亲鄙夷地说),他安排自己的时间——从巴黎到巴登,到伦敦,再回到巴黎——只为靠近她。他与她的丈夫成为朋友,并与他合作翻译项目。他请求这对夫妇收养他的私生女,并以波琳的名字给她重新取名为波琳内特。当波琳的舞台生涯结束,转向创作轻歌剧时,屠格涅夫为她提供剧本。
屠格涅夫的天赋在于作一个见证者。他写给波琳和福楼拜的信中,记述了历史事件和日常琐事。他从巴黎写信描述1848年革命时观察到:“我也被那些在人群队伍中穿梭的热巧克力和小雪茄小贩们所震惊。他们贪婪、得意、漠不关心,看起来就像渔夫在拖拽一张沉甸甸的渔网。”1865年7月7日,华盛顿特区酷热的一天,玛丽·苏拉特、刘易斯·鲍威尔、大卫·赫罗尔德和乔治·阿泽罗特——参与刺杀亚伯拉罕·林肯的同谋——被处以绞刑,吸引了人群围观,一位记者也同样注意到,“监狱外,气氛则截然不同。卖蛋糕和柠檬水的小贩们正兴高采烈地兜售他们的商品。”有了安全的距离,生活便可以带着好奇心去审视——这就是旁观者的慰藉。
——
很多年里,我都随身带着威廉·特雷弗的《两种人生》(Two Lives),这是一本包含两部中篇小说的集子,《读屠格涅夫》(Reading Turgenev)和《我在翁布里亚的房子》(My House in Umbria),前者是我最喜欢的特雷弗作品。在她们虚构的现实中,两位主人公几乎没有共同之处:一位来自小镇的新教爱尔兰妇女,选择在精神病院度过三十多年;一位在翁布里亚拥有漂亮房子的英国女人,有着可疑的过去和暧昧的现在。她们之间不太可能相遇。
一个爱尔兰女人在精神病院里阅读并背诵屠格涅夫,这与在北京一所中学的图书馆里发现他,并非天差地别。人们很容易赋予在特雷弗作品中与屠格涅夫重逢的机缘巧合以意义,尽管这样做很愚蠢。联系总是可以被创造出来,形成一套人为的符号和模式系统。但生活,它抗拒阐释,也规避陈词滥调。
几次住院之后,我不再随身带着《两种人生》了。我说不清为什么。那时我只读已故作家的书。也许是为了抗拒医嘱,为了进一步孤立自己。那时我对生活中所有坚实的东西都心存疑虑。一天下午,我和小儿子坐在长椅上,等他哥哥下课。我们没有说话,像我们经常那样,但我能感觉到他把手放在我手里并一直放在那里的那种舒适感,仿佛这是世界上最自然的事情。想必是的,但我突然意识到,我不理解这一点。我可以近似地理解,但那仅仅是人类学家的理解。
——
仅仅因为传记中的相似细节而将两位作家并置,这暴露的是一个人的动机和局限。
在玛丽安·摩尔的书信中,屠格涅夫只被提到过一次。在她十八岁时,一次纽约之行(她称这次旅行为“鲸腹中的逗留”,是她首次接触到活跃于世的职业艺术家和诗人),她在一位艺术家的书柜里,注意到他的作品摆在莫里哀旁边。没有理由相信屠格涅夫的作品对摩尔有多重要。人们可以想象她会不赞成他对一个已婚女人的那种不加掩饰的迷恋。也可以想象,他对如此一个坚不可摧、正直不阿的人会感到多么沮丧。他不会像跟托尔斯泰或陀思妥耶夫斯基那样,与她好好争吵一番。
我开始读摩尔的书信,是在偶然看到她诗歌《沉默》中那句常被引用的话之后:“最深沉的感情总是显露于沉默;/ 非沉默,而是克制。” (The deepest feeling always shows itself in silence; / not in silence, but restraint.) 我一定在另一段生命里用中文写过类似的话;事实上,我知道我写过,并且曾作为这一信念的信徒生活过。当一个人放弃一个信念时,他同时使自己成为叛逆者和被弃者。
我当时正在读几位作家的书信和日记,再加一个逝者也无妨。他们的寻常琐碎,比那些闪光的思想和言辞更能抚慰我。即使是最乏味的条目或最 mundane (世俗平庸) 的通信,也都指向一个终点。我曾放弃过许多令我厌烦的小说,但我从未在中途放弃追随一位作家在书信或日记中的旅程。
然而,我并未在自己的寻常琐碎中找到慰藉。那些日子,因为没有写作而过得很慢,是以分钟来衡量的,记录在日记里,因为我想理解如何“振作自己”。一小时的哭泣可以缩短到半小时,再到十五分钟;十分钟不受打扰的阅读可以翻倍或三倍。“写小说就是要理解时间是如何流逝的,”多年前我对一位朋友说过。我当时没有意识到的是,时间也可以静止不动。对于莫泊桑的女主人公来说,十年光阴在几句话里就过去了。然而,为了通过让疯狂的笔在日记中不停移动来避开任何毁灭性的冲动,我常常发现,写了二十页之后,时钟上才勉强走过了五分钟。
在一封写给一位心灰意冷的朋友的信中,摩尔写道:
无论问题是什么,我们都必须摆脱被困的感觉——哪怕一个人只能对自己说,“若非现在,即是将来。”……如果没有任何事物能吸引或支撑我们(而我们又能获得食物和新鲜空气),那就该我们说,“若非现在,即是将来”,而不是闷闷不乐。我从未完全成功过,并且开始认为我永远也不会;尽管如此,那种自动参与的感觉,会带着人前行。
生活的自动参与:我把这个想法当作一个假的护身符紧紧抓住。我不相信将来会与现在有任何不同,但我喜欢她那句话的音韵。
——
像屠格涅夫一样,摩尔也终生未婚。他认为婚姻对艺术而言是一场灾难。她的诗歌《婚姻》开篇就称婚姻为“一种制度”和“一项事业”,但更早的时候,在她二十四岁时,在给H.D.的信中写道:“(没有所谓的审慎婚姻;)婚姻是一场十字军东征;其中总有悲剧。”
摩尔和屠格涅夫传记之间的相似之处显而易见。摩尔的母亲玛丽·华纳,在摩尔出生后不久便与丈夫分居,她丈夫余生大部分时间都在一家治疗妄想性单狂症的疗养院度过。玛丽独自抚养了摩尔和她的哥哥华纳。像屠格涅夫的哥哥一样,华纳也违背了母亲的意愿结了婚。与瓦尔瓦拉·彼得罗夫娜及其地狱般的狂怒不同,玛丽表现出了足够的宽宏大量,尽管她对儿媳几乎谈不上容忍。“我的罪过在于,虽然我为你死不足惜,但我拒绝为你而活,”华纳婚后不久写信给母亲。我常常回到这句强音(fortissimo)十足的话。不是每个生于暴虐母亲之下的孩子,都有足够的头脑清晰和力量来阐明这个决定。
我常常会花好几天的时间琢磨摩尔的话,却不能完全领会其含义,也不明白为何它们感觉如此重要。“任性本身是一种吸引人的品质,但任性未能考虑到损耗的问题,而损耗是不可避免的,”她在一封信中写道,我把这封信发给了一个朋友。“她是什么意思?”我问。
“你到底为什么读她?”朋友问。
一个人会反复阅读那些让自己感到亲近的作家——比如屠格涅夫——或者那些像D.H.劳伦斯、斯蒂芬·茨威格和罗曼·罗兰一样,在某个特定时刻闯入生活,成为个人历史一部分的作家。然而,阅读摩尔需要一种与她本人相匹配的任性。因为不理解,我只能通过继续阅读来强行进入——这是一种反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