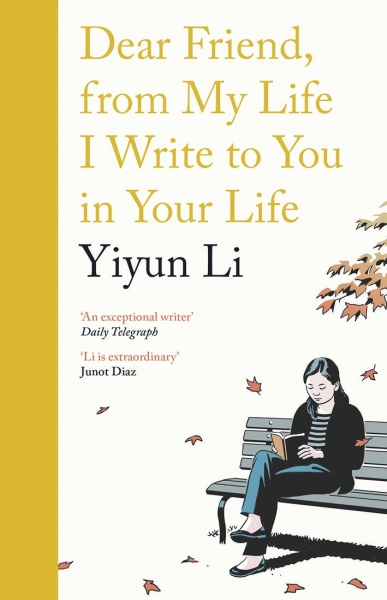这本书可以从很多方面解读——进步的、有远见的、革命性的——但我当时并不关心这些。吸引我的是永无止境的戏剧性。一个富家千金女扮男装,以便自由旅行并接受男性教育;她结识了两个年轻男子,一个是未来的中国皇帝,另一个是她未来的未婚夫。纠缠于这个爱情三角中的是时代的动荡。女主角的父亲受到政敌迫害;为了救他,她入仕为官。不出所料,她在殿试中名列第一,令人惊讶的后果是被选为驸马。她的新娘原来是她失散多年的朋友,那位朋友曾因心碎而试图自杀,后被皇帝的叔叔救下收养,并封为公主。
我当时十二岁,尽管以冷漠和书卷气著称,内心却滋生出一种情节剧倾向。我抄录并背诵书中的段落,在各种情绪下对自己引用。我深切地失落于未能与这位女诗人同时代,仿佛那样就能改变这本书的命运,甚至女诗人本人的命运。现在想来,隐身,这个我与已故作家不知疲倦地对话的前提,与我年少时渴望的越界恰恰相反。这种希望在作家的生活中找到一席之地、并改变一本书命运的愿望:必定需要勇气和天真才能去越界。
任何年轻的心灵都必须爱上一本书一次,才能学会如何阅读。幸运的是,我的迷恋被另一本书终结了,与陈端生的作品形成对比,这本书写于作者生命的尽头。我不知道是谁为图书馆购买了那本薄薄的、外观严肃的小册子——屠格涅夫的《散文诗》。没有另一本书能与之媲美,而且它很少有人借阅,以至于我违反规定,一周又一周地续借它。除了知道他是俄国人,我对屠格涅夫一无所知。只有他的文字,关于交谈的骷髅,沉思的山峦,朋友间的背叛,临刑前从容镇定的女人,作者对自己死亡的沉思,以及青春与幸福转瞬即逝的瞬间。我不知道这本书是在他写作生涯末期写就的,在此期间,他一直因背叛祖国、对进步与革命态度冷淡、以及坚持做一名非政治作家而受到批评。
当时我的心灵是易受渗透的,所以也许与屠格涅夫的相遇发生得太早了。或许,这次相遇恰逢其时,像一道安装好的闸门,不加区分地拦阻了希望与愿望。
——
一位朋友在我住院期间每天都给我打电话,出院后依然如此。有时我什么也说不出来,只是哭泣。“你必须写作,”她总是这样说。“我写不了,”我说。“你的那些人物值得活下去,”她说。“我不再关心他们了,”我说。“但我仍然关心他们,”她说。这样的对话重复了几次,然后有一天,她建议我们一起读《理智与情感》。几天后,她发来一条信息,引用了埃莉诺恳求玛丽安的话,当时玛丽安沉浸在悲痛中,不肯接受劝解:“你得振作起来。”(Exert yourself.)
可那个能让你“振作”的自我,又在哪里呢?只有在将自我排除在外之后,“振作”(或者说“用力”)的意义才向我显现。那段时间,除了照顾家人,我的生活几乎完全沉浸在阅读中。我重读了书架上屠格涅夫的所有作品:他的小说、故事、散文诗、随笔和书信,还有两本传记,其中一本是V.S.普里切特写的。(我一向偏爱小说家写的传记——比如普里切特、斯蒂芬·茨威格、罗曼·罗兰。)这种密集的阅读在我的脑海里引起了一个微小的转变。这个转变是什么,是否真实,仍有待时间去印证,但感觉上,在我与屠格涅夫漫长的相识中,我终于抵达了一个地方,能够将他视为一个来自遥远过去的人物——他所属的那个过去,以及我最初阅读他的那个过去——在北京读中学时,以及刚移民到美国时。
重读他的书信集,我发现一处酒渍,是在温哥华一家空荡荡的酒店餐厅独自用餐时留下的。饭后,我在一个昏暗的剧院里和一支爵士乐队排练。朗读时,我完全听不见自己的声音。结束后,乐队里有个人用竹笛吹奏了一支缓慢的曲子:“若你错过我搭乘的列车,你会知道我已离去;汽笛声百里之外仍可闻。”(If you miss the train I’m on, you will know that I am gone; you can hear the whistle blow a hundred miles.)
《五百里》——我十几岁时在北京第一次听到这首歌,一个同排的战友在横穿华中地区的行军途中用一支廉价的木笛吹奏过它,我从医院回来后也听过它——这首歌,如同这些记忆,如同屠格涅夫的书,如今都属于遥远的过去了。
“哦,我亲爱的托尔斯泰,要是你知道我日子过得多难,心里多苦就好了!……愿上帝让你免于体会这种感觉:生命已经逝去,同时却还未开始。”屠格涅夫在一封信中写道。他当时四十岁。他主要的几部作品大都尚未动笔。他与托尔斯泰长达数十年的争吵还未开始(第二年他给一位朋友写信说:“我已经和托尔斯泰了结了所有往来;作为一个人,他对我来说已不复存在”)。再过五年,他将遇见福楼拜——一段持续了十七年的友谊,更像是一种亲缘关系,直到福楼拜去世。
一个智力活跃、身体健康的人,说自己的生命已经结束,这要么是傲慢,要么是怯懦。《战争与和平》中,安德烈公爵在第一个妻子难产去世后,“回顾了自己的一生,得出了那个一成不变、令人慰藉又令人绝望的结论:他没有必要再开始任何事情,他只需活下去,不作恶,不焦虑,无所欲求。”他当时三十一岁,还未遇见娜塔莎,他一生的挚爱。
这不是个陌生的故事。屠格涅夫在他的青年和中年时期一直哀叹的——生命尚未开始便已逝去——正是我在学校图书馆初遇他时需要听到的。所有的孩子都需要一个体系来帮助他们停止做孩子。对我而言,那种不容置疑的宿命论就成了那个体系。想象自己回到陈端生或屠格涅夫或所有那些先我而来的人的时代,这其中有种慰藉。相信自己早已衰老,这也有好处,因为它将我从必须年轻的负担中解脱出来。还有死亡的可能性,它允许一个人绕过那些必须细致活过的人生枝节。普里切特称屠格涅夫的悲观主义是绝对的。这种绝对性——无论是悲观主义、乐观主义还是宿命论——是对抗那些萦绕心头之物的最有效防御。
——
萦绕心头的,恰如其词源所暗示的,是家。屠格涅夫的母亲瓦尔瓦拉·彼得罗夫娜以骄傲和狂怒统治着整个家庭。他的父亲,就像《初恋》里的父亲一样,为了钱财而结婚,婚姻不忠,英年早逝。伊万·屠格涅夫是两个儿子中较小的一个,也是母亲的最爱。当他的哥哥尼古拉违背母亲意愿结婚时,她切断了与他的关系,任由他靠着微薄的文员薪水挣扎着养活妻子和三个孩子。经过伊万多年努力调解哥哥和母亲的关系后,她安排孙辈们被带到圣彼得堡的街上,看了他们一眼,然后就离开了。当这三个孩子在同一年夭折时,她对尼古拉的丧子之痛依然无动于衷。
比忍受一个暴虐的父母更糟糕的,是成为那个受宠的孩子。我不知道,即使是最刻薄的父母,是否也有一个孩子,其角色就是被选中,并且当他无法以同等程度回报那份爱时,就会遭到殴打。瓦尔瓦拉·彼得罗夫娜以一种复仇式的、狂暴的热情爱着伊万。“只有我孕育了你,”当他在国外旅行时,她写信给他。“你是自私者中的自私者。我比你更了解你的性格……我预言你不会被你的妻子所爱。”
屠格涅夫成年后大部分时间都住在国外,在他母亲眼中,也在许多同胞眼中,他是个遗弃者。但是,一个人又能如何与那萦绕心头之物共存呢?“我甚至不用看你一眼就知道你的一切,因为你是我身上掉下来的肉,”我成长过程中,母亲常常这样说。
——
读到关于一个充满愤怒和占有欲的母亲的故事,我会不寒而栗。并非所有母亲都如此——这个想法越来越成为我的慰藉。有陈端生的母亲,在那个认为教育有损女性美德的时代,将两个女儿培养成了诗人。看到约翰·麦克加恩葬在他母亲旁边,也令人安心。当我见到一位朋友的父母时,尽管理论上我明白,但看到他们之间那种自然的亲近,还是觉得非同寻常。而我竟觉得这非同寻常,这个事实本身让事后我哭了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