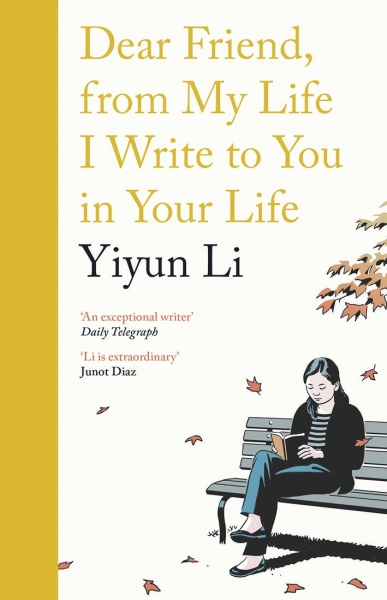在无法与物品和记忆割舍的父母抚养下长大的孩子,会变成什么样?有形的物品也会固化记忆。我在想,我父亲对细小旧物的执着,与我母亲毫无节制的脆弱和残酷之间,是否存在类似的情节剧。“空无”——不执着于任何事物,不保留任何事物——曾是情节剧的避难所,直到它不再是为止。
我到爱荷华城参加一个朗读会,麦克弗森请我到他家吃晚饭。他在一张咖啡桌上摆好了盘子、银器、新餐巾、杯子和酒,并让一个朋友从餐馆带来了食物。晚饭时,他谈了很多关于他生活的事情,有些我知道,有些是我从他身边的人那里听说的。谈话似乎可以永远进行下去,我则不停地看时间。离开前,他问我第二天能否再来,我说不行,因为我一大早要飞芝加哥。
就在那时,我第一次看到他的眼泪。我认识麦克弗森时,他的人生阶段与潘凯克认识他时不同,我从未试图将我认识的这个人与他巅峰时期的作家联系起来。有一次,他借给我一本书,我在最后一页空白处看到潦草地记着与拉尔夫·埃里森的一段对话。我没有问他,他觉得必须记住的是什么。这些年来,我一直唠叨他的健康问题,当他心情好时,他会像个受了责备却不合作的孩子,但我仍感觉到我们之间有距离。我过去常常向自己解释,这是我的羞怯和他的南方礼仪造成的——他总是称我为“李女士”。但我现在怀疑,我只是假装存在距离,就像他当初拒收潘凯克的包裹一样。我想相信,我通过他的作品已经足够了解麦克弗森。当一个人理解另一个人时,也许了解本身不再重要,或者说,它重要到让人无法承受。
晚饭时有一刻,我觉得我能看到许多尚未发生的事情:麦克弗森的未来,他健康的恶化,他的孤独,以及他日渐增多的沉默;还有我自己的未来。麦克弗森如今不为人所熟知,并且大体上已被遗忘,这并不奇怪。他一生都在反抗别人想把他塑造成的样子——一个顺从的农奴,一个政治斗士。他的拒绝,在任何时代、任何国家,都将是一场徒劳的战斗。
当未来过早地变成记忆时,人会感到失衡。那天晚上我逃跑了,因为我不想让麦克弗森看到我的惊慌失措。第二天,我打电话给一个朋友,问她,他是如何做到不自杀而活下来的。这是个可怕的问题,但我当时无法说出口的是:一个人如何能阻止自己在死亡带来的平静中寻求慰藉?我和麦克弗森共进晚餐时放纵过这种想法,就像我曾在不同时候希望我父亲也能得到那种解脱一样。放弃自己的生命,和放弃对所爱之人的希望,哪个更不可原谅?
对任何人来说,看着亲近的人受苦都是困难的。悲伤源于不理解痛苦,也源于知道痛苦即使结束了,仍会作为记忆存活下去。一个孩子不会,也不应该理解父母的记忆,然而这种不理解并不能提供豁免。我们每个人内心的那个孩子,都承载着记忆情节剧的重负,不仅是我们自己的,还有我们时代之前的那些。
“事情本不该是这样的,”拉尔夫·埃里森,被他的时代所伤,对麦克弗森说。麦克弗森肯定也对自己说过这话。那样的失望必定源于被理解的希望。我已经逃离了它,逃向我的虚无,我的宿命论,以及我坚持的无足轻重。然而,我从未有过片刻犹豫去阅读茨威格或曼斯菲尔德或其他作家。在这些情况下,人是受到保护的。他们的记忆永远不会变成我的。
写作的不足之处,类似于与人连接的不足之处。故事必须让其情节剧与读者的情节剧相遇,这至关重要,然而情节剧使得这样的相遇变得稀少。
“菲尔·奥克斯上吊自杀了。布里斯·潘凯克开枪自杀了。我们其余的人,如果足够幸运,无法想象如此极端的反抗行为,就设法忍耐下去,”麦克弗森在他的前言结尾写道。这样的仁慈,人不能不注意到;与曼的冷酷判断形成鲜明对比。我从未问过麦克弗森是否有过自杀的念头。我从未问过他是如何设法忍耐的。但这不重要:我必须活在我自己的警世故事里。有些人在故事中寻求胜利,有些人寻求逃避,还有些人寻求平静。我仍然不知道我想从我的故事中得到什么,但人总希望,接受暂时的无知,好过接受虚无。
两种人生
直到一位采访者问我,是否有一本书,因为读得太早而从此萦绕于心,我才意识到自己从未使用过“萦绕”(haunt)这个词,我觉得这个词令人幽闭而虚伪。我也不知道“haunt”这个词与“家”(home)有关。从词源学上看,它来自中古英语的“hauten”(居住,栖息,使用,雇用),源自古法语的“hanter”(居住,常去,常到某处),再源自古诺尔斯语的“heimta”(带回家,取回)。当我们感觉被萦绕时,我们体验到的是旧家的牵引力,但更令人不安的可能性是,过去已变得无家可归,而我们在现在为它提供了一个栖息之所。
我告诉采访者,有一本书,我或许读得太早,尽管我绝不会称之为“萦绕”。
一本我读得太早的书:回答这个问题需要梳理记忆——人做这件事时,总是害怕不准确。我上中学时,父亲开始清晨慢跑,在我去公交车站前就离开家,只比我早几步。我花了三十年不去回想,才明白我曾以为是他的锻炼习惯,其实是一位父亲的策略。六点半,我们公寓和公交车站之间的路对一个孩子来说并非最安全的地方。他从不徘徊,但有时公交车来得早,他会比我先到车站,挡着车门,好让车不至于不等我就开走。
乘车二十分钟后,我在另一个站换乘。几个同学也在那里等车——那是一段更长的路程,把我们带到城市边缘,我们的学校就建在圆明园的土地上,那里当时是一片废墟和荒野。中学第一周,一个女孩和她父亲跑向一辆刚刚进站的公交车。我们都看着父亲挡着车门,催促女孩上车。“你们怎么没上车?”他事后问道——我们谁都没动。“坐错了,”我们面面相觑,最后有人回答。虽然路线号相同,但那是郊区线,永远到不了女孩的学校。
就像我父亲慢跑的记忆一样,这件事也是在我试图回答采访者的问题时才想起来的。回想起来,我能重构那位父亲的担忧、内疚和沮丧,他对我们无动于衷的失望;我能质疑我们的沉默,那并非出于恶意或冷漠,而是害怕引起不必要的注意。我们那时正从童年过渡出来。世界——而世界大体上属于成人——是个不可信赖的地方。被不确定性抓住,若再被他人注意到,会更糟糕。但不可避免地,总有那么一个时刻,人必须将自己区分开来。
对我来说,那个时刻是开学一个月后,我被选为图书管理员助理。每周两次,我和另一位学生助理要待到五点半,隔着窗户把书递给许多挣扎着递给我们写着杜威分类号纸条的手(每个学生一次可以写五个号码,允许借出一本书)。闭馆后,我们整理书架,清理掉在地上的纸条,然后就可以享受我们的特权:我们可以借两本书。
在那之前,我从未进过图书馆。我的文学启蒙包括从祖父书架上读到的中国古诗词(我曾痴迷地背诵),以及报纸上连载的小说,有中国的也有翻译的,但来源并不可靠,因为我无法持续拿到报纸。(我错过了《复活》的后半部分,因为它没有连载完,这在三年级时让我非常难过。我也错过了《大卫·科波菲尔》的主要部分,后来通过在邻居家看刚引进中国的英国迷你剧弥补了——我们家当时没有电视机。)
几个月内,我读完了文学书架(我开始称之为800类)上的所有书。书籍质量参差不齐,只能满足饥渴心灵的口味。保留下来的不多。事实上,我只记得两本书。
第一本是一部十八世纪的韵文小说《再生缘》(这个书名翻译是我自己的,未能完全抓住其精髓,但我更喜欢它,胜过电视剧改编的名字《新再生缘》)。作者陈端生出身于一个富裕的文学世家。她在十七八岁时开始创作这部书,以自娱并娱乐母亲和妹妹,两年内完成了十六卷。母亲去世后,她停笔十年,直到丈夫因政治原因被流放才重新开始写作。她四十多岁去世,留下小说未完成。另有两位作者——才华稍逊,我很快就判断出来了——续写了三卷。除了第一次阅读,我总是读到第十七卷结尾就停下。人应当忠于自己在书页上视为朋友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