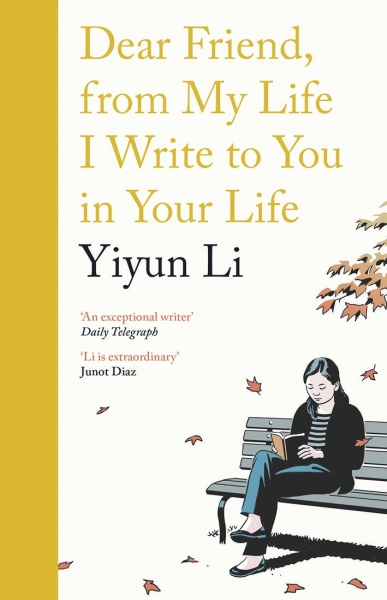与茨威格小说中的女人不同,潘凯克没有让内心的情节剧越界。他给予的比他拥有的更多,比他应该给予的更多,但他没有困住任何人。没有经历过自杀冲动的人,错过了一个关键点。并非是人想要结束自己的生命,而是结束痛苦——那场为了不让情节剧越界而进行的永恒斗争——的唯一方式,就是抹去身体。我不信任对自杀的评判——无论是曼的还是任何人的。它们归根结底,是对情感的评判。
医院里有个年轻女孩,是个大学生,在走廊里巡游,警告某种奇怪技术的入侵。她的头脑如此聪慧、知识渊博,言语充满幽默和智慧,她的告诫像希腊歌队的叠句一样富有韵律,以至于我常常带着钦佩看着她。探视时间,她母亲总是在场,有一次还带来一个和女孩一起长大的朋友。母女俩在走廊里来回走着,那个朋友跟在一步之后,无声地哭泣,任凭眼泪流淌。
在他的前言中,麦克弗森承认,在他们友谊的后期,他与潘凯克保持了距离。他好几个月都拒收潘凯克寄来的一个包裹,直到潘凯克去世的消息传来。包裹里有一件礼物,正如麦克弗森所料;还有一封信,信中潘凯克说他不等回复了——这样的话总是意味着相反的意思。两个人之间的理解,以及因此产生的疏远——麦克弗森和潘凯克之间的友谊让我心烦意乱。这是一个人的情节剧在回避另一个人的情节剧;这是一种未能获胜的沉默。
有人问我,为什么写作时不担心感觉暴露。这对我来说本该是最自然的问题,但我从未想过要问。暴露意味着一个陌生人可以通过阅读我的文字,违背我的意愿了解到我的一些事情。也许他可以,他会得出一个结论,无论对错,但这除了用外部术语来定义我之外,又能做什么呢?
外部世界对理解和感受的要求是有限的。我永远不能说我理解我的角色;我当然无权说我完全感受到了他们的感受。不过,如果我了解他们,无论多么有限,就足以让我想要更多地了解他们。还有什么比与那些对我而言未知且不可见的人们一起挣扎,是更隐秘的挣扎方式呢?我的情节剧不会越界,不会对角色造成任何伤害。在生活中,我没有那份自信。
我在想,认识是否有终点——不是说一个人已经知道了所有事情,而是说一个人知道了足够多。这种不懈的努力——我在那位与世界一同反驳自己的朋友身上看到过这种特质——保护人免受情节剧的伤害,正如理解和感受所不能做到的那样。
—
爱娃·阿尔特曼在美国一直待到1943年,然后与父母在英国团聚,后来成为一名医生。如果她在大西洋穿越中丧生,她将成为茨威格夫妇个人史和战时英国国家史中的一个注脚。“从属关系”(affiliation)一词与“子女义务”(filial)同源。一个孩子的幸运在于,她不仅仅被她与父母、她的传统、那些否定她独立未来的记忆和历史的从属关系所定义。
爱娃只是茨威格夫妇最后几年生活中的一小部分,但在阅读他们的信件时,我无法回避那个徒劳的问题:如果当初安排爱娃和他们一起生活会怎样?在信中,他们常常质疑让她到巴西和他们一起住是否更好,但几乎在每封信里,他们都试图说服自己和爱娃的父母,纽约对一个年轻女孩来说是更合适的地方。在他写给阿尔特曼夫妇的最后一封信中,也就是茨威格夫妇自杀的前一天写的(信件三天后才盖上邮戳,如同茨威格小说里的信一样,是在作者死后才收到的),斯蒂芬写道:“如果洛特的健康状况好一些,如果我们能让爱娃和我们在一起,那么继续下去才会有意义……”一个年轻的生命在身边,是否会提供一个锚点?三个月前,茨威格夫妇也曾出于极度的孤独考虑过收养一只小狗——“只是我们害怕一旦产生依恋,万一哪天我们不得不搬家或再次离开。”
作家的信件和日记赋予了她一个对抗时间侵蚀的胜利者地位,无论多么虚幻。它们也赋予读者一种亲近感的讨好感觉。当凯瑟琳·曼斯菲尔德在日记中声称她深爱契诃夫,以至于想收养一个俄国婴儿并取名安东时,她情感的透明让我尴尬。我感到一种想笑的冲动,因为我害怕在她身上辨认出哪怕一丝自己的影子。很久以后我才意识到,她当时正死于肺结核,正是这种疾病导致了契诃夫的早逝。我们对他人的钦佩和审视,反映了我们自身喜爱和憎恶的东西。
我们想了解一个陌生人的生活,能从中获得什么呢?但是,当我们阅读某人的私密文字,当我们与她一起经历她最脆弱的时刻,当她的文字比我们自己更能雄辩地表达我们的感受时,我们还能称她为陌生人吗?我说服自己,阅读信件和日记是与那些作家交谈的一种方式,但这肯定就像把细读交响乐谱等同于聆听它一样轻率。交谈需要的不仅仅是在页边空白处涂写。
有时我怀疑,我之所以被那些不与我交谈的人所吸引,是因为我尚未摆脱一种幼稚的愿望,希望他们能教我如何生活。或者,一个稍微复杂点的版本:我希望他们能教人如何死去。但他们的死亡只能以经过编辑的版本来阅读。他们的信件和日记戛然而止,被编辑巧妙而人为地操纵着。海明威书信集中收录的最后一封信是写给一个九岁男孩的,写于海明威自杀前三周,而那个男孩自己也只多活了七年。屠格涅夫在临终前写信给他关系疏远的的朋友托尔斯泰:“我给你写信,真的是为了告诉你,能与你同时代我有多么幸福,并向你表达我最后、真诚的请求。我的朋友,回到文学上来吧!”曼斯菲尔德最后的笔记,来自一个未完成的故事,结尾是一个只有垂死的曼斯菲尔德才会做出的观察:“那是精致的一天。是那种如此晴朗、如此寂静、如此无声的日子,你几乎感觉到大地本身也因自身的美丽而惊奇地停滞了。”
人人都撒谎,在写作中如同在生活中一样。令我沮丧的是,我固守着一个不切实际的信念:每个人的头脑中都有某种不可辩驳的真相,而且这个真相在信件或日记中被毫无隐瞒或歪曲地讲述出来。我的义务是寻找那个真相;找到它将给予我自身所缺乏的确定性。有了那种确定性,我将找到一种建立坚实自我的方法。这种负担,我在阅读或写作小说时从未承担过。
我阅读茨威格夫妇从南美寄来的信件,是因为我想了解他们是如何陷入最深的抑郁的。但是爱娃的故事线——如果可以称之为故事线的话——成了这种沉沦的对位。它有欢笑、平凡琐碎,甚至有些刻薄的时刻。茨威格夫妇对爱娃寄宿家庭的评论并非总是友善;他们对她在纽约州北部的寄宿学校带着欧洲式的怀疑;她通信迟缓被归咎于美国影响;他们害怕寄宿家庭永远不会把她还回来;还有一次又一次关于安排爱娃去巴西的讨论。随着他们的信件变得日益忧郁,随着他们——尤其是斯蒂芬·茨威格——越来越拒绝相信任何对自己或人类的希望,爱娃从未被包含在那份绝望中。这种豁免权,与父母希望子女免受自己曾经历的困难时的一厢情愿的想法如出一辙。然而,没有那种一厢情愿,父母又在做什么呢?不过是让自身记忆的情节剧主宰下一代的命运罢了。
—
我偶尔会收到某个只有过短暂接触的人发来的邮件。“你可能不记得我了,”这些邮件常常这样开头,那记起的希望通过已被遗忘的默认表达出来。
有时纯粹出于恶作剧,我会详细回复我们相遇的情景。人们被记起时会惊喜万分,但我对他们并不诚实。被记起,和被我的思维之网捕捉到,是有区别的。
许多年前,一个来自中国南方农民家庭的年轻人离家去一所大学学习理论物理。他是村里第一个高中毕业生。他母亲只买得起一双袜子给他,村民们凑了有限的钱给他买了一个手提箱。他带着空箱子里的一双袜子北上。到达后,大学给他提供了衣物和被褥,他立刻加入了武术队。他并非身强力壮之人,但他接下来四年都会参加比赛,为的是能吃饱饭。
最终,这个年轻人遇到并娶了那个院子里的女孩。他成了一个囤积物品的人,她成了一个囤积记忆的人。“好吧,至少,”我们可以说,没什么会被浪费或丢失,而事实上的确如此。我从小就害怕看到成堆的旧报纸积满灰尘,用过的火柴被放回火柴盒里。但更让我害怕的,是那些不属于我、却执意要被倾听和铭记,仿佛它们是唯一重要的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