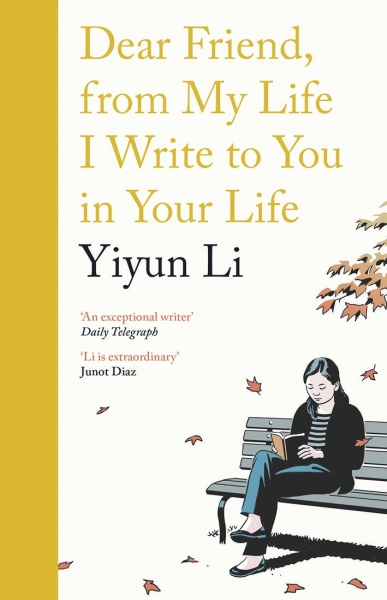在生活中,我们寻找志同道合的人,尽管——或者正因为——了解和理解的局限性。我们这样做是为了感觉不那么孤独,尽管这会带来另一种孤独。在寻找他人的过程中,我们不可避免地试图控制互动。我们坚持只被认识为我们愿意附加给自己的那个版本。迎合他人的叙述,与为我们自己修正的记忆相去不远:两者都让我们远离情感的流沙。而那些超越我们所选版本而了解我们的人——通过亲近、通过直觉、通过观察——必然会像情节剧一样在我们心中激起类似的不安。我们对情节剧的警惕是否促使我们希望逃离他们的目光,还是反过来,正是因为避免与那些比我们愿意允许的更能触及我们内心世界的人相遇,我们才能暂时感到受到自身记忆的保护?
生活的大部分复杂性在于,在许多重要的关系中,一个人扮演了不止一个角色。一个孩子,沿着街道奔跑寻找被陌生人嘲笑的疯母亲,同时也是母亲的监护人。一个父亲,谈论死亡是一种解脱,当孩子早已在同样的想法中找到慰藉时,他便在不知不觉中成了同谋。在童年之后的友谊和爱情中——它们是靠运气还是靠意志发生的?——在这些关系中,我们选择呈现不止一个自我,而伴随这些多重版本的,是适合某个版本却不适合另一个版本的记忆。有了这些相互冲突的记忆,关系便带上了情节剧的意外元素,因为没有哪个受控的叙事能免受挑战。共享的记忆可能变成被回避的记忆;尽管常常是被回避的记忆将一个人与另一个人连接起来。
只有在最无关紧要或受合同约束的互动中,才有可能每个人只扮演一个商定的角色,而在这些情况下,记忆可以被覆盖。一个人与一本书的关系也可能不那么复杂。书是永恒的;人只需为自己在时间中的变化负责。
扮演不止一个角色,扮演几个角色,并承受其后果,是不可避免的。人也可能走向相反的极端,而相信自己“什么都不是”曾在我看来是最合乎逻辑的生活方式。“什么都不是”意味着隐形和可替代;对他人而言“什么都不是”意味着对自己而言保持一切。“什么都不是”是与心智的自身免疫状况作斗争的一种方式,这最接近我那位朋友的沉默。然而,沉默并非情节剧,或者至少它没有呈现为情节剧。
—
斯蒂芬·茨威格近年在美国被重新发现,但对我来说,他与上世纪八十年代联系在一起,那时我还是个少年,不知疲倦地阅读他。在我最喜欢的一部中篇小说《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中,信件的收件人,一位著名的作家和风流浪子,并不认识寄信人,一个声称爱了他一生的女人。她年少时是他的邻居,看着他在女人堆里过着忙碌的生活。后来,他把她误认为妓女。她为他生下孩子,孩子死于1918年的流感大流行;她自己也濒临死亡,写下这封信,叙述她一生的爱恋。
这是一个情节剧式的故事,按情节剧通常的用法来说——它被改编成多种语言的电影并不奇怪——但茨威格通过赋予女主人公大多数人不敢面对的命运,将她从一个简单的陈词滥调中提升出来。她没有通过在绝望中寻找尊严来欺骗自己。“如此无目的的苦难,”她这样评价自己的一生,却毫无悔意。
我十四岁第一次读这篇小说时,迷恋于女主人公勇敢的忠诚。我现在看到了我当时错过的东西。与其说这是一个关于单相思的故事,不如说它是一个关于情节剧越界的故事。女人指责男人“近乎不人道的健忘”,然而遗忘的必要性恰恰是人性的。真正不人道的是女人的拒绝。她有勇气保持她的情节剧完整无缺;有冷酷将其强加于另一个人。这就是情节剧的残酷——如同自杀一样,它既不怀疑也不为其存在的权利辩护。
比起成为政治或历史动荡的受害者,更具毁灭性的是成为别人记忆的牺牲品。在小说结尾,男人不寒而栗。那么,谁活在真正的悲伤中:是那个将情节剧作为她记忆唯一形式的女人,还是那个已经并将永远被另一个人的记忆所囚禁的男人?
我对这个女人抱有不公正的偏见,因为与十六岁时不同,我现在警惕一个人的记忆可能造成的伤害。“你知道吗,我死的那一刻,你爸爸就会娶别人?”我小时候母亲常常对我低语。“你知道吗,我不能死,因为我不想让你生活在继母手下?”或者,她会被一种莫名的愤怒攫住,说我,她唯一爱的人,该遭最丑陋的死亡,因为我爱她不够。“你为什么这样诅咒我,妈妈?你为什么不阻止她诅咒,爸爸?”尽管真相是,我不想知道答案。我甚至憎恨思考这些问题——他人和世界所做的一切,不应像一个人对自己所做的那样,定义一个人。
有一种反抗只伴随着青春和缺乏经验而来,那就是拒绝接受生活的本来面目。格雷厄姆·格林在他的回忆录《逃避之路》中,追忆他六岁时看的第一部电影——一部关于厨娘变王后的默片——以及银幕外的音乐。“她的行进伴随着一位老妇人的钢琴声,但那跑调的琴弦发出的‘嗒-嗒-嗒’声,在其他旋律都褪色后,却留在了我的记忆里……我一直想写的就是那种书:崇高的浪漫故事,在青春时代以那些终将证明是幻觉的希望俘获我们,到年老时我们为了逃避悲伤的现实而再次回到它。”格林是我读过的唯一承认自己不仅欣赏情节剧,而且想写情节剧的作家。“我也是!”我在页边空白处写下。这是我唯一一次承认自己的野心,尽管是对一个死人。我可能达不到目标,但这并不重要。捕捉一个瞬间——无论是生命的,还是历史的——与其说是写作的理由,不如说是为了回头直面情节剧,去理解幻觉如何滋生幻觉,记忆如何颂扬记忆。
这次重读这篇小说,我已经忘记了——或者拒绝记起——我最初听到的音乐是什么。我尊重这位女性对记忆坚定不移的信念。我们中有多少人敢于宣称这一点?有些人,我们渴望邀请他们进入我们的记忆,有些人,我们渴望被他们邀请进入他们的记忆;有些人,我们努力与之共同创造未来的记忆。然而最终,那音乐中有某种难以承受的东西。人或许能在独处时捕捉到几个片段,或许能允许自己在某个故事或一次不经意的谈话中听到它的回声,但要与另一个人分享那情节剧,甚至要向自己完全承认它,都需要智慧和勇气。
—
布里斯·D’J·潘凯克自杀后,他的母亲请詹姆斯·艾伦·麦克弗森为他的短篇小说集写前言。潘凯克曾在上世纪七十年代于弗吉尼亚大学师从麦克弗森,两人成了朋友。麦克弗森是我在爱荷华作家工作坊的导师。
潘凯克有个习惯,给他生命中的每个人送礼物。“他喜欢给予,却从未学会接受。他从不觉得自己配得上礼物,”他母亲在给麦克弗森的信中写道。麦克弗森也同样慷慨地送礼物。有一年夏天,他送给工作坊每个学生一个会唱歌、会功夫的老鼠玩具;另一个夏天,他送给每个人一本书(托尔斯泰的《主人与仆人及其他故事》);有一个手掌大小、饰有小人像的精致时钟,他歪歪扭扭地包好,送给我们即将出生的长子;有一套《晚安,月亮》的礼品装,送给我们以麦克弗森名字命名的小儿子;还有从冯·莫尔百货公司买来的雕刻精美的盘子和昂贵的巧克力送给我们家,那家百货公司在爱荷华城,下午会有一位穿长裙的钢琴师在近乎空旷的店里弹奏肖邦。麦克弗森六十岁生日时,我和一个朋友约好在一个停车场向一位花农——我前同事的丈夫——买六十朵花。那是秋天,花季已晚,花农对这个时间点很恼火。“要是你上周来问就好了,”他说,“那时我有更好的花。”麦克弗森接受礼物时,和他一贯给予时一样慷慨。
“我一直认为,他送的礼物是一种让人远离的方式……一种将他们的注意力集中在他用自己最佳特质的原材料所创造出来的人格面具上的方式,”麦克弗森在谈到潘凯克时写道。读到这句话很难受。潘凯克总是想要给予的渴望,我很熟悉,尽管我无法在给予时不质疑自己的动机。给予与慷慨有关,还是与它带来的自私的慰藉有关?与它提供的自欺有关,当真相是一个人几乎或根本没有什么可以给予的时候?如果一个人不停地给予,有一天他是否会好到足以被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