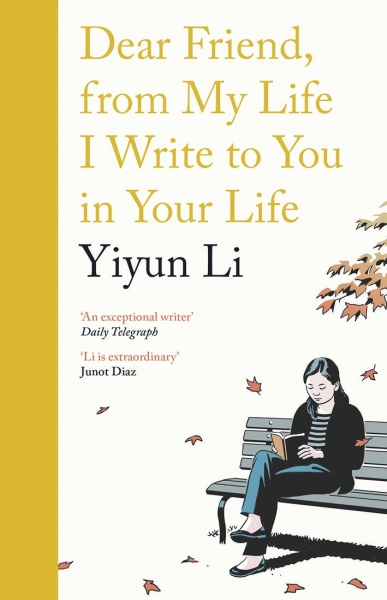华裔美国作家李翊云的回忆录《亲爱的朋友,我从我的生命里写进你的生命》Dear Friend, from My Life I Write to You in Your Life
世上并无通往世界之外的阶梯;每个世界都四顾无边。
——艾米·莉奇,《存在之物》(Things That Are)
她一向喜欢叫醒睡着的人;这确实是我们能对同伴状态做出的最大改变了,仅次于杀死他们或生下他们。
——丽贝卡·韦斯特,《这真实的夜晚》(This Real Night)
亲爱的朋友,我从我的生命里写信给你,在你的生命里
1.
我初次接触“之前与之后”(before and after)这个概念,是在一本时尚杂志里。那是我刚到美国时,朋友们让我订阅的。我如实听从了她们的建议——那时我对美国有种人类学家的迷恋。我从未见过铜版纸印刷的杂志,那印刷和纸张的质量,更不用说折页里藏着的一堆香水小样,都让我好奇这杂志是怎么盈利的,毕竟我买一本才花不到一美元。
我最喜欢的专栏在杂志最后一页,内容是名人的形象改造——比如发型和发色——用两个圆圈分别标示出“之前”和“之后”。对于改造效果,我通常没什么意见,但我喜欢这个短语的确定性,“之前”与“之后”,中间没有任何模糊不清的过渡。
在美国生活多年后,每当看到减肥项目、牙齿美白贴、生发疗程或整形手术的广告,用“之前”和“之后”来展示对比效果时,我仍会感到一阵短暂的兴奋。那种断言中的确定性——似乎每个不幸或不便的处境,都有一个解决办法让其不再是问题——既吸引我,又让我困惑。生活似乎可以重置,它好像在说;时间可以被分割。但在我看来,这种逻辑就像去另一个地方就能变成另一个人一样,不大可能。变换的风景充其量只是分散注意力,否则就是为旧习气搭了个新舞台。一个人从一个时空点带到另一个时空点,无论是地理上还是时间上,带的都是她自己。即使最多变的人,也始终如一地是她自己。
2.
我正要出门去上课,一个住在大洋彼岸新罕布什尔州的熟人打来电话到我办公室。她当时旅行到了附近一个城市。我和她通话不到两分钟,就让我丈夫去找她。他陪了她十二个小时,取消了她的商务会面,并确保她乘飞机回了家。两周后,她丈夫打来电话,说她在一个周日晚上从办公室跳了下去。他请我参加她的追悼会。我考虑了很久,决定不去。
我们的记忆与其说是关乎过去,不如说是关乎现在。过去无疑是真实的。证据不缺:照片、日记、信件、旧手提箱。但我们从浩如烟海的证据中挑选和舍弃的,是此刻合乎我们心意的部分。我们携带过去的方式有很多种:将其浪漫化,将其否定,用修改过的甚至完全虚构的记忆来装点它。而现在,却不那么容易被操纵。
我不希望现在去评判过去,所以我不想去琢磨我缺席她追悼会这件事。我们大约是同一时期来到这个国家的。当我告诉她我打算放弃科研成为一名作家时,她似乎很好奇,但她丈夫却说这是个大错特错。“你为什么非要把自己的生活弄得那么难呢?”他问。
3.
我和时间的关系一直很麻烦。过去我信不过,因为它可能已被我的记忆玷污。未来是假设,应审慎对待。现在呢——现在不就是一场持续的考验吗:在这混沌的过渡状态中,人挣扎着去理解,关于自身,哪些必须改变,哪些需要接纳,哪些应当保留。除非采取正确的行动,否则人似乎永远无法通过考验,抵达那个“之后”。
4.
经历了一段艰难时期,两次住院中的第二次之后,我去参加了一个为生活已然分崩离析的人们举办的项目。常常有人会说——哭着、颤抖着,或眼眶干涩地——他或她希望能回到过去,把一切都重新纠正过来。
我也希望生活可以重置,但能重置到何时呢?从任何一个时间点,我都可以追溯到更早的某个点:被忽视的警示信号,累积的错误,但这样做毫无用处,因为我往往最终会陷入一个暴力的愿望——希望自己从未出生。
大多数时候我都很安静,直到有人说我闪烁其词,没有进步。但我的痛苦是我的私事,我想;如果我能理解并清晰表达自己的问题,我一开始就不会在这里了。
在我没什么可说的时候,有人催促我:“你想分享些什么吗?”那时我觉得自己的希望已经耗尽。我看着旋转门送进新人,又把旧人放回外面的世界;相似的故事被讲述着,带着同样的悔恨和绝望;讲座已经是第三轮重复。如果我永远被困在那个地下室房间里怎么办?我崩溃了,能感觉到集体松了一口气:我的眼泪似乎证明,我终于打算合作了。
我本只想隐身,但无论是在那里还是别处,隐形都是一种奢侈品。
5.
我一生中总被人问:你在隐藏什么?我不知道我在隐藏什么,而我越是试图否认,人们就越觉得我不可信。我母亲过去常向客人评价我的“鬼鬼祟祟”。公共澡堂负责收费的一个女人经常质问我,问我瞒着她什么。没什么,我说,她会说她从我眼睛里就能看出我在撒谎。
沉默寡言是一种自然状态。它不是隐藏。人们不会对所有人都平等而轻易地展现自己。沉默寡言不像隐藏那样让人感到孤独,但它确实会疏远他人,让别人觉得不被重视。
6.
中国有五个时区,但全国使用统一时间——北京时间。每到整点,所有广播电台都会响起六声报时信号,随后是庄严的宣告:“刚才最后一响,是北京时间七点整。”这段记忆是可靠的,因为它不属于我个人,而属于几代中国人,属于我们亿万人:每个小时,报时信号和宣告声都通过高音喇叭在每个“人民公社”、学校、军营和住宅区放大播放。
但在这种恒定之下,时间既霸道又难以捉摸。即使在我们最私密的时刻,它也不放过我们。在我们关于生活的每一个想法和感受中,时间都占据一席之地。当我们谈论犹豫不决时,是我们不愿放开某个现在。当我们谈论继续前行(moving on)——多么意气风发的词——我们是在切断过去。而如果一个人想从时间那里寻求仁慈,它要么嘲弄地溜走,要么更糟,报以冷漠。我们中有多少人曾对别人或对自己说过:要是我能再多一点时间就好了……
7.
一个人隐藏某件事,原因有二:要么是觉得需要保护它,要么是为之感到羞耻。而且这两种可能性并非总能分开。如果我和时间的关系很麻烦,如果时间既霸道又难以捉摸,会不会是我只是在躲着时间,隐藏自己?
我过去常常从午夜写到凌晨四点。那时我有年幼的孩子,做着各种工作(从和老鼠打交道,到处理尸体组织,再到教写作),还有一个野心,就是要把写作和我的现实生活分开。当大多数人被睡眠渡过黑夜,浑然不觉时间流逝,不知天气如何时,我却感到一种奢侈,仿佛活在现实的边缘。
对于那些沉睡者来说,夜晚是抵御时间的茧。对我而言,我愿意相信,夜晚甚至更好。夜里,时间是我的财产,而非相反。
8.
2008年我回北京时,一个朋友来看我。我们聊了聊她的房产投资和我们的老同学。她离开我父母家半小时后,打来电话。她说她刚才不想当面提,但我们十几岁时关系很近的一个男孩自杀了,和他的情人一起。
我的第一反应是诧异,诧异我的朋友会等到我们彼此看不见了才告诉我。我的下一个反应仍然是诧异,好像我一直就在等着这个消息。
我们那位过世的朋友有了外遇,他和那个女人都经历了艰难的离婚,结果却被当作通奸者而受到排挤。
“他要是去了美国就好了,”我的朋友说。
“为什么?”我问。上大学时,他作为一个自学成才的设计师就已经做得很不错了。他常常在信里附上从报纸杂志剪下的广告:名牌服装、进口薄荷糖、羊绒制品。他本是在国家发展中的经济体里能过上好日子的人。
我的朋友叹了口气。“你呀,是唯一一个比他还(不切实际/理想主义)的人,”她说,“你应该知道,这个国家不适合梦想家。”
我和那个男孩的友谊,很大程度上存在于通信中。那是个不同的时代,思想和情感靠邮件传递,紧急情况靠电报传达。直到我上大学,我家才装了电话;电子邮件是很久以后,我到了美国才有的。我仍然记得那些日子,摩托车的引擎声会惊扰最宁静的夜晚——只有宣布死亡或临终消息的电报才允许这样的闯入。信件,尤其是那些贴了太多邮票的信,承载着友谊的重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