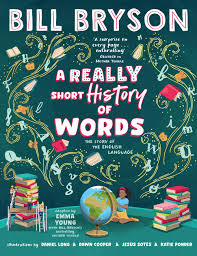然而,到了20世纪初,也就是我们故事重新开始的地方,我们距离理解这一点,或者实际上理解与遗传这一混乱事务相关的几乎任何其他事情,都还很遥远。
显然,需要一些富有灵感和巧妙的实验,幸运的是,那个时代产生了一位年轻人,他具备进行这项工作的勤奋和才能。他的名字是托马斯·亨特·摩尔根,1904年,就在孟德尔豌豆实验被及时重新发现四年后,甚至在“基因”这个词出现将近十年之前,他开始对染色体进行极其专注的研究。
染色体是在1888年偶然发现的,之所以这样命名是因为它们很容易吸收染料,因此在显微镜下很容易看到。到二十世纪初,人们强烈怀疑它们参与了性状的传递,但没有人知道它们是如何,甚至是否真的这样做的。
摩尔根选择的研究对象是一种微小的、脆弱的苍蝇,正式名称为黑腹果蝇(Drosophila melanogaster),但更常被称为果蝇(或醋蝇、香蕉蝇、垃圾蝇)。我们大多数人都熟悉果蝇,就是那种脆弱、无色的昆虫,似乎有一种强迫性的冲动要淹死在我们的饮料里。作为实验室标本,果蝇具有某些非常吸引人的优点:它们饲养和喂食成本几乎为零,可以在牛奶瓶里繁殖数百万只,从卵到具有繁殖能力的成虫只需十天或更短时间,而且只有四条染色体,这使得事情保持了方便的简单性。
摩尔根和他的团队在纽约哥伦比亚大学谢默霍恩大厅的一个小实验室(后来不可避免地被称为“果蝇室”)工作,开始了一项细致的育种和杂交计划,涉及数百万只果蝇(一位传记作者说是数十亿只,但这可能有些夸张),每只果蝇都必须用镊子捕捉,并在珠宝商的放大镜下检查,以寻找任何微小的遗传变异。六年来,他们尝试用他们能想到的任何方法来产生突变——用辐射和X射线照射果蝇,在强光和黑暗中饲养它们,在烤箱中轻轻烘烤它们,在离心机中疯狂旋转它们——但都没有成功。就在摩尔根濒临放弃之际,突然出现了一个可重复的突变——一只眼睛是白色的而不是通常的红色果蝇。有了这个突破,摩尔根和他的助手们能够产生有用的畸形,从而追踪一个性状在连续几代中的传递。通过这种方法,他们能够找出特定特征和单个染色体之间的相关性,最终或多或少地让所有人都满意地证明了染色体是遗传的核心。
然而,问题仍然存在于下一个生物学复杂性层面:神秘的基因以及构成它们的DNA。这些东西更难分离和理解。直到1933年,摩尔根因其工作获得诺贝尔奖时,许多研究人员仍然不相信基因的存在。正如摩尔根当时指出的那样,对于“基因是什么——它们是真实的还是纯粹虚构的”,尚无共识。科学家们难以接受如此基础的细胞活动物质的物理现实,这可能看起来令人惊讶,但正如华莱士、金和桑德斯在《生物学:生命的科学》(那本罕见的可读大学教科书)中指出的那样,我们今天在诸如思想和记忆等心理过程方面也处于大致相同的位置。当然,我们知道我们拥有它们,但我们不知道它们采取了什么(如果有的话)物理形式。对于基因来说,很长一段时间都是如此。认为你可以从身体里取出一个基因并带走进行研究的想法,对许多摩尔根的同辈来说,就像今天科学家们可能捕捉到一个游离的思想并在显微镜下检查它一样荒谬。
可以肯定的是,与染色体相关的某种东西正在指导细胞复制。终于,在1944年,经过十五年的努力,曼哈顿洛克菲勒研究所的一个团队,由一位才华横溢但性格内向的加拿大人奥斯瓦尔德·艾弗里领导,成功完成了一项极其棘手的实验,在该实验中,一种无害的细菌菌株通过与外源DNA杂交而变得永久具有传染性,证明了DNA远不止是一种被动分子,几乎可以肯定它是遗传的活性剂。奥地利出生的生物化学家欧文·查戈夫后来相当认真地提出,艾弗里的发现值得获得两个诺贝尔奖。
不幸的是,艾弗里遭到了他在研究所的一位同事的反对,那是一位意志坚强、令人不快的蛋白质爱好者,名叫阿尔弗雷德·米尔斯基,他竭尽全力诋毁艾弗里的工作——据说,甚至包括游说斯德哥尔摩卡罗林斯卡研究所的当局不要授予艾弗里诺贝尔奖。此时艾弗里已经六十六岁,身心俱疲。无法应对压力和争议,他辞去了职务,再也没有靠近过实验室。但其他地方的其他实验压倒性地支持了他的结论,很快,寻找DNA结构的竞赛开始了。
如果你在20世纪50年代初是个爱打赌的人,你的钱几乎肯定会押在加州理工学院的莱纳斯·鲍林身上,他是美国顶尖的化学家,有望破解DNA的结构。鲍林在确定分子结构方面无人能及,并且是X射线晶体学领域的先驱,这项技术将被证明对于窥探DNA的核心至关重要。在他极其杰出的职业生涯中,他将获得两次诺贝尔奖(1954年的化学奖和1962年的和平奖),但在DNA方面,他确信结构是三螺旋而非双螺旋,并且从未完全走上正确的轨道。相反,胜利落到了英格兰一个不太可能的四人科学家组合身上,他们并非作为一个团队工作,常常互不理睬,而且大多是该领域的新手。
四人中,最接近传统学究的是莫里斯·威尔金斯,他二战期间大部分时间都在帮助设计原子弹。另外两人,罗莎琳德·富兰克林和弗朗西斯·克里克,则在英国政府部门研究地雷度过了战争岁月——克里克研究的是会爆炸的那种,富兰克林研究的是能产煤的那种。
四人中最不循规蹈矩的是詹姆斯·沃森,一位美国神童,小时候曾作为极受欢迎的广播节目《智力竞赛小子》(The Quiz Kids)的成员而声名鹊起(因此至少可以声称是J.D.塞林格的《弗兰妮与祖伊》及其他作品中格拉斯家族某些成员的部分灵感来源),年仅十五岁就进入了芝加哥大学。他二十二岁就获得了博士学位,当时隶属于剑桥著名的卡文迪什实验室。1951年,他是个二十三岁的笨拙青年,头发异常蓬乱,照片上看起来像是正努力吸附到某个框外的强大磁铁上。
克里克,年长十二岁,当时还没有博士学位,头发不那么令人印象深刻,稍微更像穿着花呢外套。在沃森的记述中,他被描绘成一个爱吹嘘、好管闲事、乐于争论、对任何不能迅速分享想法的人不耐烦,并且经常面临被要求离开的危险的人。两人都没有接受过正规的生物化学训练。
他们的假设是,如果你能确定DNA分子的形状,你就能看到——事实证明是正确的——它是如何做它所做的事情的。他们希望通过尽可能少地做除了思考之外的工作来实现这一点,并且思考也只在绝对必要时进行。正如沃森在他自传体著作《双螺旋》中愉快地(如果有点不诚实地)评论的那样,“我希望基因可以在我不学习任何化学的情况下被解决。”他们实际上并未被指派研究DNA,并且一度被命令停止研究。沃森表面上是在掌握晶体学艺术;克里克则应该完成一篇关于大分子X射线衍射的论文。
尽管在流行记述中,克里克和沃森几乎独享了揭开DNA之谜的所有功劳,但他们的突破性进展至关重要地依赖于竞争对手所做的实验工作,而这些结果的获得,用历史学家丽莎·贾丁的委婉说法,是“偶然的”。至少在一开始,远远领先于他们的是伦敦国王学院的两位学者,威尔金斯和富兰克リン。
新西兰出生的威尔金斯是一个沉默寡言的人,几乎到了隐形的地步。1998年美国公共广播公司(PBS)一部关于DNA结构发现的纪录片——他因此与克里克和沃森分享了1962年的诺贝尔奖——竟然完全忽略了他。
所有人物中最神秘的是富兰克林。沃森在《双螺旋》中对富兰克林进行了极其不讨好的描绘,将她描绘成一个不讲道理、 secretive 、长期不合作的女人——而且这一点似乎尤其激怒了他——几乎是故意地不性感。他承认她“并非没有吸引力,如果她对衣服哪怕有一点点兴趣,可能会相当惊艳”,但在这方面她辜负了所有期望。他惊奇地注意到,她甚至不用口红,而她的着装品味“展现了英国蓝袜子少女的所有想象力”。[4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