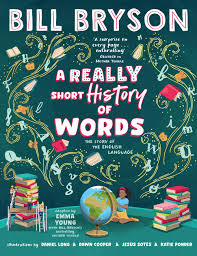根据比利时生物化学家克里斯汀·德·迪夫的说法,你拥有“大约几百种”不同类型的细胞,它们在大小和形状上差异巨大,从可以延伸数英尺的神经细胞丝到微小的盘状红细胞,再到帮助我们视觉的杆状光感受器细胞。它们的大小范围也极其广泛——在受孕时刻最为显著,当一个跳动的精子面对一个比它大八万五千倍的卵子时(这颇能让人重新审视男性征服的概念)。然而,平均来说,一个人类细胞大约宽二十微米——也就是大约百分之二毫米——这太小了以至于看不见,但足够宽敞以容纳数千个像线粒体这样的复杂结构,以及数百万数百万的分子。从最字面的意义上说,细胞的活跃程度也各不相同。你的皮肤细胞都是死的。想到你身体表面的每一寸都是已故的,这有点令人恼火。如果你是一个中等身材的成年人,你大约携带着五磅重的死皮,每天有数十亿个微小的碎片脱落。用手指划过布满灰尘的架子,你画出的图案很大程度上就是旧皮肤。
大多数活细胞很少能存活超过一个月左右,但也有一些显著的例外。肝细胞可以存活数年,尽管其内部的组成部分可能每隔几天就更新一次。脑细胞则与你同寿。你出生时大约有一千亿个脑细胞,这就是你所能得到的全部。据估计,你每小时会损失五百个,所以如果你有什么重要的思考要做,真的没有片刻可以浪费。好消息是,你脑细胞的各个组成部分会不断更新,因此,就像肝细胞一样,它们的任何部分实际上都不太可能超过一个月左右的年龄。事实上,有人提出,我们身体的任何一点——甚至连一个游离的分子——都不是九年前我们身体的一部分。虽然感觉可能不像,但在细胞层面上,我们都是年轻人。
第一个描述细胞的人是罗伯特·胡克,我们上次遇到他时,他正和艾萨克·牛顿就反平方定律的发明权争论不休。胡克在他六十八年的人生中成就斐然——他既是一位有成就的理论家,也是一位制作精巧实用仪器的能手——但他所做的任何事都没有像他1665年出版的畅销书《显微图谱:或通过放大镜制作的微小物体的一些生理描述》那样为他带来更大的赞誉。这本书向一个着迷的公众揭示了一个极其微小的宇宙,其多样性、拥挤程度和精细结构远超任何人曾经想象的程度。
胡克最早识别出的微观特征之一是植物中的小室,他称之为“细胞”(cells),因为它们让他想起了僧侣的房间(cells)。胡克计算出,一平方英寸的软木塞将包含1259,712,000个这样的小室——这是科学史上第一次出现如此巨大的数字。此时显微镜已经存在了一代人左右的时间,但胡克显微镜的与众不同之处在于其技术上的优越性。它们达到了三十倍的放大倍数,使其成为十七世纪光学技术的顶尖水平。
因此,仅仅十年后,当胡克和伦敦皇家学会的其他成员开始收到来自荷兰一位不识字的布商的图纸和报告,其放大倍数高达275倍时,这让人感到有些震惊。这位布商的名字是安东尼·范·列文虎克。尽管他几乎没有受过正规教育,也没有科学背景,但他是一位敏锐而专注的观察者,也是一位技术天才。
至今仍不清楚他是如何从简单的手持设备中获得如此惊人的放大倍数的,这些设备不过是镶嵌着微小玻璃泡的普通木销,更像是放大镜,而不是我们大多数人认为的显微镜,但实际上两者都不太像。列文虎克为他进行的每一项实验都制作了一个新仪器,并且对他的技术极其保密,尽管他有时会向英国人提供一些如何提高分辨率的建议。[40]
在长达五十年的时间里——令人瞩目的是,他开始这项工作时已经四十多岁了——他向皇家学会提交了近二百份报告,全部用低地荷兰语写成,这是他唯一掌握的语言。列文虎克没有提供任何解释,只是简单地陈述了他发现的事实,并附有精美的图画。他几乎对所有能进行有效检查的东西都提交了报告——面包霉菌、蜜蜂的蜇针、血细胞、牙齿、头发、他自己的唾液、排泄物和精液(对后两者,他带着焦急的歉意,说明其不洁的性质)——其中几乎所有东西以前从未在显微镜下见过。
1676年,他报告在一份胡椒水样本中发现了“微小动物”后,皇家学会的成员们花了一年时间,动用了英国技术所能生产出的最好的设备来寻找这些“小动物”,最终才把放大倍数调对。列文虎克发现的是原生动物。他计算出,一滴水中就有8,280,000个这些微小的生物——比荷兰的人口还多。世界以人们以前从未怀疑过的方式和数量充满了生命。
受到列文虎克奇妙发现的启发,其他人开始如此热切地凝视显微镜,以至于他们有时会发现实际上并不存在的东西。一位受人尊敬的荷兰观察家尼古拉斯·哈特索克(Nicolaus Hartsoecker)确信他在精细胞中看到了“微小的预成形人”。他称这些小生物为“小人”(homunculi),有段时间许多人相信所有人类——实际上是所有生物——都只是微小但完整的先前存在的生物的巨大膨胀版本。列文虎克本人偶尔也会因热情而得意忘形。在他最不成功的一次实验中,他试图通过近距离观察一次小爆炸来研究火药的爆炸特性;结果他差点弄瞎自己。
1683年,列文虎克发现了细菌,但这差不多就是接下来一个半世纪里所能取得的进展了,因为显微镜技术的限制。直到1831年,才有人第一次看到细胞核——发现者是苏格兰植物学家罗伯特·布朗,这位科学史上频繁出现但总是模糊不清的访客。布朗生活于1773年至1858年,他称之为“核”(nucleus),源自拉丁语nucula,意为小坚果或果仁。然而,直到1839年,才有人意识到所有生物物质都是细胞构成的。是德国人特奥多尔·施旺有了这一洞见,这不仅相对较晚,就科学洞见而言,而且起初并未被广泛接受。直到1860年代,以及法国路易·巴斯德的一些里程碑式的工作,才最终证明生命不能自发产生,而必须来自先前存在的细胞。这一信念被称为“细胞理论”,它是所有现代生物学的基础。
细胞被比作许多东西,从“复杂的化工厂”(物理学家詹姆斯·特雷菲尔语)到“广阔、拥挤的大都市”(生物化学家盖伊·布朗语)。细胞既是这两者,又都不是。它像化工厂,因为它致力于大规模的化学活动;像大都市,因为它拥挤、繁忙,充满了看似混乱随机但显然有其系统的相互作用。但它比你见过的任何城市或工厂都更像一个噩梦般的地方。首先,细胞内部没有上下之分(重力在细胞尺度上没有意义),而且没有一原子宽度的空间是未使用的。到处都有活动,还有持续不断的电能嗡鸣。你可能感觉不到自己带电,但你确实是。我们吃的食物和呼吸的氧气在细胞中结合成电能。我们之所以不会互相电击或坐在沙发上时烧焦沙发,是因为这一切都发生在微小的尺度上:仅仅0.1伏特的电压在纳米级的距离上传播。然而,如果将其放大,它将转化为每米两千万伏特的电压,大约相当于雷暴主体携带的电荷。
无论大小或形状如何,你几乎所有的细胞都基本按照相同的蓝图构建:它们有一个外壳或膜,一个细胞核(其中包含维持你生存所必需的遗传信息),以及两者之间一个繁忙的空间,称为细胞质。细胞膜并非像我们大多数人想象的那样,是一个耐用、有弹性的外壳,需要用尖针才能刺破。相反,它是由一种称为脂质的脂肪物质构成的,其稠度大约相当于“轻质机油”,引用舍温·B·努兰的话。如果这听起来出人意料地不结实,请记住,在微观层面上,事物表现不同。对于任何分子尺度的东西来说,水变成了一种重型凝胶,而脂质就像铁一样坚固。
如果你能参观一个细胞,你不会喜欢它。如果把原子放大到豌豆那么大,细胞本身就是一个直径约半英里的球体,由称为细胞骨架的复杂支架支撑。在其中,数百万数百万的物体——有些像篮球那么大,有些像汽车那么大——会像子弹一样呼啸而过。你没有地方可以站立,每秒钟都会从各个方向被撞击和撕裂数千次。即使对于其全职居住者来说,细胞内部也是一个危险的地方。平均而言,每条DNA链每8.4秒就会被化学物质和其他因素攻击或损坏一次——一天内达到一万次——这些因素会撞击或不经意地切断它,而每一个这样的伤口都必须迅速缝合,否则细胞就会死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