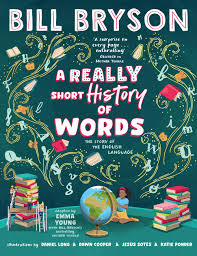在海洋中,情况也大致相同。所有的菊石都消失了,但它们的表亲鹦鹉螺,生活方式相似,却游弋了下来。在浮游生物中,一些物种几乎被消灭——例如,92%的有孔虫——而其他生物,如硅藻,结构相似,生活在一起,却相对未受损害。
这些都是难以解释的不一致之处。正如理查德·福蒂观察到的那样:“仅仅称它们为‘幸运儿’然后就此打住,似乎并不能令人满意。”如果,正如看起来完全可能的那样,这次事件之后是数月的黑暗和令人窒息的烟雾,那么许多昆虫幸存者就难以解释了。“一些昆虫,像甲虫,”福蒂指出,“可以靠木头或其他散落的东西为生。但是像蜜蜂那样靠阳光导航并需要花粉的昆虫呢?解释它们的生存就没那么容易了。”
最重要的是,还有珊瑚。珊瑚需要藻类才能生存,藻类需要阳光,两者都需要稳定的最低温度。过去几年里,关于珊瑚因海水温度仅变化一度左右而死亡的报道广受关注。如果它们对微小的变化如此脆弱,它们是如何在漫长的撞击冬季中幸存下来的?
还有许多难以解释的区域差异。南半球的灭绝似乎远没有北半球严重。特别是新西兰,似乎几乎毫发无损地度过了难关,尽管那里几乎没有穴居生物。甚至它的植被也绝大多数幸免于难,然而其他地方的火灾规模表明破坏是全球性的。简而言之,我们不知道的东西太多了。
一些动物绝对繁荣起来——包括,有点令人惊讶的是,龟类再次出现。正如弗兰纳里指出的那样,恐龙灭绝后的时期完全可以被称为龟类时代。北美有十六个物种幸存下来,另外三个物种很快就出现了。
显然,适应水生环境是有帮助的。希克苏鲁伯(KT)撞击消灭了近90%的陆地物种,但只消灭了10%生活在淡水中的物种。水显然提供了对热和火焰的保护,但在随后的贫瘠时期,可能也提供了更多的食物。所有幸存下来的陆地动物都有一个习惯,即在危险时期退回到更安全的环境——水中或地下——这两种环境都提供了相当大的庇护,以抵御外部的破坏。以腐肉为生的动物也享有优势。蜥蜴过去是,现在也是,基本上不受腐烂尸体中细菌的影响。事实上,它们常常被吸引过去,而且很长一段时间里,显然有很多腐烂的尸体。
人们常常错误地认为只有小型动物在KT事件中幸存下来。事实上,幸存者中包括鳄鱼,它们不仅体型庞大,而且比今天的鳄鱼大三倍。但总的来说,确实如此,大多数幸存者都是小型且鬼鬼祟祟的。事实上,在世界黑暗而充满敌意的时候,体型小、温血、夜行、饮食灵活、天性谨慎是完美的生存条件——这些正是我们哺乳动物祖先的特质。如果我们的进化更先进一些,我们很可能已经被消灭了。相反,哺乳动物发现自己身处一个它们比任何活着的生物都更适应的世界。
然而,这并非意味着哺乳动物蜂拥而出填补了每一个生态位。“进化可能厌恶真空,”古生物学家史蒂文·M·斯坦利写道,“但填补它往往需要很长时间。”也许长达一千万年,哺乳动物一直谨慎地保持着小型体型。在第三纪早期,如果你有山猫那么大,你就能称王称霸了。
但一旦它们开始发展,哺乳动物就大量扩张——有时甚至到了几乎荒谬的程度。有一段时间,有像犀牛一样大的豚鼠,也有像两层楼房子一样大的犀牛。无论捕食链中哪里有空缺,哺乳动物都会崛起(通常是字面意义上的)来填补它。浣熊科的早期成员迁移到南美洲,发现了一个空缺,并进化成了像熊一样大小和凶猛的生物。鸟类也同样不成比例地繁荣起来。数百万年来,一种名为泰坦鸟(Titanis)的巨型、不会飞的食肉鸟可能是北美最凶猛的生物。它无疑是有史以来最令人生畏的鸟。它高十英尺,重超过八百磅,喙可以撕下几乎任何惹恼它的东西的头。它的家族以强大的方式生存了五千万年,然而直到1963年在佛罗里达发现了一具骨架,我们才知道它曾经存在过。
这引出了我们对灭绝不确定性的另一个原因:化石记录的贫乏。我们已经提到了任何一套骨骼变成化石的可能性微乎其微,但记录实际上比你想象的还要糟糕。想想恐龙。博物馆给人的印象是我们拥有全球丰富的恐龙化石。事实上,绝大多数博物馆的展品都是人造的。伦敦自然历史博物馆入口大厅里那具巨大的梁龙骨架,它曾令几代参观者欣喜和增长见闻,就是用石膏制成的——1903年在匹兹堡建造,由安德鲁·卡内基赠送给博物馆。纽约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的入口大厅则被一个更宏伟的场景所主导:一具巨大的腕龙骨架保护着它的幼崽,抵御着一只迅猛而多齿的异特龙的攻击。这是一个令人印象深刻的展览——腕龙向高高的天花板耸立起大约三十英尺——但也完全是假的。展览中的几百块骨头每一块都是铸模。去参观世界上几乎任何大型自然历史博物馆——巴黎、维也纳、法兰克福、布宜诺斯艾利斯、墨西哥城——迎接你的将是古老的模型,而非古老的骨骼。
事实是,我们对恐龙的了解并不多。在整个恐龙时代,已确认的物种不到一千种(其中近一半仅知于单一标本),这大约是现存哺乳动物物种数量的四分之一。请记住,恐龙统治地球的时间大约是哺乳动物的三倍,所以要么恐龙在物种产生方面效率低下,要么我们几乎没有触及表面(用一个不可抗拒地恰当的陈词滥调来说)。
在恐龙时代的数百万年里,至今尚未发现任何化石。即使是晚白垩世时期——由于我们长期以来对恐龙及其灭绝的兴趣,这是被研究得最多的史前时期——所有生存过的物种中约有四分之三可能尚未被发现。比梁龙更庞大或比特暴龙更令人生畏的动物可能曾成千上万地在地球上漫游,而我们可能永远不会知道。直到最近,关于这个时期恐龙的所有已知信息仅来自大约三百个标本,代表着仅仅十六个物种。记录的稀少导致了这样一种普遍的信念,即在希克苏鲁伯撞击事件(KT事件)发生时,恐龙已经在走向灭绝的路上。
在20世纪80年代末,密尔沃基公共博物馆的古生物学家彼得·希恩决定进行一项实验。他动用了两百名志愿者,对蒙大拿州著名的地狱溪地层中一个界定清晰但也被仔细搜寻过的区域进行了辛苦地普查。志愿者们一丝不苟地筛选,收集了每一颗牙齿、每一块椎骨和骨头碎片——所有被先前挖掘者忽略的东西。这项工作耗时三年。完成后,他们发现他们将全球晚白垩世恐龙化石的总数增加了两倍多。这项调查证实,恐龙的数量一直很多,直到希克苏鲁伯撞击事件发生时。“没有理由相信恐龙在白垩纪最后三百万年里是逐渐灭绝的,”希恩报告说。
我们如此习惯于认为我们自己作为生命主导物种是不可避免的,以至于很难理解我们之所以在这里,仅仅是因为及时的地外撞击和其他随机的侥幸事件。我们与其他所有生物的共同点在于,近四十亿年来,我们的祖先每次在我们需要时,都设法从一系列正在关闭的门中溜了过去。斯蒂芬·杰伊·古尔德在一句著名的引言中简洁地表达了这一点:“人类今天之所以在这里,是因为我们特定的谱系从未断裂——在可能将我们从历史上抹去的十亿个点中,一次也没有。”
我们在本章开头提出了三点:生命想要存在;生命并非总是想要变得多么了不起;生命不时会灭绝。对此我们可以加上第四点:生命继续存在。而且常常,正如我们将看到的,它以一种绝对令人惊叹的方式继续存在。
《万物简史》
第23章:存在的丰富性
在伦敦自然历史博物馆,这里那里,建在光线不足的走廊凹处,或者矗立在矿物、鸵鸟蛋和大约一个世纪以来其他丰富杂物的玻璃柜之间,有一些秘密的门——至少在某种意义上是秘密的,因为它们没有任何吸引游客注意的地方。偶尔你可能会看到一个神情恍惚、头发有趣地桀骜不驯、标志着学者身份的人从其中一扇门出来,匆匆走过走廊,很可能又穿过稍远处另一扇门消失,但这相对罕见。大多数时候,门都关着,丝毫没有暗示它们后面存在着另一个——平行的——自然历史博物馆,其规模与公众所知并喜爱的那个一样庞大,并且在许多方面更加奇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