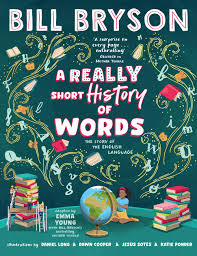不幸的是,对于兽孔目动物来说,它们的表亲双弓纲动物也在积极进化,在它们的情况下变成了恐龙(以及其他一些东西),这逐渐证明对兽孔目动物来说太强大了。由于无法与这些好斗的新生物正面竞争,兽孔目动物基本上从记录中消失了。然而,极少数进化成了小型、毛茸茸、穴居的生物,它们作为小型哺乳动物耐心等待了很长一段时间。它们中最大的也没有长过家猫,大多数不比老鼠大。最终,这将证明是它们的救赎,但它们将不得不等待近1.5亿年,直到第三个超级王朝,即恐龙时代,突然结束,为第四个超级王朝和我们自己的哺乳动物时代腾出空间。
每一次这些大规模的转变,以及期间和之后发生的许多较小的转变,都依赖于那个看似矛盾却至关重要的进步动力:灭绝。地球上物种的死亡,从最字面的意义上说,是一种生活方式,这是一个奇怪的事实。没有人知道自从生命开始以来存在过多少物种。三百亿是一个常被引用的数字,但这个数字曾被高达四万亿。无论实际总数是多少,曾经生活过的所有物种中有99.99%已不复存在。“粗略地说,”芝加哥大学的戴维·劳普喜欢说,“所有物种都灭绝了。”对于复杂生物来说,一个物种的平均寿命只有大约四百万年——大致相当于我们现在所处的位置。
灭绝对受害者来说当然总是坏消息,但对于一个充满活力的星球来说,这似乎是件好事。“灭绝的替代选择是停滞,”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的伊恩·塔特萨尔说,“而在任何领域,停滞很少是好事。”(我或许应该指出,我们这里谈论的是灭绝作为一个自然的、长期的过程。由人类粗心大意造成的灭绝则完全是另一回事。)
地球历史上的危机总是与随后的戏剧性飞跃联系在一起。埃迪卡拉动物群的衰落之后是寒武纪时期的创造性爆发。4.4亿年前的奥陶纪大灭绝清除了海洋中许多固着滤食性生物,并以某种方式创造了有利于快速游动的鱼类和巨型水生爬行动物的条件。反过来,当泥盆纪晚期的另一次大爆发再次给生命带来剧烈震荡时,这些生物处于向旱地派遣殖民者的理想位置。历史上,这种情况断断续续地发生过。如果这些事件中的大多数没有恰好在它们发生的时候、以它们发生的方式发生,我们几乎肯定不会在这里。
地球在其历史上经历了五次主要的大灭绝事件——按顺序分别是奥陶纪、泥盆纪、二叠纪、三叠纪和白垩纪——以及许多规模较小的灭绝事件。奥陶纪(4.4亿年前)和泥盆纪(3.65亿年前)各自消灭了大约80%到85%的物种。三叠纪(2.1亿年前)和白垩纪(6500万年前)各自消灭了70%到75%的物种。但真正的大灭绝是大约2.45亿年前的二叠纪大灭绝,它拉开了漫长的恐龙时代的序幕。在二叠纪,至少95%的化石记录中已知的动物消失了,再也没有回来。甚至大约三分之一的昆虫物种也消失了——这是它们唯一一次大规模消失。这是我们经历过的最接近完全灭绝的时刻。
“那真是一场大灭绝,一场地球从未经历过的规模浩大的屠杀,”理查德·福蒂说。二叠纪事件对海洋生物尤其具有毁灭性。三叶虫完全消失了。蛤蜊和海胆几乎灭绝。几乎所有其他海洋生物都遭受重创。总的来说,据认为,在陆地和水中,地球失去了52%的科——这是生命宏大等级中属之上、目之下的级别(下一章的主题)——以及可能高达96%的所有物种。这将需要很长时间——据一种估算,长达八千万年——物种总数才能恢复。
有两点需要牢记。首先,这些都只是有根据的猜测。对二叠纪末期存活的动物物种数量的估计,从低至45,000种到高达240,000种不等。如果你不知道有多少物种存活,你几乎无法有说服力地确定灭绝的比例。此外,我们谈论的是物种的死亡,而不是个体的死亡。对个体而言,死亡率可能要高得多——在许多情况下,几乎是全部。那些幸存下来进入生命彩票下一阶段的物种,几乎肯定要归功于少数伤痕累累、步履蹒跚的幸存者。
在大规模灭绝事件之间,也发生过许多规模较小、不那么为人所知的灭绝事件——亥姆菲尔期、弗拉期、法门期、兰乔拉布期以及其他十几次——这些事件对物种总数的破坏性不那么大,但常常对某些种群造成致命打击。包括马在内的食草动物在约五百万年前的亥姆菲尔期事件中几乎被消灭。马的数量减少到只剩一个物种,这个物种在化石记录中出现得如此零星,以至于表明它一度濒临灭绝。想象一下没有马、没有食草动物的人类历史。
几乎在所有情况下,无论是大的灭绝事件还是较小的灭绝事件,我们都对其原因知之甚少,简直令人困惑。即使排除了那些更古怪的观点,关于灭绝事件原因的理论仍然比实际发生的事件还要多。至少有二十多种潜在的罪魁祸首被认为是原因或主要促成因素:全球变暖、全球变冷、海平面变化、海洋缺氧(一种称为缺氧症的状况)、流行病、来自海底的巨大甲烷气体泄漏、流星和彗星撞击、被称为超级飓风的失控飓风、巨大的火山隆起、灾难性的太阳耀斑。
这最后一种可能性尤其引人入胜。没有人知道太阳耀斑能有多大,因为我们从太空时代开始才观察它们,但太阳是一个强大的引擎,其风暴也相应地巨大。一次典型的太阳耀斑——我们在地球上甚至不会注意到——将释放相当于十亿颗氢弹的能量,并向太空抛出约一千亿吨致命的高能粒子。磁层和大气层通常会将这些粒子打回太空或安全地引导到两极(在那里它们产生了地球美丽的极光),但据认为,一次异常大的爆发,比如说典型耀斑的一百倍,可能会压倒我们飘渺的防御。那将是一场壮丽的光影秀,但几乎肯定会杀死沐浴在其光芒下的绝大多数生物。此外,根据美国宇航局喷气推进实验室的布鲁斯·祖鲁塔尼的说法,相当令人不寒而栗的是,“它不会在历史上留下任何痕迹”。
正如一位研究人员所说,这一切留给我们的是“大量的推测和极少的证据”。寒冷似乎与至少三次大的灭绝事件有关——奥陶纪、泥盆纪和二叠纪——但除此之外,几乎没有达成共识,包括某个特定事件是迅速发生还是缓慢发生。例如,科学家们无法就晚泥盆纪灭绝事件——脊椎动物移居陆地的后续事件——是持续了数百万年、数千年,还是在一个活跃的日子里发生的达成一致。
为灭绝事件提出令人信服的解释如此困难的原因之一是,要大规模地消灭生命是如此之难。正如我们从曼森撞击事件中所看到的,你可以承受猛烈的打击,然后仍然完全恢复,尽管可能有点摇摇晃晃。那么,在地球经受的数千次撞击中,为什么希克苏鲁伯撞击事件(KT事件)造成的破坏如此独特呢?嗯,首先,它的确是巨大的。它以相当于1亿兆吨的力量撞击。这样的爆发难以想象,但正如詹姆斯·劳伦斯·鲍威尔指出的那样,如果你为地球上每个活着的人引爆一颗广岛原子弹,你仍然比希克苏鲁伯撞击事件的规模少大约十亿颗炸弹。但即使是那样,可能也不足以消灭地球上70%的生命,包括恐龙。
希克苏鲁伯陨石还有额外的优势——如果你是哺乳动物的话,那就是优势——它降落在一个仅十米深的浅海中,很可能角度正好,当时氧气水平比现在高10%,所以世界更易燃。最重要的是,它降落的海底是由富含硫的岩石构成的。结果是一次撞击,将比利时大小的海底区域变成了硫酸气溶胶。在随后的几个月里,地球遭受了足以灼伤皮肤的酸雨。
从某种意义上说,一个比当时存在的物种中有70%被消灭更大的问题是,剩下的30%是如何幸存下来的?为什么这次事件对当时存在的每一只恐龙都造成了如此不可挽回的毁灭性打击,而其他爬行动物,如蛇和鳄鱼,却安然无恙地通过了?据我们所知,在北美,没有一种蟾蜍、蝾螈、火蜥蜴或其他两栖动物灭绝。“为什么这些脆弱的生物能够从如此空前的灾难中毫发无损地幸存下来?”蒂姆·弗兰纳里在他引人入胜的美国史前史著作《永恒的边疆》中问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