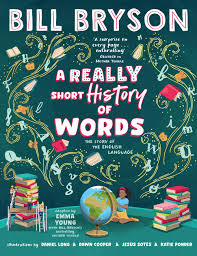1946年,斯普里格是南澳大利亚州政府的一名年轻助理地质学家,当时他被派去调查弗林德斯山脉埃迪卡拉山区的废弃矿井,那是一片位于阿德莱德以北约三百英里的干旱偏远地区。目的是看看是否有任何旧矿井可以通过使用新技术而有利可图地重新开采,所以他根本没有研究地表岩石,更不用说化石了。但有一天吃午饭时,斯普里格漫不经心地翻开一块砂岩,惊讶地——至少可以这么说——看到岩石表面覆盖着精致的化石,很像树叶在泥土中留下的印记。这些岩石早于寒武纪大爆发。他看到的是可见生命的黎明。
斯普里格向《自然》杂志提交了一篇论文,但被退稿了。于是他在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科学促进协会的下一次年会上宣读了这篇论文,但未能获得协会主席的青睐,后者称埃迪卡拉的印记仅仅是“偶然的无机标记”——由风、雨或潮汐造成的图案,而非生物。他的希望尚未完全破灭,斯普里格前往伦敦,在1948年的国际地质大会上展示了他的发现,但未能引起兴趣或信任。最终,由于没有更好的发表途径,他在《南澳大利亚皇家学会会刊》上发表了他的研究结果。然后他辞去了政府工作,投身于石油勘探。
九年后,1957年,一个名叫约翰·梅森的男学生在英格兰中部地区查恩伍德森林散步时,发现了一块岩石,上面有一个奇怪的化石,类似于现代的海笔,并且与斯普里格发现并一直试图告诉大家的某些标本完全一样。这个男学生把它交给了莱斯特大学的一位古生物学家,后者立刻认出它是前寒武纪的。年轻的梅森的照片登上了报纸,并被当作早熟的英雄对待;许多书中至今仍如此。这个标本以他的名字命名为查恩虫(Chamia masoni)。
如今,斯普里格最初的一些埃迪卡拉标本,以及自那时起在整个弗林德斯山脉发现的其他1500件标本中的许多,都可以在阿德莱德坚固可爱的南澳大利亚博物馆楼上一个房间的玻璃柜里看到,但它们并没有引起太多关注。那些精致蚀刻的图案相当模糊,对于外行来说并不十分引人注目。它们大多是小型的圆盘状,偶尔带有模糊的拖曳带状物。福蒂将它们描述为“软体怪胎”。
关于这些东西是什么,它们如何生活,至今仍然几乎没有达成共识。据我们所知,它们没有嘴或肛门来摄取和排出消化物质,也没有内部器官来处理这些物质。“在生活中,”福蒂说,“它们中的大多数可能只是躺在沙质沉积物的表面,就像柔软、无结构、无生命的扁平鱼一样。”在它们最活跃的时候,它们并不比水母更复杂。所有埃迪卡拉生物都是双胚层的,这意味着它们由两层组织构成。除了水母,今天所有的动物都是三胚层的。
一些专家认为它们根本不是动物,而更像是植物或真菌。即使是现在,植物和动物之间的区别也并非总是清晰的。现代海绵一生都固定在一个地方,没有眼睛、大脑或跳动的心脏,但它仍然是动物。“当我们回到前寒武纪时,植物和动物之间的差异可能更加模糊,”福蒂说。“并没有规定说你必须明确地是其中一种或另一种。”
关于埃迪卡拉生物是否是今天任何生物(可能除了某些水母)的祖先,也尚未达成一致。许多权威人士认为它们是一种失败的实验,一次未能成功的复杂性尝试,可能是因为迟缓的埃迪卡拉生物被寒武纪时期更灵活、更复杂的动物吞噬或排挤掉了。
“现今没有与之非常相似的生物存活,”福蒂写道。“很难将它们解释为后来生物的任何一种祖先。”
普遍的看法是,它们最终对地球生命的发展并非至关重要。许多权威人士认为,在前寒武纪-寒武纪界限处发生了一次大规模灭绝,所有埃迪卡拉生物(除了不确定的水母)都未能进入下一阶段。换句话说,复杂生命的真正开端始于寒武纪大爆发。无论如何,古尔德就是这样看的。
至于伯吉斯页岩化石的修订,几乎立刻就有人开始质疑这些解释,特别是古尔德对这些解释的解释。“从一开始,就有一些科学家怀疑斯蒂夫·古尔德提出的说法,无论他们多么钦佩其表达方式,”福蒂在《生命》一书中写道。这说得还算温和。
“要是斯蒂芬·古尔德能像他写作那样清晰地思考就好了!”牛津大学学者理查德·道金斯在一篇评论(发表于伦敦《星期日电讯报》)《奇妙的生命》的开篇中咆哮道。道金斯承认这本书“令人不忍释卷”,是“文学上的杰作”,但他指责古尔德通过暗示伯吉斯页岩的修订震惊了古生物学界,从而进行了“浮夸且近乎不诚实的”事实歪曲。“他所攻击的观点——即进化不可阻挡地走向像人类这样的顶峰——已经有50年没人相信了,”道金斯怒斥道。
然而,这正是许多普通评论者得出的结论。一位在《纽约时报书评》上撰文的评论员兴高采烈地提出,由于古尔德的书,科学家们“一直在抛弃他们几代人未曾审视的一些先入之见。他们正不情愿或热情地接受这样一种观点,即人类既是大自然的偶然产物,也是有序发展的产物。”
但针对古尔德的真正猛烈抨击源于这样一种信念,即他的许多结论根本就是错误的或被粗心地夸大了。道金斯在《进化》杂志上撰文,攻击古尔德关于“寒武纪的进化与今天是一种不同类型的过程”的断言,并对古尔德反复暗示“寒武纪是进化‘实验’、进化‘试错’、进化‘错误开端’的时期”表示愤怒。“那是所有伟大的‘基本身体构造’被发明的肥沃时期。如今,进化只是修补旧的身体构造。回到寒武纪,新的门和新的纲出现了。如今我们只得到新的物种!”
道金斯注意到这个观点——即没有新的身体构造出现——被多么频繁地提及,他说:“就好像一个园丁看着一棵橡树,惊奇地评论道:‘这棵树多年来没有出现任何主要的新大枝,这不是很奇怪吗?如今,所有的新生长似乎都只在细枝末节上。’”
“那是一段奇怪的时期,”福蒂现在说,“尤其是当你想到这一切都是关于五亿年前发生的事情时,但情绪确实非常激动。我在我的一本书里开玩笑说,在写关于寒武纪的文章之前,我感觉自己应该戴上安全帽,但当时确实有点像那样。”
最奇怪的是《奇妙的生命》中的英雄之一西蒙·康威·莫里斯的反应,他突然在自己的一本书《创造的熔炉》中猛烈抨击古尔德,令古生物学界的许多人感到震惊。用福蒂的话说,这本书对待古尔德“带有蔑视,甚至憎恶”。“我从未在一本专业人士的书里遇到过如此的恶意,”福蒂后来写道。“《创造的熔炉》的普通读者,如果不了解历史,永远不会猜到作者的观点曾经接近(如果不是完全认同)古尔德的观点。”
当我问福蒂这件事时,他说:“嗯,这非常奇怪,真的很令人震惊,因为古尔德对他的描绘是如此的奉承。我只能假设西蒙感到尴尬。你知道,科学在变,但书籍是永恒的,我想他后悔自己如此不可挽回地与他不再完全认同的观点联系在一起。还有那些‘哦,他妈的,又一个门’之类的东西,我估计他后悔因此而出名。”
发生的情况是,早寒武纪化石开始经历一个严格重新评估的时期。福蒂和德里克·布里格斯——古尔德书中的另外两位主要人物——使用一种称为支序分类学的方法来比较各种伯吉斯化石。简单来说,支序分类学就是根据共享特征来组织生物体。福蒂举了一个例子,比较鼩鼱和大象。如果你只考虑大象的巨大体型和引人注目的长鼻,你可能会得出结论,它与微小、嗅探的鼩鼱几乎没有共同之处。但如果你将它们都与蜥蜴进行比较,你会发现大象和鼩鼱实际上是按照非常相似的蓝图构建的。本质上,福蒂的意思是,古尔德看到了大象和鼩鼱,而他们看到的是哺乳动物。他们相信,伯吉斯生物并不像初看起来那样奇怪和多样。“它们通常并不比三叶虫更奇怪,”福蒂现在说。“只是我们花了一个世纪左右的时间来适应三叶虫。你知道,熟悉感会滋生熟悉感。”
我应该指出,这并非因为草率或疏忽。根据常常扭曲和零碎的证据来解释古代动物的形态和关系显然是一件棘手的事情。爱德华·O·威尔逊曾指出,如果你选取现代昆虫的特定物种,并将它们呈现为伯吉斯风格的化石,没有人会猜到它们都来自同一个门,因为它们的身体构造差异如此之大。此外,两个更早的寒武纪地点的发现——一个在格陵兰,一个在中国——以及更多零散的发现,也对修订工作起到了重要作用,这些发现提供了许多额外的、往往更好的标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