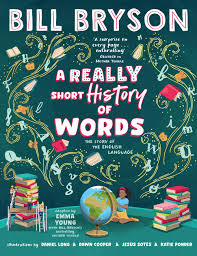在那里,在一篇只有五页的短章(全书九百多页)中,有学问的人第一次接触到了接近现代概念的原子。道尔顿简单的洞见在于,所有物质的根源都是极其微小、不可再分的粒子。“我们试图在太阳系中引入一颗新行星,或者消灭一颗已经存在的行星,就像试图创造或毁灭一个氢粒子一样,”他写道。
原子的概念和术语本身都并非全新。两者都由古希腊人提出。道尔顿的贡献在于思考这些原子的相对大小和特性,以及它们如何组合在一起。例如,他知道氢是最轻的元素,所以他给了它一个原子量 1。他还相信水由七份氧和一份氢组成,所以他给了氧一个原子量 7。通过这种方式,他能够得出已知元素的相对重量。他并非总是非常准确——氧的原子量实际上是 16,而不是 7——但原理是正确的,并构成了所有现代化学和大部分其他现代科学的基础。
这项工作使道尔顿声名鹊起——尽管是以一种低调、英国贵格会式的方式。1826 年,法国化学家 P. J. 佩尔蒂埃前往曼彻斯特拜访这位原子英雄。佩尔蒂埃原以为他会隶属于某个宏伟的机构,因此当他发现道尔顿正在一条后街的小学校里教男孩们初级算术时,他惊讶不已。根据科学史学家 E. J. 霍姆亚德的记载,困惑的佩尔蒂埃看到这位伟人时结结巴巴地说:
“请问我有幸与道尔顿先生说话吗?”因为他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这位欧洲闻名的化学家竟然在教一个男孩最初的四则运算。“是的,”这位务实的贵格会教徒说。“在我教好这个孩子算术的时候,你愿意坐下吗?”
尽管道尔顿试图避免一切荣誉,但他还是违背自己的意愿被选为皇家学会会员,获得了无数奖章,并得到了一笔可观的政府养老金。1844 年他去世时,有四万人瞻仰了他的灵柩,送葬队伍绵延两英里。他在《国家传记词典》中的条目是篇幅最长的之一,在十九世纪的科学家中,只有达尔文和莱尔的条目长度能与之媲美。
道尔顿提出他的假说一个世纪后,它仍然完全是假设性的,一些著名的科学家——特别是维也纳物理学家恩斯特·马赫,声速就是以他命名的——甚至怀疑原子的存在。“原子无法被感官感知……它们是思想的产物,”他写道。原子的存在在德语世界尤其受到如此怀疑,以至于据说它在 1906 年伟大的理论物理学家、原子爱好者路德维希·玻尔兹曼的自杀中起了一定作用。
正是爱因斯坦在 1905 年关于布朗运动的论文中提供了原子存在的第一个无可辩驳的证据,但这并没有引起多少注意,而且无论如何,爱因斯坦很快就全神贯注于他的广义相对论研究。因此,原子时代的第一位真正的英雄,如果不是第一个登场的人物的话,是欧内斯特·卢瑟福。
卢瑟福 1871 年出生于新西兰的“偏远地区”,父母是从苏格兰移民过来种植少量亚麻和抚养大量孩子的(引用史蒂文·温伯格的话)。他在一个偏远国家的偏远地区长大,距离科学主流尽可能地遥远,但在 1895 年,他获得了一项奖学金,带他来到了剑桥大学的卡文迪什实验室,那里即将成为世界上最热门的物理学研究地。
物理学家们以对其他领域科学家的蔑视而闻名。当伟大的奥地利物理学家沃尔夫冈·泡利 的妻子为了一个化学家而离开他时,他惊愕不已。“如果她跟了一个斗牛士,我还能理解,”他惊奇地对一位朋友说。“但是一个化学家……”
这是卢瑟福会理解的一种感受。“所有的科学要么是物理学,要么是集邮,”他曾说过,这句话此后被多次引用。因此,当他在 1908 年获得诺贝尔奖时,获奖领域是化学而非物理学,这其中自有某种引人入胜的讽刺意味。
卢瑟福是个幸运的人——幸运地是个天才,但更幸运的是生活在一个物理学和化学如此激动人心、如此兼容的时代(尽管他自己有不同的看法)。它们再也不会如此舒适地重叠了。
尽管取得了种种成功,卢瑟福并非特别聪明的人,数学方面实际上相当糟糕。讲课时,他常常会迷失在自己的方程式中,以至于讲到一半就放弃,让学生们自己去解决。根据他长期的同事、中子的发现者詹姆斯·查德威克的说法,他甚至在实验方面也不是特别聪明。他只是坚韧不拔、思想开放。他用精明和一种勇气取代了才华。用一位传记作者的话来说,他的头脑“总是在前沿运作,尽可能远地眺望,而这比大多数其他人要远得多”。面对棘手的问题,他准备比大多数人更努力、更长时间地工作,并且更愿意接受非正统的解释。他最大的突破来自于他愿意花费大量极其枯燥的时间坐在屏幕前数α粒子闪烁,正如人们所知的那样——这种工作通常会被外包出去。他是最早看到——可能是第一个——原子固有力量的人之一,如果加以利用,可以制造出强大到足以“让这个旧世界化为乌有”的炸弹。
他体格魁梧,嗓门洪亮,声音能让胆小的人退缩。有一次,当得知卢瑟福即将在大西洋彼岸进行广播时,一位同事干巴巴地问:“为什么要用广播?”他还有着巨大的、善意的自信。当有人对他评论说他似乎总是在浪潮之巅时,他回答说:“嗯,毕竟,浪潮是我制造的,不是吗?”C. P. 斯诺回忆起有一次在剑桥的一家裁缝店里,他无意中听到卢瑟福说:“我每天都在长胖。而且在智力上也是。”
但无论是体型还是名声,都远在他 1895 年到达卡文迪什[20] 之后。那是科学史上一个非凡多事的时期。在他到达剑桥的那一年,威廉·伦琴在德国维尔茨堡大学发现了 X 射线,第二年亨利·贝克勒尔发现了放射性。而卡文迪什本身也即将开启一段漫长的辉煌时期。1897 年,J. J. 汤姆森及其同事在那里发现了电子;1911 年,C. T. R. 威尔逊在那里制造了第一个粒子探测器(我们稍后会看到);1932 年,詹姆斯·查德威克在那里发现了中子。更遥远的未来,詹姆斯·沃森和弗朗西斯·克里克将在 1953 年在卡文迪什发现 DNA 的结构。
起初,卢瑟福研究无线电波,并取得了一些成就——他成功地将清晰的信号传输了一英里多,这在当时是相当不错的成就——但在一位资深同事说服他无线电没什么前途后,他放弃了。然而,总的来说,卢瑟福在卡文迪什并没有取得成功。在那里待了三年后,他感觉自己毫无进展,于是接受了蒙特利尔麦吉尔大学的一个职位,并在那里开始了他漫长而稳步走向伟大的历程。到他获得诺贝尔奖时(根据官方引文,获奖理由是“对元素衰变以及放射性物质化学的研究”),他已经转到曼彻斯特大学,事实上,正是在那里,他将完成他最重要的工作,确定原子的结构和性质。
到了二十世纪初,人们已经知道原子是由部分组成的——汤姆森发现电子已经证明了这一点——但不知道有多少部分,它们如何组合在一起,或者它们呈现什么形状。一些物理学家认为原子可能是立方体形状的,因为立方体可以如此整齐地堆叠在一起而没有任何浪费的空间。然而,更普遍的观点是,原子更像一个葡萄干面包或李子布丁:一个致密、坚实的物体,带有正电荷,但上面镶嵌着带负电荷的电子,就像葡萄干面包里的葡萄干一样。
1910年,卢瑟福(在他的学生汉斯·盖革的协助下,后者后来发明了以他名字命名的辐射探测器)将电离的氦原子,即α粒子,射向一张金箔。[21]令卢瑟福惊讶的是,一些粒子反弹了回来。他说,这就像他向一张纸发射了一枚十五英寸的炮弹,结果炮弹弹回了他的膝盖上。这根本就不应该发生。经过深思熟虑,他意识到只可能有一种解释:那些反弹回来的粒子撞击了原子核心处某种小而密的东西,而其他粒子则畅通无阻地穿过去了。卢瑟福意识到,原子大部分是空的空间,中心有一个非常致密的原子核。这是一个非常令人满意的发现,但它立刻带来了一个问题。根据所有传统物理定律,原子根本不应该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