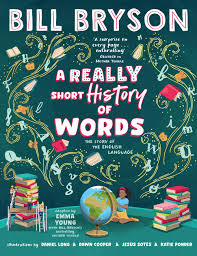结合勒维特的宇宙标尺和维斯托·斯莱弗方便的红移,埃德温·哈勃现在开始以全新的眼光测量太空中的选定点。1923 年,他证明了仙女座中一团被称为 M31 的遥远薄纱根本不是气体云,而是一片恒星的光辉,一个独立的星系,直径十万光年,距离至少九十万光年。宇宙比任何人想象的都要 vast (浩瀚)—— vastly vaster (浩瀚得多)。1924 年,他发表了一篇里程碑式的论文《螺旋星云中的造父变星》(nebulae,源自拉丁语“云”,是他对星系的称呼),表明宇宙不仅由银河系组成,而且由许多独立的星系——“岛宇宙”——组成,其中许多比银河系更大,距离也远得多。
仅这一发现就足以确保哈勃的声誉,但他现在转向了计算宇宙到底有多浩瀚的问题,并做出了一个更惊人的发现。哈勃开始测量遥远星系的光谱——斯莱弗在亚利桑那州开始的那项工作。利用威尔逊山天文台新的百英寸胡克望远镜和一些巧妙的推断,他计算出天空中所有的星系(除了我们自己的本星系群)都在远离我们。此外,它们的速度和距离成正比:星系越远,移动速度越快。
这真是令人震惊。宇宙正在膨胀,向各个方向迅速而均匀地膨胀。不需要太多的想象力就能从此倒推,意识到它必定是从某个中心点开始的。远非每个人一直假设的那样稳定、固定、永恒的虚空,这是一个有开端的宇宙。因此它也可能有终结。
正如斯蒂芬·霍金指出的那样,令人惊奇的是,以前没有人想到过膨胀宇宙的想法。一个静态的宇宙,正如牛顿和此后每一位有思想的天文学家都应该明白的那样,会向内坍缩。还有一个问题是,如果恒星在一个静态宇宙中无限期地燃烧,它们会使整个宇宙变得无法忍受地热——肯定比我们能承受的要热得多。一个膨胀的宇宙一下子就解决了很多问题。
哈勃是一位远比思想家更优秀的观测者,他并没有立刻领会到自己发现的全部含义。部分原因在于他对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极其无知。这相当引人注目,因为,首先,爱因斯坦和他的理论当时已经世界闻名。此外,1929 年,阿尔伯特·迈克尔逊——当时已步入晚年,但仍是世界上最敏锐、最受尊敬的科学家之一——接受了威尔逊山天文台的一个职位,用他那可靠的干涉仪测量光速,他必定至少向哈勃提到了爱因斯坦理论对其自身发现的适用性。
无论如何,哈勃未能抓住机会在理论上取得进展。相反,将这两条线索整合到他自己的“烟花理论”中的任务留给了比利时牧师兼学者乔治·勒梅特(拥有麻省理工学院博士学位),他提出宇宙始于一个几何点,一个“原始原子”,它爆发成荣耀,此后一直在分离运动。这个想法非常巧妙地预见了现代大爆炸的概念,但它远远超前于时代,以至于勒梅特很少得到超过我们在此给出的这一两句话的关注。世界还需要几十年的时间,以及彭齐亚斯和威尔逊在新泽西他们那嘶嘶作响的天线上无意中发现宇宙背景辐射,大爆炸才开始从一个有趣的想法转变为公认的理论。
哈勃和爱因斯坦都不会是那个宏大故事的主要部分。尽管当时没有人会猜到,但两人都已经完成了他们所能做的几乎所有事情。
1936年,哈勃出版了一本名为《星云王国》的通俗读物,以奉承的风格解释了他自己相当可观的成就。在这里,他终于表明自己已经熟悉了爱因斯坦的理论——至少在某种程度上是这样:在大约两百页的书中,他给了它四页的篇幅。
哈勃于 1953 年死于心脏病发作。最后一个小小的怪事等待着他。出于神秘的原因,他的妻子拒绝举行葬礼,并且从未透露她如何处理了他的遗体。半个世纪后,这位世纪最伟大天文学家的下落仍然未知。要寻找纪念碑,你必须仰望天空,看看 1990 年发射并以他名字命名的哈勃太空望远镜。
万物简史
第九章:强大的原子
当爱因斯坦和哈勃富有成效地解开宇宙大尺度结构的同时,另一些人则在努力理解一种更近在咫尺,但在某种程度上同样遥远的东西:微小且永远神秘的原子。
伟大的加州理工学院物理学家理查德·费曼曾观察到,如果你必须将科学史浓缩为一句重要陈述,那将是“万物皆由原子构成”。它们无处不在,构成一切。看看你周围。全是原子。不仅是像墙壁、桌子和沙发这样的固体,还有它们之间的空气。它们存在的数量是你根本无法想象的。
原子的基本工作单元是分子(源自拉丁语“小质量”)。分子仅仅是两个或多个原子以或多或少稳定的排列方式协同工作:将两个氢原子加到一个氧原子上,你就得到了一个水分子。化学家倾向于从分子的角度思考,而非元素,就像作家倾向于从词语的角度思考,而非字母,所以他们计算的是分子,而这些分子数量至少可以说极其庞大。在海平面、华氏 32 度的温度下,一立方厘米的空气(即大约方糖大小的空间)将包含 4500 亿亿个分子。它们存在于你周围看到的每一个立方厘米中。想想你窗外的世界有多少立方厘米——需要多少方糖才能填满那个景象。然后想想建造一个宇宙需要多少。简而言之,原子非常丰富。
它们也异常耐用。因为原子寿命如此之长,它们真的四处游荡。你拥有的每一个原子几乎可以肯定地穿过了几颗恒星,并成为数百万个生物的一部分,最终才成为你。我们每个人在原子数量上如此众多,并且在死亡时被如此积极地回收利用,以至于我们相当数量的原子——据估计,我们每个人多达十亿个——很可能曾经属于莎士比亚。另外十亿个分别来自佛陀、成吉思汗和贝多芬,以及任何你能想到的其他历史人物。(显然,这些人必须是历史人物,因为原子需要几十年才能被彻底重新分配;无论你多么希望,你还不是猫王的一部分。)
所以我们都是转世——尽管是短暂的转世。当我们死后,我们的原子会分解并转移到别处寻找新的用途——作为一片叶子、另一个人或一滴露珠的一部分。然而,原子几乎永远存在。没有人确切知道一个原子能存活多久,但根据马丁·里斯的说法,它可能大约是 10^35 年——这个数字如此之大,即使我也乐于用符号表示。
最重要的是,原子非常微小——确实非常微小。五十万个原子肩并肩排列起来可以躲在一根人类头发后面。在这样的尺度上,单个原子基本上是无法想象的,但我们当然可以尝试一下。
从一毫米开始,就是这么长的一条线:-。现在想象这条线被分成一千个等宽的部分。每一个宽度就是一个微米。这是微生物的尺度。例如,一个典型的草履虫大约两微米宽,即 0.002 毫米,这确实非常小。如果你想用肉眼看到一滴水中的草履虫游泳,你必须将这滴水放大到大约四十英尺宽。然而,如果你想看到同一滴水中的原子,你必须将这滴水放大到十五英里宽。
换句话说,原子存在于另一个数量级的微小尺度上。要达到原子的尺度,你需要将每一个微米切片再削成一万个更细的宽度。这就是原子的尺度:一毫米的千万分之一。这是一种远远超出我们想象能力的纤细程度,但如果你记住一个原子相对于一毫米线的宽度,就像一张纸的厚度相对于帝国大厦的高度一样,你就能对这个比例有所了解。
当然,正是原子的丰富性和极强的耐久性使它们如此有用,而它们的微小性则使它们如此难以探测和理解。认识到原子具有这三个特性——微小、众多、几乎不可摧毁——并且万物皆由它们构成,这并非像你可能预期的那样,首先出现在安托万-洛朗·拉瓦锡身上,甚至不是亨利·卡文迪什或汉弗莱·戴维,而是一位名叫约翰·道尔顿的节俭、受教育程度不高的英国贵格会教徒,我们最早在化学那一章遇到过他。
道尔顿 1766 年出生在靠近科克茅斯的湖区边缘,一个贫穷但虔诚的贵格会织布工家庭。(四年后,诗人威廉·华兹华斯也将在科克茅斯降生。)他是一位异常聪明的学生——确实非常聪明,以至于在年仅十二岁这个令人难以置信的年幼年龄,就被任命负责当地的贵格会学校。这或许更多地说明了学校的情况,而非道尔顿的早熟,但或许并非如此:我们从他的日记中得知,大约在这个时候,他正在阅读牛顿《原理》的拉丁文原著以及其他类似具有挑战性的著作。十五岁时,他仍在教书,在附近的肯德尔镇找到了一份工作,十年后他搬到了曼彻斯特,此后五十年几乎没有离开过那里。在曼彻斯特,他成了一位知识界的旋风式人物,撰写了从气象学到语法的各种主题的书籍和论文。色盲,他所患的一种疾病,因为他的研究而长期被称为道尔顿症。但正是 1808 年出版的一本厚厚的书《化学哲学新体系》,使他声名鹊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