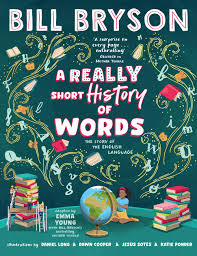迈克尔逊和莫雷所做的,实际上并非有意为之,是动摇了对一种称为“光以太”的长期信念。光以太是一种稳定、无形、无重、无摩擦,但不幸完全虚构的介质,被认为弥漫于宇宙之中。笛卡尔构想,牛顿拥护,此后几乎所有人都尊崇的以太,在十九世纪物理学中占据绝对核心地位,用以解释光如何穿越空间的空虚。在 1800 年代尤其需要它,因为光和电磁现在被视为波,也就是一种振动。振动必须在某种东西中发生;因此需要并长期信奉以太。直到 1909 年,伟大的英国物理学家 J. J. 汤姆森仍然坚持:“以太并非思辨哲学家的奇幻创造;它对我们来说就像我们呼吸的空气一样必不可少”——这距离它几乎无可争辩地被证实不存在已经过去了四年多。简而言之,人们确实对以太情有独钟。
如果你需要说明十九世纪美国是一个充满机遇的国度,阿尔伯特·迈克尔逊的一生几乎是无可挑剔的例证。他 1852 年出生于德波边境一个贫穷的犹太商人家庭,幼年随家人来到美国,在加州淘金热时期的矿区长大,父亲在那里经营一家杂货店。由于家境贫寒,无法支付大学学费,他前往华盛顿特区,在白宫前门徘徊,以便在尤利西斯·S·格兰特总统出来进行每日散步时能走到他身边。(那显然是一个更天真的时代。)在这些散步过程中,迈克尔逊如此讨得总统欢心,以至于格兰特同意为他争取一个美国海军学院的免费名额。正是在那里,迈克尔逊学习了物理学。
十年后,迈克尔逊已是克利夫兰凯斯学院的教授,他对测量一种称为“以太漂移”的东西产生了兴趣——这是一种运动物体在穿越太空时产生的逆风。牛顿物理学的预测之一是,光穿过以太的速度相对于观察者应该有所不同,取决于观察者是朝向光源运动还是远离光源运动,但没有人想出测量这个的方法。迈克尔逊想到,地球一年中有一半时间朝向太阳运动,另一半时间则远离太阳,他推断,如果你在相反的季节进行足够仔细的测量,并比较两次光线的传播时间,你就能得到答案。
迈克尔逊说服了新近致富的电话发明家亚历山大·格雷厄姆·贝尔提供资金,建造了一台由迈克尔逊自己设计的巧妙而灵敏的仪器,称为干涉仪,它可以非常精确地测量光速。然后,在和蔼可亲但神秘莫测的莫雷的协助下,迈克尔逊开始了长达数年的 meticulous (一丝不苟的) 测量。这项工作既精细又累人,曾一度不得不暂停,以便让迈克尔逊短暂但彻底地精神崩溃一下,但到 1887 年,他们得到了结果。结果完全出乎两位科学家的意料。
正如加州理工学院天体物理学家基普·S·索恩所写:“光速在所有方向和所有季节都被证明是相同的。”这是两百年来——事实上,正好是两百年来——第一次暗示牛顿定律可能并非在所有时间和所有地方都适用。迈克尔逊-莫雷实验的结果,用威廉·H·克罗珀的话来说,成为了“可能是物理学史上最著名的否定性结果”。迈克尔逊因此项工作获得了诺贝尔物理学奖——他是第一个获此殊荣的美国人——但这要等到二十年后。与此同时,迈克尔逊-莫雷实验将像一股霉味一样令人不快地徘徊在科学思想的背景中。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有他的发现,但当二十世纪来临时,迈克尔逊仍然把自己算作那些相信科学工作已近尾声的人之一,用《自然》杂志一位作者的话来说,只剩下“几座塔楼和尖顶需要添加,几个屋顶雕饰需要雕刻”。
事实上,当然,世界即将进入一个科学的世纪,在这个世纪里,许多人将什么都不懂,没有人会什么都懂。科学家们很快将发现自己漂浮在一个令人困惑的粒子和反粒子领域,在那里,事物在纳秒看起来缓慢而平淡的时间跨度内出现又消失,在那里,一切都是奇怪的。科学正从一个宏观物理学的世界,即物体可以被看到、持有和测量的世界,转向一个微观物理学的世界,即事件在远低于想象极限的尺度上以难以想象的速度发生。我们即将进入量子时代,而第一个推开这扇门的人是迄今为止不幸的马克斯·普朗克。
1900年,普朗克已是柏林大学的理论物理学家,年龄已届四十二岁,他提出了一个新的“量子理论”,假设能量并非像流水一样连续不断,而是以他称为“量子”的独立包形式存在。这是一个新颖且优秀的概念。短期内,它有助于解决迈克尔逊-莫雷实验的难题,因为它证明了光未必是波。从长远来看,它将为整个现代物理学奠定基础。无论如何,这是世界即将改变的第一个线索。
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新纪元的黎明——发生在 1905 年,当时德国物理学期刊《物理学年鉴》上刊登了一系列论文,作者是一位年轻的瑞士官员,他没有大学背景,无法使用实验室,也无法经常使用比伯尔尼国家专利局(他当时在那里担任三级技术审查员)更大的图书馆。(他最近申请晋升为二级技术审查员被拒绝了。)
他的名字是阿尔伯特·爱因斯坦,就在那一个多事之秋的一年里,他向《物理学年鉴》提交了五篇论文,其中三篇,根据 C. P. 斯诺的说法,“是物理学史上最伟大的论文之一”——一篇利用普朗克的新量子理论研究光电效应,一篇关于悬浮小颗粒的行为(即所谓的布朗运动),还有一篇概述了狭义相对论。
第一篇论文为作者赢得了诺贝尔奖,并解释了光的本质(此外还帮助实现了电视等事物)。[17] 第二篇论文提供了原子确实存在的证据——令人惊讶的是,这一事实曾一度存在争议。第三篇论文仅仅改变了世界。
爱因斯坦 1879 年出生于德国南部的乌尔姆,但在慕尼黑长大。他早年的生活几乎没有显示出未来的伟大。众所周知,他直到三岁才学会说话。1890 年代,他父亲的电器生意失败,全家搬到了米兰,但当时已是青少年的阿尔伯特前往瑞士继续他的教育——尽管他第一次大学入学考试失败了。1896 年,他放弃了德国国籍以逃避兵役,并进入苏黎世理工学院,参加了一个为期四年的课程,旨在培养高中科学教师。他是个聪明但并非出类拔萃的学生。
1900年,他毕业了,几个月内就开始向《物理学年鉴》投稿。他的第一篇论文,关于吸管中流体物理学(真是奇特的主题),与普朗克的量子理论发表在同一期。从1902年到1904年,他发表了一系列关于统计力学的论文,结果发现康涅狄格州那位默默无闻、富有成效的J. 威拉德·吉布斯也完成了这项工作,在他的1901年的《统计力学基本原理》中。
与此同时,他爱上了一位名叫米列娃·马里奇的匈牙利同学。1901 年,他们有了一个私生女,这个女儿被悄悄地送人收养了。爱因斯坦从未见过他的孩子。两年后,他和马里奇结婚了。在这些事件之间,1902 年,爱因斯坦在瑞士专利局找到了一份工作,并在那里待了接下来的七年。他喜欢这份工作:它足够有挑战性,能够吸引他的思维,但又不足以分散他对物理学的注意力。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他在 1905 年提出了狭义相对论。
这篇题为《论运动物体的电动力学》的论文是有史以来发表的最非凡的科学论文之一,其呈现方式和内容同样引人注目。它没有脚注或引文,几乎不含数学公式,没有提及任何影响或先于它的工作,并且只致谢了一个人——专利局的一位同事米歇尔·贝索。C. P. 斯诺写道,就好像爱因斯坦“是通过纯粹的思考得出结论,没有借助他人,没有听取他人的意见。在很大程度上,这正是他所做的。”
他著名的方程式 E = mc² 并非与论文一同出现,而是在几个月后的一份简短补充中提出的。正如你从学生时代所记得的那样,方程式中的 E 代表能量,m 代表质量,c² 代表光速的平方。
简单来说,这个方程式表明质量和能量是等效的。它们是同一事物的两种形式:能量是解放了的物质;物质是等待发生的能量。由于 c²(光速乘以自身)是一个真正巨大的数字,这个方程式所说的是,在每一个物质事物中都蕴藏着巨大的——真正巨大的——能量。[18]